|
五、结语 现在来追究一下闽语文读音的来源,大家都同意基本上文读音的起源是由于科举制度带来的(19)。李如龙(1996:55)指出:“闽方言形成之后,赶上盛唐中古音的强大影响,各地闽方言的文读音显然是广韵音系覆盖的结果。”丁邦新(2007:2-3)的序言中指出: 在中国历史上首开科举是隋代的事,正好隋仁寿元年(601年)陆法言《切韵》成书。唐代沿袭《切韵》的孙愐的《唐韵》非常盛行。王国维《书蒋氏藏唐写本唐韵后》说:“唐人盛为诗赋,韵书当家置一部,故陆孙二韵,当时写本当以万计。”相信当时南北两大方言的所谓标准音就随着科举跟韵书而流行(丁邦新1995),既有实际的需要,又有完整的系统。这些标准音进入大多数方言就成为文读音。 标准音产生改变,或者以邻近的大都市通行的方言作为标准音,或者民间找不到说标准音的读书人,而从文化较高的城市找来的师傅说某一种方言,这种种原因都可能造成声韵各异的文读音,而一千多年以来标准音虽然改变却又总是存在。因此“优势语言”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来源,造成文读音的层次,而读书、科举、官场的需要则成为推波助澜的动力。至于白话音,则因为移民群先后的混杂,也可能造成不同的层次。 我引用这一大段文字主要是说明闽语文白层次造成的原因,以及跟世界上其他语言比较起来为什么独特。 在白话层里又因移民群先后的原因,留下早晚层次的痕迹。近年来陈忠敏(2002)、梅祖麟(2001)还讨论吴语跟闽语层次间的对应,以及鱼虞有别的层次属于古江东方言的现象。古江东方言就是丁邦新(1995)所说的《切韵》时代的金陵音系。 汉语方言里整体文白异读的现象并不一致,官话、吴语、晋语、客家话、赣语、湘语、粤语大体跟北京音一样,文读未必是读书音,而是一种口语,时间或早或晚。当两种白话音融合的时候,用其中一种强势的白话音来读书,因为用这种白话音读书,慢慢就成为文读。这种情形包括所有片面的文白异读,只有某些声母、某些韵母、或某些韵尾的字具有两读,而不是全面。这是两种白话音的混合引起的现象,其中也许还有更早期的底层。底层的语音或多或少,有的可以说定,有的难以论断。另一种情形较为全面,就像闽语跟儋州话,白读是本有的,文读真的是所谓读书音,由于科举盛行,文读是为了读书从强势方言借进来的语音,以及离标准音远的地方引进的形形色色的外来方言。 2010年5月20-22日国际中国语言学会年会在美国哈佛大学举行,我应邀作主题讲演,本文是就讲演的初稿增订而成。 注释: ①2007年我主编了一本《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其中收了15篇论文;最近在各种学术刊物中见到的有关方言层次的论文总有几十篇,硕士博士论文也不在少数。 ②这里的看法大概是目前一般的意见,我没有一一列明出处。参看丁邦新(2007)。 ③这一节里的说明大体根据丁邦新(2006)的文章《北京话文白异读和方言移借》,文字上略有不同。为了讨论的方便,并免去读者翻检之劳,引用的部分比较长一点。 ④这里讨论韵母,例字中的声调符号都省略了;以下如非必要,也不标声调。 ⑤丁邦新(1998)曾经用“交融积累”跟“犬牙交错”来说明北京话入声的演变。 ⑥丁邦新(2011)另外写了一篇文章《苏州话文白的性质》,见《中国语言学集刊》5.1:81-94。这里只是简略地引用那篇文章相关的部分。 ⑦赵元任的《早年自传》里并未清楚说明几岁学会苏州话,此处根据赵新那、黄培云(1998:47)。  ⑨王洪君(2006:74)认为旧派、新派“主要不是年龄的区别,而是社会集团的分别。”显然有以今律古的问题,参看丁邦新(2011)的讨论。 ⑩斜线前面的是文读,后面的是白读。下同。 (11)李如龙、张双庆(1992)的资料客赣语各有17个方言点;刘纶鑫(1999)则有12个客家话跟23个赣语方言点。 (12)这些地方所在的省份见李如龙、张双庆(1992)目录之前的地图。 (13)23个方言点中只有接近安徽、湖北边境的湖口、星子两地“放假”的“假”读t  ia。 ia。(14)这个异读来源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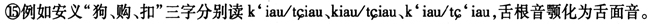 (16)李如龙、张双庆(1992:18)提到:“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有些点文白读和异读未能充分反映。” (17)“苦、气”两字的文白异读出现的词汇不同,文读见于“辛苦、气体”,白读见于“苦味、出气”,但另外三个字文白出现的词汇并没有清楚的分野。 (18)根据杨艳未发表稿:“衡阳方言的文白异读”。 (19)记忆中似乎别人有类似的看法,但我努力翻检,没有找到,只能归之于共识。 【参考文献】 [1]陈重瑜2002《北京音系里文白异读的新旧层次》,《中国语文》第6期。 [2]陈忠敏2002《方言间的层次对应——以吴闽语虞韵读音为例》,见丁邦新、张双庆编:《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语言的关系》73-8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3]陈忠敏2007《语言层次的定义及其鉴定方法》,见丁邦新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135-16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4]丁邦新1966《如皋方言的音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6:573-633。 [5]丁邦新1986《儋州村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84,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6]丁邦新1987《论官话方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8.4:809-841。 [7]丁邦新1995《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国语文》第6期。 [8]丁邦新1998a《汉语方言接触的几个类型》,《语言学论丛》20:149-165,北京:商务印书馆。又见2008:129-141。 [9]丁邦新1998b《丁邦新语言学语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10]丁邦新2002《苏州同音常用字汇之文白异读》,《中国语文》第5期。 [11]丁邦新2003《一百年前的苏州话》,上海教育出版社。 [12]丁邦新2006《北京话文白异读和方言移借》,《语言暨语言学》专刊外编之七,《门内日与月:郑锦全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1-8。又见2008:211-218。 [13]丁邦新2007《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14]丁邦新2008《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15]丁邦新2011《苏州话文白的性质》,《中国语言学集刊》5.1:81-94。 [16]耿振生2003《北京话文白异读的形成》,《语言学论丛》27:56-68,北京:商务印书馆。 [17]何大安1981《澄迈方言的文白异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2.1:101-152。 [18]侯精一温端政1993《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李蓝1991《“贵州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及“读后”订补》,《中国语文》第3期。 [20]李荣1982《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音韵存稿》107-118,北京:商务印书馆。 [21]李如龙1996《方言与音韵论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言研究中心。 [22]李如龙张双庆1992《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 [23]梁玉璋1984《福州话的文白异读》,《中国语文》第6期。 [24]刘纶鑫1999《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5]刘勋宁1983《陕北清涧方言的文白异读》,《中国语文》第1期。 [26]梅祖麟2001《现代吴语和“支脂鱼虞,共为不韵”》,《中国语文》第1期。 [27]钱乃荣1992《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28]王福堂2006《文白异读中读书音的几个问题》,《语言学论丛》32:1-13,北京:商务印书馆。 [29]王洪君1987《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中国语文》第1期。 [30]王洪君2006《层次与演变阶段——苏州话文白异读析层拟测三例》,《语言暨语言学》7.1:63-86。 [31]王洪君2007《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见丁邦新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36-8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32]熊正辉1985《南昌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第3期。 [33]杨秀芳1982《闽南语文白系统的研究》,台湾大学博士论文。 [34]叶祥苓1988《苏州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 [35]詹伯慧张日升1987《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36]张琨1985《论吴语方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6.2:215-260。 [37]张盛裕1979《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第4期。 [38]张振兴1989-1990《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1989.3:171-179;1989.4:281-292;1990.1:44-51。 [39]赵新那黄培云1998《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 [40]赵元任1928《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 [41]赵元任1984《早年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42]周长楫1983《厦门话文白异读的类型》,《中国语文》第5、6期。 [43]S  ren Egerod 1956 The Lungtu Dialect, Copenhagen: Ejnar Munksgaard, Ltd. Publishers
(责任编辑:admin) ren Egerod 1956 The Lungtu Dialect, Copenhagen: Ejnar Munksgaard, Ltd. Publishers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