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史记》衍生型文本的生成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面所举个案中,司马迁对于文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时他对于文本完全“失控”,例如瞽叟欲杀舜、师曹诵《巧言》诸例,他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些重复、误读、失实的内容,假设他注意到了,相信这些错误都可得以纠正。但也有时,他注意到所据文本存在叙事上的“疏漏”,试图对其加以弥缝,并认为自己在此过程中控制了文本,但实际上文本仍处于失控的状态,例如公子斑鞭荦、庆父哀姜私通诸例。在这些个案中,面对难以理解的文本,司马迁的“弥缝”并非基于浪漫的文学想象,而是为了完成叙述、构建文本的被动之举。不过,从效果上看,这些“弥缝”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史记》的“文学性”。 不过,《史记》中的另外一些个案显示,司马迁的“弥缝”常常又是有意为之的。面对文本,司马迁尝试彻底掌控他们,“其文则史”、“其意则丘窃取之”,(31)公羊学对于孔子“作《春秋》”(32)这一文本书写方式的强调以及司马迁“继《春秋》”(33)的志向赋予其“控制文本”的行为一种合法性乃至神圣性,使得他敢于、甚至乐于对既有文本进行各种形式的改造,生成新的衍生型文本。我们可将其概括为四种基本方式: 首先是改笔,例如《五帝本纪》中关于舜嗣位的记述: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34) 这段材料又见于《孟子·万章》: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曰:“……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35) 《史记·孟子列传》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36)由是知司马迁尝读《孟子》,而《五帝本纪》中的这段记述既然与《孟子》存在高度相关性,则我们有理由推定,《万章》篇这段内容正是司马迁所据史源。不过,从《万章》篇的叙述来看,自“尧崩”至“践天子位焉”并不是一段独立的文本,而是紧承上文:万章向孟子请教尧何以以天下与舜,而孟子从根本上反对“以天下与人”之说,而是强调“天命论”,认为尧只是向天推荐舜,真正授命于舜者不是尧而是天,故万章继而请教“天”如何授命于舜,于是孟子先以“使之主祭”和“使之主事”统论“天受之”与“民受之”之意,继而结合舜的具体经历,指出其相尧二十八载,非人力所能及,自有天命蕴于其中。又言尧崩后,舜避位而诸侯朝觐、狱讼、讴歌皆之舜,由此得出结论“故曰天也”。此“故曰”二字远承前文“曰:天与之。”且与上文先后两次出现的“故曰”体例相同,都是孟子总结陈词的引语。简言之,自“舜相尧”至“故曰天也”是一段逻辑严密、语气贯通的论述,《五帝本纪》系截取《万章》篇“尧崩”以下数句援为己用,这一结论当无大谬。 然而有趣的是,司马迁的叙述与《万章》篇存在一处关键差异,即《万章》中“故曰天也”句在《五帝本纪》中作“舜曰:天也!”而前文已言,“故曰”是《万章》中孟子总结陈词之引语,且这里“故曰天也”显然是对上文论述的总结,因此,从文本内部的语意关系来看,《万章》中的“故曰天也”与上下文之间是一以贯之的同质化关系,而《五帝本纪》中的“舜曰:天也!”则是经过改笔的异质性文本。舜嗣位的这段文本在《万章》中原本承担论据的功能,而司马迁将其截取,并赋予其叙事的功能,而在他的叙事语境中,显然无法容纳“故曰”这样的总结式话语,而“天”作为《万章》中讨论的权力合法性来源,在《五帝本纪》中则仍可承担其权力来源的功能,因此,司马迁改“故”为“舜”,圆融地将孟子“天也”这一核心理念归诸舜本人之口。相对于上一部分所举“文本失控”之例,这里司马迁成功掌控了这段文本,若无《孟子》为对照,读者实在无法发现其内在异质性。从文学叙事的层面来看,这一改笔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其次是留白。仍以《五帝本纪》为例,据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介绍,这一部分的基本史料来源是《五帝德》和《帝系》,这两部文献都见于今本《大戴礼记》,将两者比对后我们发现,在黄帝、颛顼、帝喾三人的记述中,分别有一段文字见于《大戴礼记》本《五帝德》,而不见于《史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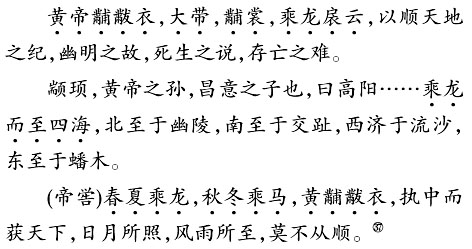 为什么关于三帝服色、乘舆的记载不见于《史记》呢?(38)若将其简单解释为司马迁所据《五帝德》的残缺,恐怕过于随意。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司马迁认为这三帝“乘龙”之说太过离奇,是所谓“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者,所以,本着“择其言尤雅者”的钞录原则,尽管颛顼一节中“北至于幽陵”四句因此显得颇为突兀,但为了符合其著述原则,司马迁还是有意刊落了这三节文字。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留白”是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虽然不着一笔,但那空缺的部分恰体现了画家精巧的构思,并与着笔之处形成有效的呼应。在笔者看来,司马迁这里的删节就如同绘画中的“留白”,在取舍之间体现了司马迁的匠心独运。设想,如果没有《大戴礼记·五帝德》中的这段文字,司马迁的这一细微的删改是几乎难以被发现的,而一旦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则我们对于他著述的原则便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 还有一例见于《五帝本纪》中关于瞽叟、象合谋杀舜一事的记载: 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39) 这段材料又见于《孟子·万章》: 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揜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40)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