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时安 “我是上海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一个喝着黄浦江水,听着上海东区机器轰鸣声长大的上海人。这里有我的至亲骨肉,有我的良师益友,有给了我血肉灵魂的土地。在上海,我看见无数的文学家、艺术家,一代接着一代,像黄浦江的潮水,一浪接着一浪,生生不息地向着艺术的高峰无畏攀登。”在去年出版的评论集《攀登者》后记中,评论家毛时安深情写道。那些无畏攀登艺术高峰的身影,就是这本文集书名的缘起。 这部文集的副题则是:上海文化的目击与思考。在这座由江南文化的柔韧、海派文化的包容创新、红色文化的坚定信仰共同构筑了独特文化底色的伟大城市中,毛时安始终与艺术家们一起工作,他看着艺术家把时代和人们的喜怒哀乐写入作品,把这座城市的精神和力量,把寻常百姓平凡而伟大的生活、灵魂,变成作品里人物灵魂悸动的心电图,他以目击者、参与者、思考者的身份,深入评论了代表上海文化时代标高的各类艺术作品。 四十多年来,毛时安见证上海文化一路走来的艰辛和努力,看着它结出“满树繁花,累累硕果”。 文集中有他对文学艺术的热情肯定和褒扬,也有对文化发展中问题的清醒反省和忧思。“为人唯真而已。”他说,“正如古人所言,修辞立其诚,至始至终,我都是诚实的、坦诚的。所有的肯定和批评,都出自我内心的真诚,出自我几十年如一日的文化立场。我始终以无比的真诚对待世界,以无比的热忱对待生活,以无比的坦诚对待内心。以无比的虔诚对待写作。” “也许,我的评论还不够深刻,不够完美,但我勉力用文艺评论的形式记下了上海文化不断前行,不断攀登的行迹。”他这样评价自己。“我希望用自己的文字,借助评论努力呼应时代的精神诉求。我一直期待,在一个匆忙而有点恍惚的年代里,文字能提供一些让心安稳的定力,战胜困难的坚毅。我希望我的评论有热情的火光,能感染读者的心。我希望我的评论有助于观众读者更深入欣赏理解优秀作品的精髓,并从中了解这些年上海文化走过的历程。” 确实,毛时安是上海文化当之无愧的“在场者”,他几乎没有离开过上海和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最前沿。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求学时,他发表在《华东师大学报》《美术》上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关于创作方法“百花齐放”的探讨》,发表在《名作欣赏》上的《文气、文风、文眼——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山水游记赏析》和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上的《〈艺概〉和刘熙载的美学思想》,就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学生的身份在重要的文艺期刊上发表重量文章,在当时堪称“奇迹”。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是当时的上海青年评论家群体的代表性成员,与许子东、吴亮、程德培、蔡翔等同为《上海文学》的重要青年作者。从1989年开始,他又担任《上海文论》副主编和上海市作协副秘书长的职务。在《上海文论》时,他邀请学者陈思和和王晓明主持《重写文学史》栏目。在上海市作协的工作中,他参与为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如巴金、柯灵、胡风、夏衍、陈伯吹、王辛笛等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为中青年作家组织研讨会,组织编辑“大上海小说”丛书。他还在本报组织过一系列热门话题讨论。“上世纪90年代初,文学思潮混乱,文学开始向文化转向,但尚不明确,我在时任《文学报》总编辑郦国义的支持下,开始主持热门话题的讨论,包括影视、广告、建筑,等等,各种热门的大文化话题,持续了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当时,全国有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包括钱谷融先生、贾植芳先生都参与其中。”回忆往事,毛时安历历在目。 1997年,毛时安进入上海市文化局从事创作和管理工作,参与了上海许多重要剧目的创作。他海量地观看了数千场演出,为后来的戏剧评论积累了坚实基础。他主持推进的“海上风艺术文丛”,给那个时代的创作群体留下了群体肖像。丰富的经历,使他熟悉文艺界的各行各业,宏观的文化管理视野和专业的眼光,也让他的评论有独到的风格和深度。直到现在,他还一直奔波忙碌,辗转全国各地,参与全国重大文艺项目的创作、提高、评论工作。 “可以这么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场。在文学活动风云翻卷的时候,在戏剧大浪淘沙的历史转折节点上,我都站在潮头,某种意义上,我参与了一座城市和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尽了个人所能及的推进的力量。我是问心无愧的。”毛时安说。 参与一座城市和一个时代的文化进程的同时,毛时安也和艺术家们结下深厚情谊。他评论的对象,是点燃城市精神焰火的作家、画家、音乐家、戏剧人,他一直在侧耳倾听这座城市的灵魂之声。“一座城市的高度,主要不是她建筑的高度,而是她文化和精神的高度。而上海这座城市最值得引以为傲的,便是她拥有一批执着于人文理想的文化人。” “献给我生活的这座伟大的城市。”在《攀登者》的扉页上,毛时安写道。 “时代的发展节奏实在太快,一定需要有人做记录员。” 记者:在《攀登者》中,读者可以看到你对话剧《商鞅》、昆剧《班昭》、沪剧《挑山女人》、歌剧《白毛女》、交响合唱《启航》、小说《长街行》、电视连续剧《焦裕禄》《平凡的世界》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等等,近二十年来几乎上海所有重要文艺作品和重要活动的评论和分析文章,为读者了解上海的文化状况和发展脉络提供了很好的了解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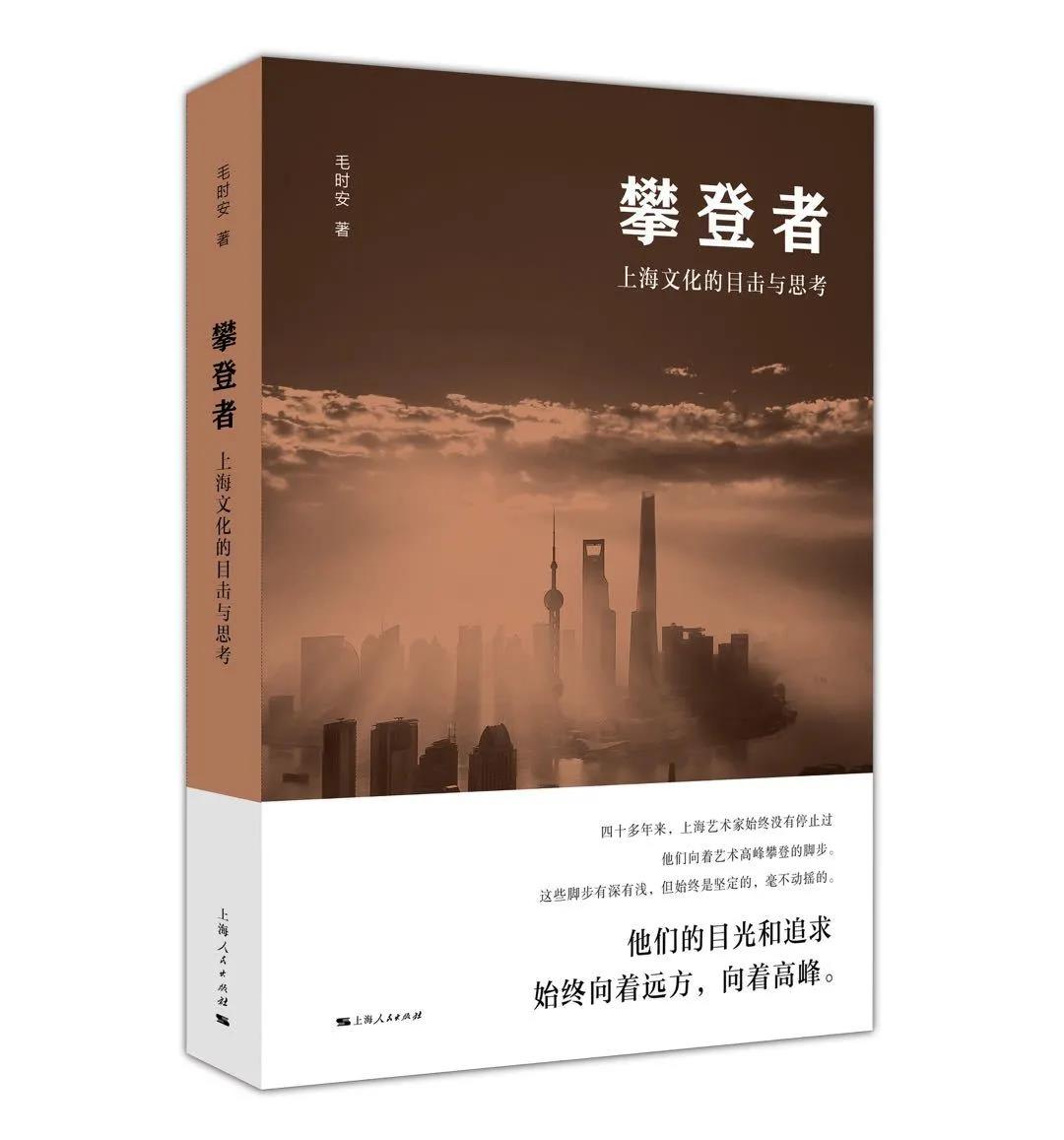 毛时安:可以这么说,《攀登者》是近二十年上海文化、特别是主流文化的一个记录。此外,书中还有我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希望能解决一些问题,有时带有一点担忧。写评论,很重要的一点,“诚”。不管你表达怎样的观点、想法,你确实是经过自己的内心,是自己想表达的内容,而不是别人要你表达的意思。 我和赵长天相知三十多年又在上海市作协共事过八年,我曾经讲过,我说长天,哪怕我们没有能力创作,也要做忠实的记录,因为这个时代的发展节奏实在太快了,一定需要有人来做记录员。上海作家姚克明就曾说,看到我的评论,就相当于看到了上海文化发展的当代历史。而我所有的写作都是繁忙工作之余见缝插针进行的。白天,我是在场的参与者,晚上,我是坚持个人文化立场的思考者。 记者:你对上海文化的观察、记录和评价,其实远远不止二十年。这些年里,你一直活跃在艺术现场。 毛时安: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直到现在,在这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始终是上海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个在场者。从1973年25岁发表美术评论开始到现在,在这条路上,我其实是一路颠簸着走过来的。 我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一型的评论家。比如,在文学上,作家程乃珊最早的作家论是我写的,叫《独特的生活画卷》。史铁生在《作家》上发表小说《奶奶的星星》,我以《星星的魅力——读史铁生〈奶奶的星星〉》为题推介了这篇作品。我还写过上海英年早逝的作家李肇正的长篇评论《平民生活的叙事者》,还和赵长天联手主编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城市生活》。 上世纪80年代初,徐汇区文化馆经常有人组织民间的具有实验性和探索性的画展,我经常去看。1981年时,我就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长篇美术评论。我的戏剧评论也写得很早,1983年就发表了相关作品。 所以我一直在现场。上世纪80年代,我在文学的现场。1997年以后,我开始直接在文艺的现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美术的现场。而艺术到最后是可以共通的。上大学时,我曾跟着徐中玉先生深入学习古代文论。中国传统文论比较灵动。比如,谈及艺术的三个阶段,技、艺、道。在技的层面,以绘画为例,技是技术,西方绘画有素描、透视、色彩,中国画有笔墨、线条,掌握了技术层面之后,将之结合为整体,就成为艺术。艺术之上,还有道。在道的层面上,所有的艺术都是可以打通的。比如,节奏,快慢轻重明暗轻响,音乐、绘画、文学、戏剧,都要有节奏对比。节奏背后,便是艺术家生命气息的投入。 记者:作为评论家,你的评论范围涉及文学、美术、舞台艺术、影视等等,涵盖了文化的大部分领域。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你都不是浅尝辄止,而是能把这些作品不同寻常的特点、以具有审美眼光的论述展示在读者面前。这些年来,你不仅是评论者,更一直是文化实践的积极参与者。 毛时安:因为工作,我从一个偶尔台下看戏的观众成了一个在台下不断看戏的人,也借机深深感受到了艺术家们非比寻常的付出和艰辛。记得1997年9月去文化局报到前,为了提前进入角色,8月16日我先行去上海芭蕾舞团观看《梁祝》的联排。两幕之间休息,就看见主演辛丽丽和演员们一个个拉着把杆大口大口地喘气,满脸挂着晶莹的汗珠,脚背上都是弯弯曲曲像蚯蚓一样凸起的血管,似乎可以听到血液奔腾的声音。排练厅灰色的地胶像一片凝重的土地,你仔细去凝视,就会发现刻在上面的无数的暗光,一道压着一道,那是无数青春的足尖轻盈掠过而深深刻下的生命的印记。 在场给我带来了一种批评的巨大活力,带给我那种被新鲜吸引的、要表达的欲望和冲动。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表达,要写。几十年里,我始终在艺术的现场,而且参与了实际工作。所以,我的在场是深入到肌理深处的在场。 记者:读你的作品,尤其是《敲门者——叩开画家的心灵之门》和舞台艺术评论《野百合的春天在哪里》时,我感觉到你对评论文字的雕琢与注重,许多文章都是文质兼美,读者既能感受到艺术家作品的独特魅力,又被文章本身的华彩所吸引。评论家荣广润说你是一个非常求文采和新意的评论家,“他的评论大都文采盎然,有相当的可读性。如用‘冷思考’‘华丽转身’‘缺血缺钙’来概括表达自己的看法、有思考但毫不晦涩。这些词在经他文章推广后,很快成了大家喜欢的常用词。”评论文章需要文字和内容之间的平衡,你写作时是如何考虑的? 毛时安:有时候,老师说过的一两句话可以受用终身。我始终记得大学时王智量老师和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世界上的事情,说有易,说无难。还有,我们的写作老师说,短文章要俏。一个“俏”,多么概括生动。这些话,我记了一辈子。 为了把文章写好,我还会经常写点散文。文艺评论如何展现汉语写作的文字魅力,文学光彩,和汉语评论的阅读美感,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在这个浑沌多元的世界,我们用艺术,用文字,努力应对时代的精神诉求。以文字为业的人,更应力求以精美的闪烁着思维火光的文字,驱散人心中的暗和寒。所以,我不喜欢把评论写得很刻板,经常写散文练练语感,换换思维。而我的批评文章,成分并不单一,其中既有理性的部分,也有感性的部分,有回忆和感情的部分,也有现场的观感,我希望在批评上能呈现自己的想法。直到现在,我还在一直不停地实践、追求。 “艺术家要按照艺术的规律来反映这个时代向上、向前进程中的复杂性。” 记者:在《攀登者》中,除了对上海近二十年重要作品和重要活动的巡礼,你也敏锐地发现问题,尽可能直言不讳,对不少文艺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而这种问题、立场、意识,同时贯穿在你具体作品的评论中,让这些评论能穿过表面,直抵本质。以戏剧评论为例,荣广润说你的涉及面很宽,但真正关注的重点其实都是戏剧创作的根本性问题。也有评论家说过,这些年里,你始终恪守着自己的文化立场,没有改变。在场之外,你的立场是什么? 毛时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更想做个思想者,而不是评论家。 我最早的戏剧评论评论了话剧《马》,当时我就写到我的一些立场。我一直很警惕过度现代化,警惕过度市场化(产业化)。但我也是最早提出要建设上海文化大市场的人。我一面提出坚持建设文化市场,同时我又坚决反对过度市场化。因为我认为文化最根本的功能是作用于人的灵魂,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过度的现代化、市场化、产业化,对文化发展是不利的。 记者:但现在似乎很少有人这么坚定而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立场了。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文化和市场的相互关系,也已经被大部分人默认。更多的人认为,艺术创作面临的困境,外部环境占有很大的因素。 毛时安:其实,我们可以问一问,人们为什么需要文化?钱能解决文化的所有问题吗?现在,我们一讲艺术问题就讲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固然有它的原因,但全世界的文化都有外部环境问题。虽然问题有轻重,在外部环境的约束下,我们如何发挥? 不是一定要和政治对撞才是艺术,不对撞也可以是艺术。比如,像话剧《艺术》这样的作品,面对着一张白纸,三个男人完全是无中生有,演绎出一出戏剧。写《艺术》会有什么环境问题吗?《哥本哈根》严肃吧,但这个剧作家还写过《糊涂戏班》这样的闹剧。他一方面能写得这么严肃,另一方面又写打闹,就是有大本事。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对文化艺术的要求,关键看我们如何怎么去对待、处理这种要求。我曾经强调,文艺界还是要解放思想,要充分利用现有环境,将艺术才华发挥到极致。我们要面对现实,充分利用现有时代提供的各种可能性,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但现在,我们缺少强行突破的魄力,缺少在强行突破中显示智力的作品。 记者:确实,面对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艺术家同样面临着时代带来的要求。而艺术就是戴着镣铐跳舞。你觉得在当下,艺术家应该如何做,可以如何做? 毛时安:艺术家要动真情,拿出真本领,按照艺术的规律来反映这个时代向上、向前进程中的复杂性。因为时代向上、向前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一马平川的,其中有艰难有曲折,也有内心的彷徨等等复杂的情绪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从这个要求来看,现在的不少作品没有写出人物内心的冲突和忧伤,而只是把他们简单变成了新闻报道的舞台化、银幕化、戏曲化。这些复杂,在不少作品被大量的口号、标语,被豪言壮语消解掉了。 比如,我们要写一个脱贫致富的作品,不能把“脱贫致富”作为口号从头唱到尾,而是要写主角内心的经历。他受到了什么压力?他是怎么从压力中、从个人的思想冲突中走出来的?他和外部环境发生了什么冲突?这些冲突在他内心又引起了什么样的波澜?而不是永远是振臂高呼,永远是一往无前。我们要认识到,这样的作品是没有艺术的有效性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艺术是和日常生活、新闻报道完全不同种类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存在如果不能打动人的心灵和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无效艺术。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避免艺术作为精神产品的无效性,抵制那些对精神、对心灵无效的作品。因为无效作品最后往往抛弃了观众,观众如果失去了对艺术的信任,就很难再与艺术形成良性互动。 记者:你提到的问题和给出的建议,在当下的艺术创作中确实非常具有针对性。但是,在观众和艺术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并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 毛时安:不管在哪种情况下,艺术如果一味地取悦于某种需求,就会产生问题。艺术应该归到艺术本身,不能成为理念和口号的复读机。艺术是一种创造,要有创造性的元素。创造性的元素越大,则艺术性越强。 我们要重新呼吁高度重视艺术规律。艺术是有它的一般规律的。这些一般规律不可违反。艺术是规律的产物,题材创作并不意味着成功。 在时代需要下,当下的艺术创作有必要强调现实主义,强调主旋律,但在强调时代精神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多样化。时代精神不仅表现在主旋律作品中,也表现在其他类型的作品中。比如,在强调婚姻自由、自由恋爱的那个时代,《梁祝》证明了自由恋爱的必要性,《梁祝》就是主旋律。 记者:说到主流创作,在2020这个特殊的年份,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谈到抗疫文艺。在面对重大灾难时,艺术何为? 毛时安:在重大灾难突然降临之际要不要文艺,要不要戏剧,要不要艺术?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通观文学艺术史,在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面临重大灾情、疫情和战争的历史时刻,人类所有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从来就不是冷漠的旁观者,而是坚定不移的在场者和参与者。他们用文艺作品表达发自内心的对苦难中的生命的关切。我们需要戏剧和文艺用人道主义的立场表达我们对生命远去的痛惜和悲悯。 人类的每一次苦难都孕育着艺术的庄严主题,而戏剧是最能承担这一历史主题的艺术样式。需要注意的是,抗疫文艺不是无病呻吟的文人雅事,不是无关痛痒的吟诗作画,而是时代压在艺术家肩头的使命。 抗疫文艺需要风暴过后的沉思默想,需要沉淀,需要升华,需要对巨大历史的把握,和人性幽微的洞察。应该承认,借助自媒体平台海量披露的极具细节和温度、感动了亿万受众的信息,是对艺术家创作的巨大挑战。但是,我相信戏剧人有能力应对这一挑战,充分发挥戏剧独有的强大的在场感,让现在与后来的人们在剧场强大的现场共鸣里,永远记得2020年春天来临之际中国大地这场突发的苦难和抗争。期待在苦难升华后有思想深邃、反思深刻、有精神力度的大作品,期待一座戏剧的纪念碑。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