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末助词的冷热类型
http://www.newdu.com 2025/11/06 04:11:19 《外语教学与研究》 邓思颖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句末助词的有无多寡,由后续语的“冷”、“热”所决定。造成后续语冷热的原因与主体句的强弱有密切关系,即与主体句的屈折成分和韵律特点有关。根据主体句与后续语“此消彼长”原则,主体句越“强”,后续语则越“冷”,越欠缺句末助词;主体句越“弱”,后续语则越“热”,句末助词的数量就会越多。本文以汉语普通话、粤语、英式英语、新加坡英语为例进行分析,结论支持“此消彼长”原则。 关 键 词:句末助词;冷热类型;后续语;联合结构 作者简介:邓思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 基金项目:本研究获得石定栩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成语法的汉语研究与新时代汉语语法理论创新”(18ZDA291)资助。 1.问题的缘起 句末助词位于句末,文献上又称为“语气词”。汉语是一种有句末助词的语言,如普通话的“吗”,位于句子的末尾,表达一定的语气,如(1)。根据句法学的分析,句末助词位于句子的“边缘”位置,正好用来研究句子边缘结构的句法特点,也可以通过这个语法现象比较语言的异同。 (1)他喜欢语言学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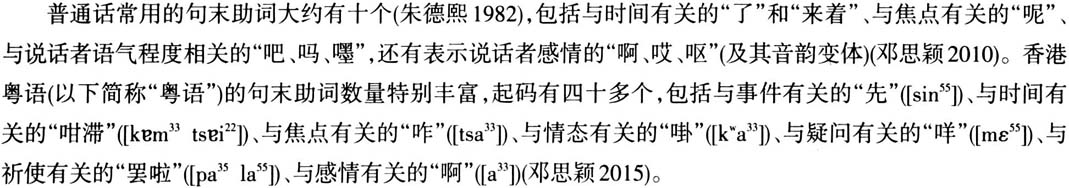 (2)佢睇书先。(‘他先看书。’) (3)佢睇完书咁滞。(‘他快看完书。’) (4)佢睇书咋。(‘他只看书。’) (5)佢睇书啩。(‘他或许看书吧。’) (6)佢睇书咩?(‘难道先看书吗?’) (7)佢睇书罢啦。(‘倒不如叫他看书吧。’) (8)佢睇书啊。(‘他看书啊。’) 一般认为英语①是一种没有句末助词的语言,上述提到的普通话的“吗”、粤语的“啩”,英语中通通都没有。虽然英语句末允许一些成分,类似汉语的句末助词,如(9)中的huh、right、okay,但其性质基本与(10)中的aren’t we相同,属于“尾句”(tag),构成疑问尾句(question tag),不算是句末助词。 (9)We're on the list,huh/right/okay? (10)We're on the list,aren't we? 仅考虑普通话、粤语及英语句末助词的有无多寡,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类型分布(11):粤语的句末助词非常丰富,位于类型光谱的一端;英语没有句末助词,位于类型光谱的另一端;普通话虽然有句末助词,但数量不算多,夹于两种语言之间。 (11)粤语>普通话>英语 为什么有(11)这样的类型光谱?怎样理解粤语、普通话、英语的差异?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方案来解释语言差异,并预测句末助词的语言类型。 2.冷热语言 McLuhan(1964)在媒体研究方面提出过著名的“冷热”论断,把媒体区分为“冷媒体”(cool medium)和“热媒体”(hot medium),前者提供较少信息,观众的参与度较高、较积极,通过参与来补足信息;后者提供较多信息,由于信息较为丰富,因而观众的参与度较低、较为被动。例如,工作坊和对谈往往要求互动,参与较为主动,属于冷媒体;讲座和书本的信息量大,因而听讲座和读书较为被动,参与较少,属于热媒体。 Huang(1984)参考Ross(1982)的说法,借用了McLuhan(1964)有关“冷热”的论断,用于主语省略的类型分析。Huang(1984)认为有两大类语言:“冷语言”(cool language)和“热语言”(hot language),前者需要听者的投入,用推理、语境、知识等手段来理解句子;后者的句子已经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听者可以直接听得到。以主语省略为例,汉语属于冷语言,听者需要通过语境来洞悉被省略的主语所指;英语属于热语言,主语不能省略,每个句子早已提供了完备的信息。至于西班牙语这类语言,主语可以被省略,听者需要一定程度的参与,但不必通过语境,而是可以通过一致关系(agreement)所表示的信息把省略的主语复原,属于“中热语言”(medium-hot language)。 本文认为,冷、热、中热等概念也同样适用于句末助词的类型现象。上述(11)中三种类型的语言,可以分别描述为冷语言、热语言、中热语言。粤语属于热语言,句末助词数量多,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语义语用信息,听者可以通过句末助词准确理解;英语属于冷语言,没有句末助词,原本由句末助词所表达的内容需要听者通过别的方式来理解;普通话属于中热语言,有少量的句末助词,提供适量的信息,然而,相对粤语而言,普通话所缺乏的句末助词,听者也需通过别的方式来理解。根据句末助词的冷热描述,(11)的左端是热语言,右端是冷语言。 3.后续语的冷热 把冷热的概念借用来描述(11)的句末助词语言类型,区分为冷语言、中热语言、热语言三种,形象地描述了听者与句末助词的关系,有一定的概括性。粤语句末助词丰富,听者的参与度低;英语缺乏句末助词,听者要用别的方式参与复原原本句末助词所表达的信息;普通话有句末助词,但数量不多。句末助词的冷热论断为了解这些现象踏出了一小步。不过,对于这种语言差异的现象,我们仍然会追问:为什么粤语是热语言,英语是冷语言?句末助词的冷热由什么因素来决定? 首先,为了方便讨论,我们把句子划分为两个部分:“主体句”和“后续语”(Luke 2012;陆镜光2004a,b;邓思颖2018)。主体句和后续语两者通过一个无声的连词“  ”连接起来,构成联合结构(Tang 2015;邓思颖2016a,b,c,e,2018),如(12)所示。 ”连接起来,构成联合结构(Tang 2015;邓思颖2016a,b,c,e,2018),如(12)所示。(12)[主体句]  [后续语] [后续语]假设句末助词来自原本位于后续语的谓词(邓思颖2016d),随着历时演变,后续语的谓词(或与谓词相关的成分)经过语法化后成为句末助词,并入主体句之内,成为虚词。较为典型的例子如普通话的“了”(来自动词“了”)、“来着”(来自动词“来”)、“吧”(来自动词“罢”)、“吗”(与否定谓语的否定词有关)等,以及粤语的“啩”(来自动词“估”)、“  ”(来自动词“话”)。根据这个假设,我们认为粤语的后续语非常“热”,有数量较多的成分,表达了丰富的信息。后续语越“热”,句末助词的数量就越多。 ”(来自动词“话”)。根据这个假设,我们认为粤语的后续语非常“热”,有数量较多的成分,表达了丰富的信息。后续语越“热”,句末助词的数量就越多。后续语在粤语中较为丰富已是一个显著的现象(Luke 2012)。粤语不仅有较多的句末助词,所谓“延伸句”(或称为“倒装句、变式、易位句”等)也特别丰富,好像比普通话更有弹性,如(13)的后续语是主语“我”,(14)的后续语是主语“我”加状语“寻日”(‘昨天’),(15)的后续语是“我寻日交”(‘我昨天交’)。这个听起来较为“啰嗦”的后续语就是起到“衬托”的作用,凸显了前面主体句的重要,加强了说话者的语气,带出一种强调的效果(陈冠健2016)。像(15)这种后续语,粤语可以接受,反倒在普通话中并不常见(邓思颖2018)。从后续语的复杂性可以窥探后续语的冷热:粤语后续语比普通话为“热”。正因如此,粤语的句末助词就比普通话的多。 (13)我寻日交论文啊,我。(‘我昨天交论文啊,我。’) (14)我寻日交论文啊,我寻日。(‘我昨天交论文啊,我昨天。’) (15)我寻日交论文啊,我寻日交。(‘我昨天交论文啊,我昨天交。’) 事实上,上述(13)-(15)的例子在英语中都不能说,如(16)。我们可以总结认为英语的后续语是“冷”的,欠缺了形成句末助词的源头,因而英语缺乏句末助词。语言的冷热与后续语的冷热有关,(11)的类型分布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解释。 (16)Yesterday I submitted my thesis。*I/*yesterday I/*yesterday I submitted. 4.主体句的强弱 根据上文的讨论,粤语的后续语是“热”,属于“热语言”,普通话的后续语是“中热”,属于“中热语言”,英语的后续语是“冷”,属于“冷语言”,正好说明了(11)的类型分布。基于这个冷热差异,我们仍可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三种语言的后续语有冷热之别?本文假设后续语的冷热与主体句的强弱有关:主体句“强”,则后续语“冷”;主体句“弱”,则后续语“热”。这个假设的原意是“强”的主体句能自给自足,不需要借助后续语帮忙,因而后续语所表达的信息少,形成“冷”现象;至于“弱”的主体句,欠缺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往往需要通过后续语来补足,因而后续语的地位显得较为重要,形成“热”现象。 本文认为主体句的强弱可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定义:一是屈折成分,二是韵律特征。我们认为凡有丰富屈折成分、有丰富韵律特征的主体句,都是“强”的主体句,都能自给自足,不需要后续语帮忙,导致后续语的“冷”;凡屈折成分贫乏、韵律特征贫乏的主体句,都是“弱”的主体句,所失去的信息需依靠后续语帮忙,造就了后续语的“热”。 就屈折成分而言,英语有较为丰富的屈折成分,如(17)中表示一致关系的-s,(18)中表示过去时的-ed;至于汉语普通话和粤语,都缺乏屈折成分。以普通话为例,(19)中的“喜欢”和(20)中的“跳舞”都没有任何屈折成分,这是众所周知而没有争议的事实。 (17)He loves linguistics. (18)He danced yesterday. (19)他喜欢语言学。 (20)他昨天跳舞。 至于韵律特征方面,英语属于重音定时(stress-timing)语言(Abercrombie 1967;Warner & Arai 2001等)。这种分析争议性不大,也是学界的共识。至于普通话和粤语,虽然不少意见认为普通话原则上属于音节定时(syllable-timing)语言(Benton et al.2007),但Mok(2009)却发现粤语的音节定时比普通话更强,即粤语的音节定时更长。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普通话有轻声,粤语没有。普通话的轻声形成非重读的音节,呈现重音定时语言的效果。假如以重音作为衡量韵律特征丰富程度的标准,英语属于韵律特征丰富的语言,普通话次之,而粤语最为贫乏。 综合屈折成分和韵律特征这两方面因素,英语的屈折成分和韵律特征都最丰富,普通话虽然没有屈折成分,但呈现出一些重音定时语言的效果,有较为丰富的韵律特征,而粤语既没有屈折成分,也没有丰富的韵律特征。由此观之,英语的主体句属于“强”,能自给自足,不需要后续语,后续语是“冷”,因而产生不了句末助词;粤语的主体句属于“弱”,需要后续语的补足,形成较为发达的后续语,“热”的后续语提供了形成句末助词的土壤,造就了粤语是一种句末助词丰富的语言;普通话的主体句不算“强”也不算“弱”,这种不强不弱的现象也就需要一些不冷不热的后续语,形成“中热”,所产生的句末助词在数量上也不如粤语多。这些现象正好说明了(11)的类型分布,也为(11)的类型分布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主体句的强弱由屈折成分和韵律特征来定义呢?Rizzi(1997)把句子结构区分为“词汇层次”(lexical layer)、“屈折层次”(inflectional layer)和“标句层次”(complementizer layer)三层。根据Rizzi(同上)的划分,本文认为屈折成分主要与句法结构的所谓屈折层次有关,包括体貌、时态、一致关系等成分,在句法上围绕时间词短语TP这个层次。通过轻重音等韵律特征所表达的功能,尤其是与言语行为(speech act)有关的韵律特征,与所谓标句层次有关,位处句子最高的位置,如标句词短语CP②。 根据句法分布和语义考虑,汉语句末助词可以划分为几个大类,如时间、焦点、程度、感情等(邓思颖2010)。这几类句末助词能与主体句的句法层级联系起来:时间类在屈折层次,而焦点、程度、感情三类位于标句层次。韵律与焦点、程度、感情句末助词的关系基本上得到Wakefield(2010)研究的支持。他研究部分属于焦点类和程度类的粤语句末助词,发现这些句末助词与英语的语调有关,尤其是与音高能对应起来。由此观之,把语调等韵律特征的强弱与句末助词的多寡联系起来并非不可能,甚至可以获得更多证据的支持(Zhang 2014;冯胜利2015等)。 简单来说,假如某一语言的屈折层次缺乏屈折成分,而标句层次的言语行为并非纯粹依赖韵律手段,主体句都会标签为“弱”。主体句“弱”,则后续语“热”,作为补充,最终形成较为丰富的句末助词。本文认为,粤语就属于这种语言,屈折层次和标句层次都很“弱”,需要比较“热”的后续语,因而造就了形成丰富句末助词的条件;反观英语,屈折层次和标句层次都很“强”,基本上能自给自足,后续语的作用显得不太必要,也就缺乏形成句末助词的需要。 5.中热语言的旁证——新加坡英语 普通话的主体句欠缺屈折成分,但有若干韵律特征,算是不强不弱的语言,也就有“中热”的后续语,产生出为数不多的句末助词。还有一种语言与普通话有点相似,都属于不强不弱,那就是新加坡英语(Singaporean English)。新加坡英语主体句不强不弱的特点与普通话相似,但不完全一样:主体句有一定的屈折成分,比普通话强,但比英式英语弱③。以表过去时的屈折成分为例,新加坡英语可以有-ed的出现,如(21),这有异于普通话;但时态屈折成分有时也可省略④,如(22)(Platt & Weber 1980),这有异于英式英语。 (21)He accepted in the end. (22)He talk so long,never stop,I ask him also never. 至于韵律方面,新加坡英语有一定的韵律特征,是一种处于重音定时与音节定时之间的语言(Grabe & Low 2002)。换句话说,新加坡英语的韵律特征比粤语稍强,但比英式英语稍弱。既然新加坡英语属于不强不弱的语言,我们预测后续语呈现“中热”的特点,也应该有一定数量的句末助词。这个预测,正符合我们所看到的语言事实。 新加坡英语后续语的冷热现象很值得注意。文献早已观察到新加坡英语的后续语比英式英语丰富,(23)中位于句末的already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特征(Kwan-Terry 1989;Bao 1995;Hiramoto 2015等),也可当作后续语的一种,不见于英式英语。不过,新加坡英语后续语远远比不上粤语的“热”,像(23)中的already,其使用范围仍有一定局限,欠缺像(15)那样的延伸句。由此可见,新加坡英语的后续语所呈现的现象算是“中热”,在类型上有异于英式英语,也异于粤语。 (23)I cannot go inside already. 由于新加坡英语有“中热”的后续语,我们预计应该有句末助词出现的可能性。事实上,新加坡英语有大约十一个句末助词,如(24)的la、(25)的a、(26)的what(Gupta 1992),数量上与普通话接近,应该属于“中热”的语言。 (24)Ask your mummy first la. (25)You didn't go school on Sunday a? (26)I never-I never ever draw what. 新加坡英语主体句所呈现的屈折成分和韵律特征,属于不强不弱,因此后续语有“中热”的特点也不足为奇。为了补足主体句的不强不弱,因而形成一定数量的句末助词,使新加坡英语有别于英式英语,也有别于粤语。 如果把新加坡英语加进来,上述(11)的类型分布可以补充为(27)。原本的“英语”改称为“英式英语”,也包括美式英语。粤语的后续语是“热”,主体句属于“弱”;英式英语的后续语是“冷”,主体句属于“强”;普通话和新加坡英语的后续语是“中热”,主体句属于不强不弱。按照句末助词的有无多寡,人类语言起码可以划分为(27)中的三类语言,最左端是“热语言”,最右端是“冷语言”,中间的是“中热语言”。这三类语言可通过后续语的冷热来描述,而后续语的冷热则由主体句的强弱来决定,即由屈折成分和韵律特征来决定。 (27)粤语>普通话、新加坡英语>英式英语 6.结语:此消彼长 根据本文的讨论,句末助词的有无多寡有一定的原因,那就是由后续语的冷热所决定。事实上,后续语的冷热也只是客观的描述而已。本文认为,造成后续语冷热的原因与主体句的强弱有密切关系,即与主体句的屈折成分和韵律特征有关。后续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主体句的补充。如果主体句能自给自足,那就不需要后续语;如果主体句的形式和内容较为贫乏,那就需要后续语的帮忙。换句话说,主体句越“强”,则后续语越“冷”,形成句末助词的土壤欠丰,英式英语就属于这种语言;主体句越“弱”,则后续语越“热”,句末助词的数量就越丰富,粤语就是这一种语言;主体句属于不强不弱,则后续语呈现“中热”现象,虽然有形成句末助词的可能,但数量不会多,普通话和新加坡英语就属于这一种语言。 后续语用作补充主体句,主体句的信息丰富,后续语的作用就减弱。主体句与后续语这种微妙的关系,一多一少,一强一弱,有一种张力,大致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主体句强弱和后续语冷热的关系,可称之为“此消彼长”⑤,总结于下: (28)主体句与后续语的此消彼长: 主体句越“强”,则后续语越“冷”;主体句越“弱”,则后续语越“热”。 根据(28)的“此消彼长”原则,句末助词的有无多寡是主体句与后续语处于平衡关系的结果,取决于主体句的强弱因素。这个原则仍然有待更多的语言验证。假如我们能通过主体句的形式特征对句末助词的有 无多寡做准确的预测,那应该能为语言类型描绘出一个更详细的蓝图,也能说明语言习得的一些问题。 本文构思受益于2017-2018学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访学。部分内容曾在以下专题讲座报告过: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及哲学系(2018年4月)、纽约大学语言学系(2018年4月)、哈佛大学语言学系(2018年4月)、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学院(2018年5月)、马来亚大学语言及语言学学院(2018年6月)、马来西亚国立大学语言研究及语言学系(2018年6月)、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语言、语言学及文学系(2019年4月)、中正大学语言学研究所(2019年5月);也曾在以下学术研讨会报告过:第三十届北美汉语语言学会议(俄亥俄州立大学,2018年3月)、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26届年会(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2018年5月)、第一届粤语语言学论坛(香港中文大学,2018年5月)、语言句法分析性与语法参数理论国际研讨会(北京语言大学,2018年6月)、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成立仪式暨语言学前沿国际论坛(北京语言大学,2018年10月)、首届理论语言学国际前沿课题高端研讨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9年3月)、第二届南方汉语方言研讨会(广州体育学院,2019年7月)。与会者建设性的意见对改进本文很有帮助,特此致谢。 ①如无特别说明,“英语”一般指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 ②按照冯胜利(2017)的分析,语调(或称为“句调”)属于“标句词短语韵律”,与句法结构最高的层次有关。 ③为方便行文,与新加坡英语比较时,本文以“英式英语”一词涵盖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 ④关于新加坡英语时态屈折成分的省略问题,详见Alsagoff(2001),Deterding(2003),Fong(2004)、Wee(2004)、Gut(2009)等的讨论和分析。 ⑤黄正德教授(个人通讯)向笔者指出,这种所谓“此消彼长”的现象,与“叶斯柏森循环”(Jespersen's Cycle)相似,是语言历史演变的结果,也许是考虑到句法结构各部分的平衡关系而形成的。 原文参考文献: [1]Abercrombie,D.1967.Elements of General Phonetics[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Alsagoff,L.2001.Tense and aspect in Singapore English[A].In V.Ooi(ed.).Evolving Identities:The English Languag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C].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79-88. [3]Bao,Z.M.1995.Already in Singapore English[J].World Englishes 14:181-188. [4]Benton,M.,L.Dockendorf,W.Jin,Y.Liu & J.Edmondson.2007.The continuum of speech rhythm:Computational testing of speech rhythm of large corpora from natural Chinese and English speech[A].In J.Trouvain(ed.).Proceedings of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netic Sciences ICPHS X VI[C].Saarbrücken:Saarland University.1269-1272. [5]Deterding,D.2003.Tenses and will/would in a corpus of Singapore English[A].In D.Deterding,A.Brown & L.Ling(eds.).English in Singapore:Research on Grammar[C].Singapore:McGraw-Hill.31-38. [6]Fong,V.2004.The verbal cluster[A].In L.Lim(ed.).Singapore English:A Grammatical Description[C].Amsterdam:John Benjamins.75-104. [7]Grabe,E.& E.Low.2002.Durational variability in speech and the rhythm class hypothesis[A].In C.Gussenhoven & N.Warner(eds.).Laboratory Phonology Ⅶ[C].Berlin:Mouton de Gruyter.515-546. [8]Gupta,A.1992.The pragmatic particles of Singapore Colloquial English[J].Journal of Pragmatics 18:31-57. [9]Gut,U.2009.Past tense marking in Singapore English verbs[J].English World-Wide 30:262-277. [10]Hiramoto,M.2015.Sentence-final adverbs in Singapore English and Hong Kong English[J].World Englishes 34:636-653. [11]Huang,C.-T.James.1984.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J].Linguistic Inquiry 15:531-574. [12]Kwan-Terry,A.1989.The specification of stage by a child learning English and Cantonese simultaneously[A].In H.Dechert & M.Raupach(eds.).Interlingual Processes[C].Tübingen:Gunter Narr Verlag.33-48. [13]Luke,K.-K.2012.Dislocation or afterthought?—A conversation analytic account of incremental sentences in Chinese[J].Discourse Processes 49:338-365. [14]McLuhan,M.1964.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M].New York:McGraw-Hill. [15]Mok,P.2009.On the syllable-timing of Cantonese and Beijing Mandarin[J].Chinese Journal of Phonetics 2:148-154. [16]Platt,J.& H.Weber.1980.English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Status,Features,Functions[M].Oxford:OUP. [17]Rizzi,L.1997.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A].In L.Haegeman(ed.).Elements of Grammar[C].Dordrecht:Kluwer.281-337. [18]Ross,J.1982.Pronoun deleting processes in German[R].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San Diego,California,U.S.A.,December 1982. [19]Tang,S.-W.2015.A generalized syntactic schema for utterance particles in Chinese[J].Lingua Sinica 1:1-23. [20]Wakefield,J.2010.The English Equivalents of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A Contrastive Analysis[D].Ph.D.Dissertation.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1]Warner,N.& T.Arai.2001.Japanese mora-timing:A review[J].Phonetica 58:1-25. [22]Wee,L.2004.Singapore English:Morphology and syntax[A].In B.Kortmann,K.Burridge,R.Mesthrie,E.Schneider & C.Upton(eds.).A Handbook of Varieties of English Vol.2:Morphology and Syntax[C].Berlin:Mouton de Gruyter.1058-1072. [23]Zhang,L.2014.Segmentless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antonese:An experimental study[J].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35:47-60. [24]陈冠健,2016,粤语后置重复句法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香港中文大学. [25]邓思颖,2010,《形式汉语句法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6]邓思颖,2015,《粤语语法讲义》[M]。香港:商务印书馆. [27]邓思颖,2016a,英语和汉语疑问尾句的句法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1):18-25. [28]邓思颖,2016b,汉语助词研究的两个问题[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420-423. [29]邓思颖,2016c,制图理论与助词的联合结构说[J],《语言研究集刊》(16):1-10. [30]邓思颖,2016d,汉语语气词的谓语功能[A]。载丁邦新、张洪年、邓思颖、钱志安(编),《汉语研究的新貌:方言、语法与文献——献给余霭芹教授》[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5-24. [31]邓思颖,2016e,反复问句的联合结构分析[J],《现代外语》(6):742-750. [32]邓思颖,2018,延伸句的句法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3):48-57. [33]冯胜利,2015,声调、语调与汉语的句末语气[J],《语言学论丛》(51):51-77. [34]冯胜利,2017,汉语句法、重音、语调相互作用的语法效应[J],《语言教学与研究》(3):1-17. [35]陆镜光,2004a,说“延伸句”[A]。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编辑部(编),《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学术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39-48. [36]陆镜光,2004b,延伸句的跨语言对比[J],《语言教学与研究》(6):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