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局开放的历史 现代性通常被认为与进步的线性历史这一启蒙思想之间有着密切关系,针对这种观点最为著名的批判来自本雅明。现代主义对规范性抱有怀疑,同样的,它关注的不是未来,而是当下,这种历史观念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开放“民主”地阅读历史的方式。在这种视角中,民主并不是一种可以反映出历史规律的新理念,而是一条不确定的、没有清晰结果或终极目标的道路。在一篇写于辛亥革命结束十四年的文章中,鲁迅否认民主会带来任何形式的线性进步: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43) 写于此文四年前的《阿Q正传》反映了鲁迅对探究历史所下的决心,而他所采取的视角是祛魅式的,而不是甘心失败或者反对民主。 鲁迅对革命的描绘可以用文中的四个概念来架构起来,而这四个概念恰好同阿Q对革命本质的误解相反。第一个概念,是阿Q对革命和造反(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的混淆。阿Q对在城里见到革命党被砍头而兴奋不已:“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在后来做的梦中,他将革命党描绘成身着白盔白甲的反清复明者(这是当时农民的普遍误解)。对阿Q来说,误解本身并没有改变,然而其价值却被颠倒了过来:革命还是造反,但现在好像变成了一场狂欢,而在未庄的主街上行走的阿Q则将社会翻了个底朝天:“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狂喜之中他失去了控制,开始嚷道:“造反了!造反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阿Q并没有什么政治计划:对他来说革命就是强奸、抢劫以及新一轮的压迫——一场纯粹的暴力发泄,以及对任何在旧制度中压迫过他的人的报复,而其结果只是将等级制度颠倒过来而非废除它,只是另一场在轮回式的历史中将被遗忘的农民起义。 的确,鲁迅似乎想说,要冲破传统的轮转似乎是不可能的,这在另外两个概念中得到了印证。做完那个梦之后,阿Q以一种真正儒家信徒的方式,决定向作为新掌权者的革命党“投降”。同样的,“假洋鬼子”和村里的秀才也已经用儒家的“咸与维新”来证实自己已转投革命党了。就在阿Q去尼姑庵的菜园子“革命”之前不久,他俩已经把此地扫荡过一遍了。然而事实上,当假洋鬼子不准阿Q参加革命时,阿Q用以反对的是一个从传统刑罚中获得灵感的更为陈旧的词汇:“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对鲁迅来说,“满门抄斩”正是中国古老政治中最残酷行为的象征。在《小杂感》中,他将其(他在此用了“族诛”一词)和秦朝联系起来,并引用了这个典故:“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44)因此,对鲁迅来说,让阿Q用这个词,并不仅仅暗示着历史的停滞,更是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当群众——在此他们被阿Q所代表——获得了权力时,民主化也许将产生一种特别恐怖的、混杂着现代和古代形式暴力的合体(有学者曾提到过,阿Q在街上游荡,鼓动强奸和抢劫的情形,难免会让今天的读者想起“文化大革命”)。在一篇讲述自己如何写小说的文章中,鲁迅补充道:“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45)鲁迅运用了一个一点也不现实主义,而更像是农村社戏的梦境场景,来强调仅仅将权力给予“大众”,是无法直接生产出“民主”的;而关于如何培养有民主意识公民的问题,则还是悬而未决。 那么是否可以说,鲁迅对历史的理解完全是传统的、“反现代”的呢? 王德威认为有这个可能,他将鲁迅在1906年看到的那张中国间谍被砍头的幻灯片,与“让现实成为现实的那种意义体系的残断状况”,建立起一种对应。(46)在《阿Q正传》中,看客因为阿Q是被现代的(西方的)枪炮所击毙而颇感失望。他将此与沈从文的《新与旧》的结局进行比较,微妙地指出,对沈来说“回忆(re-membering)”可以是对“肢解(dis-membering)”的一种反抗。然而,这个类比似乎不完全有说服力:肢解罪犯是古代,而不是现代社会的特质;而阿Q恰恰没有被“肢解”。这样看来,怀旧对鲁迅来说似乎并不是答案。鲁迅的小说并没有试图重建一个线性的时间观,从而使读者在传统中找到安慰。在一个后革命以及原始民主的空间内,作品拒绝表露出任何明确的姿态,它没有什么“回忆”(怀旧)的意义要提供给读者,也没有对光明未来的任何许诺。共产党的批评家起初攻击《阿Q正传》,后来又试图将它描述为一个关于革命和历史线性进步的“杰作”。而事实恰恰相反,《阿Q正传》的主角可以说始终被困在民主时间的过渡中。 这种手段,将历史构成一个过去和未来互相交织重叠的犹豫不决的时刻,也呈现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中。这部作品讲述的是政治现代性在中国和欧洲的嬗变。(47)几乎可以肯定该小说写于1917年的3月,俄国二月革命结束仅数周之后,并且也是在中国的辛亥革命结束后六年之内。卡夫卡在他1911年11月9日所写的日记上,以发生在布拉格的一个革命之梦的方式,把辛亥革命标注了下来。小说的片段首次发表于1919年9月24日布拉格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周刊《自我防御》上。当时《自我防御》的主要内容是有关“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如马丁?布伯和更富有政治倾向的运动家——如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之间的争论。卡夫卡选择了这家杂志,也说明了传统的东欧犹太文化这一主题是如何可能影响到卡夫卡对中国主题的重新诠释,并让两者结合在一起。 关于卡夫卡对一个帝国如何蜕变为现代国家过程所作的描述,本雅明曾作过最有洞察力的分析:他认为“那些史前时代便存在的暴力占据着卡夫卡的作品;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暴力也属于我们这个世间”(48)。在本雅明看来,卡夫卡自己并不完全理解这些暴力:“他只有在那面由史前世界举起、并显出罪恶原形的镜子中,以审判的形式窥见未来。”(49)这便是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描绘出来的世界根本的双重性:在表面上现代化的、以审判、法律和不断扩张的专家官僚体系所组成的结构中,总还保留了旧世界的痕迹——等级制度,超验宗教原则以及在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中存在的罪恶。 在《中国长城建造时》中,这种双重性表现在两个例子中:一边是巴别塔和长城,而另一边是皇帝和领导组。在这两个例子里,前者(塔和皇帝)象征着超验神圣:虽然这一神圣似乎并没有真实的存在,但一种神圣的灵光却继续笼罩着代表现代形式权力的长城和领导组。作品中的长城虽然被称为一座新的巴别塔,实际上建造它的过程,却仅仅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在臣民中招募劳动力的方式,而且在某种神圣合法性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工程。与叙述者一开始宣称的“中国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50)。相反,工程永远没有结束,而且可能永远无法结束;墙身上满是窟窿和豁口,这跟官方所称的它的存在是为了保卫国家的边境免遭“北方诸族”入侵的说法,背道而驰。 然而,这个工程却在调动着庞大的人群。叙述者为这种动员辩护时所用说辞,直接来自于一种古老的、基于血缘的国家叙事:“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他们国家是多么辽阔、多么富庶、多么美丽、多么可爱。每个国民都是同胞手足,就是为了他们,大家在建筑一道防御的长城,而同胞们也倾其所有,终身报答。团结!团结!肩并着肩,结成民众的连环,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是要欢畅地奔腾,通过无限广大的中国澎湃回环。”(51)这残破而无用的城墙——这些工人们为此甚至付出了他们的生命——被叙述者解释为皇帝膝下的臣民们血肉相连地团结的象征:卡夫卡直接从他那个年代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借用了人民作为国家鲜血这个比喻,而他所接触到的这些话语既有德国的也有犹太的版本,比如说在布伯的文章中。(52)这样一来,长城便象征着丧失了垂直和超验的存在合法性(皇帝)的现代国家,是如何利用一个不完美的水平投影(长城),来对普通民众的生命实施某种形式的控制,不让他们充分获得民主化所应该赋予他们的权力。这种暴力的合法性来自于一个神圣的概念,那就是皇帝是政体的化身;而卡夫卡描绘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民族”怎样可以为这种暴力替代皇帝提供一个(内在性的)合法性来源。修建长城实际上是一个借口,通过展示这一点,卡夫卡揭露了民族主义话语的神话化以及它对其臣民的欺瞒。他展现了这个有关神圣帝国的神话是如何从巴别塔神话的残留中浮现出来,在一番操控之下成为维持独裁政府统治的手段,从而生产出现代民族主义的语言:神话和历史在古老和现代主题的交合中重叠在一起。 同样的解读可以用在皇帝和“领导组”这个双重形象上,而后者才是真正的权力行使者:“在领导集团的密室里——它位于何处以及里面坐着谁,我问过的人谁也不知道,现在仍不知道。大概人的所有想法和愿望都在那间密室里盘旋,而人的所有目标和实现都在反向盘旋。透过窗户,神界的余辉洒落在领导集团所描绘的各种规划的手上。”领导组的权力是现代的,因为它基于代表性(“人的所有想法和愿望”)和科技能力,然而它却始终要蒙受“神界的余辉”,这一从传统遗留下来的合法性的恩泽。同样,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城墙或者国界的建造也要从其继承来的血缘话语中,或如卡夫卡所言,从古老的国家表象中,获得自然合法性的“余辉”。于是,在故事的核心阶段,当奄奄一息的皇帝向他的臣民派遣了一名使者时,他将一枚象征着皇室的太阳标记别在他的外衣上,而使者不出所料根本没办法来到远在天边的臣民中间,而是被困在无穷无尽的院落、台阶以及那一群群隔在皇帝与臣民间的官员之中。于是,权力的标记仍然属于宫廷,或者是在“领导组”手里;这样一来,普通人则永远也得不到权力,而只能幻想它的存在。 吉勒?德勒兹和菲力克斯?瓜塔里指出了卡夫卡的中国世界里奇特的历史性:“现代官僚制度自然而然地诞生于古老的形式内部,它通过赋予这些形式一个完美的当代功能而变成它们、使它们重生。这也是为何卡夫卡在他大部分的作品中描绘的那两个建筑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是并存的,它们在彼此之中发生,并且,那是在现代世界:它们既是天国等级制度的筑坛,又是连绵不绝的、几乎是地下的办公室。”(53)正如本雅明所言,这种暧昧的、表现为“祖先的世界”和“官僚的世界”重叠的历史性,也是《审判》和《城堡》的主题。(54)在《审判》中,现代法律程序所保证的真正的“无罪判决”,被无限的“延迟”和办公室的不断横向延伸代替了。在《城堡》中,“K”希望自己个人的权利受到城堡的认可,而城堡的回应是一种妥协:承诺给他一个乡村学校清洁工的职位——它像现代福利国家那样,用一种传统的家长式的姿态反驳K对个人权利的要求。(55)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看到现代机构解放性的潜能是如何被牢牢地束缚在新兴官僚体系之下——它的背后,依旧是那些古老的规则。没有任何历史定律能够保证现代性的承诺都将被实现,因为现代和古老的权力形式始终并存;反之,民主化有时也只意味着一种更加现代的宣传手段代替了较为陈旧的那一种。考虑到小说发表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语境之下,这种祛魅的、以不确定的态度看待历史的观点,也许可以被看作是卡夫卡对他那个年代的中国和欧洲社会民主化的一种理解。(56)这种将各种时态重叠在一起的历史观并不相信所谓历史命运和进步观念。这倒是与福柯或德勒兹的看法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民主的出现,往往是在权力架构更替的间隙,而不是某种启蒙理想以前进的方式获得实现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卡夫卡和鲁迅也有着同样的历史观,而这种历史观可以被称作是现代主义的标准:奋起反抗的个人,企图从传统的轮回历史观和与之相伴的超验的等级制度中,解脱出来;然而他却并未因此得到任何决定性的历史启示。(57)这两部作品没有“结果”,也得不出什么历史的结论;事实是,各种历史的断层重叠在一起。从反思的层面上来看,这将它们和民主化的“主叙事”区分了开来,也将它们和线性的时间观——这一以现代性为潜台词而饱受批评的观念——区分开来:这两部作品强调的是民主化总是与一种“开放式”的历史观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历史观允许读者去形成自己的观点,并找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 公共空间 文学作品的民主本质如何在社会现实中得到体现?文学真正的“民主”实践需要一种民主的交际性框架(democratic pragmatics),在这种交往形态中,读者需要扮演起重要角色。和“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浪漫主义作家也很少对自己代表读者及其经验的权威有何疑问:作家再现(represent)读者,同时也是代表读者,这样的关系直接明了。在本文看来,现代主义所关注的核心恰恰相反,对作家能否“代表”读者产生怀疑。作家在作品中,使虚构再现的行为不仅变得可疑(这种写作方式本身未必是一个创新),而且将虚构的再现制度化,使它作为表达质疑的空间。民主同样可以理解为—个不断对其自身的政治代表性的质疑的体制化。皮埃尔?罗森瓦隆认为,不可能将法国大革命或者是美国宪法采用“民主制度”等同于人们在某些关键问题——民众主权的本质及其合法性,代表民众主权的方式——已达成了共识。更确切地说,在勒夫看来,这一“民主制度”在当时允许了公共空间的体制化,并赋予了上述的议题(民众主权,民选)一个开放的、具有合法性的辩论空间。(58)同样,本文所探讨的文本对自己能否代表读者的质疑,通过系统化和体制化也变成了这些文本的现代主义特质。 到目前为止,本文分析的这些作品所处理的,便是代表/再现的问题。作者们将读者或观众对他们自己的解读这一视角收入文中,用这种方式来向作者为读者“代言”的权威提出质疑。在《四川好人》中,布莱希特不无讽刺地模仿了观众对文学作品“期盼中的大结局”的翘首以待。布莱希特并没有创造出一个完整的、封闭的文本以让读者获得个人和私密的享受,而是试图打破作品和社会之间的隔阂。(59)构建这种形式的不完整性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开一个讨论和竞争的空间。在最后一幕中,布莱希特戏弄观众们的期待,他戏仿传统大结局的“崇高”美学元素,戏谑巴洛克的、浪漫主义的,以及“瓦格纳式的”剧场风格。他引用佩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Pedro Calderon de la Barca)的“人生如梦”的手法,神明们最后奇迹般地出现从而解决了所有难题,并告诫沈黛:“要紧的是做好人”。他们向其他角色保证,这样一来,等待他们的将一定会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保证人间的问题皆可以得到美学上的解决:“我们坚信,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我们的好人是能够找到出路的。”可是,剧终的时候,神明们却飘荡在玫瑰色祥云上,唱着三重唱渐渐消失了,还为自己只是世界剧场的“旁观者而已”而感到自豪,留下沈黛的哀求无人应答。因此,神明们被表现为布莱希特所称的“享乐型”观众(culinary spectator)的镜像,他们从演出中获得娱乐后,便和大家一起说:“让我们回到天上去吧。这小小世界束缚我们太紧。你们的快乐使我们高兴,你们的痛苦让我们忧伤。”布莱希特似乎想要证明,虚构的巴洛克式大团圆呈现的完整性,所做的是鼓励观众走进戏院,从别人的痛苦中获得乐趣,然后高高兴兴地回家。然而,在这里,大结局的完整性被摧毁了。当愤怒的人们还在敲打着门板,神明们却抛弃了绝望中的沈黛——她必须抚养孩子,努力生存,并且还要做个好人。而对这些困境,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用玫瑰色的光线和音乐一笔带过。沈黛被象征性地抛给了观众,她必须自己去处理现实世界的纷繁芜杂。 故事的不完整性在剧末的收场白中再一次得到了强调:一名演员走到已经拉下的帷幕前,对着观众们表达了遗憾:“幕布拉上了,问题才暴露出来”。布莱希特用这句评论告诉人们,舞台上已“完结了”的虚构世界是人造的。这样一来,他便将现实中的戏院空间作为公共争辩和讨论场所带到了观众面前。在虚构世界中出现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且通过这种方式明明白白地将问题投射向观众和他们所在的现实世界。布莱希特戏剧的不完整性指向一个民主的世界。在那里,在文学如何同现实关联这个问题上,观众必须自己寻找答案。 演员最终这样告别观众:“尊敬的观众,去吧,您自己寻找一个结局:人世间一定有一个美好结局,一定,一定,一定!”这首先是对在最后一幕中所产生的效果的重述:神明们离开了舞台,观众被鼓励去形成他们自己的判断。因此,在自我反省的这一召唤中最重要的,是让人们坚持个体的反省态度(每个观众都被邀请去“寻找”一个结局),以对抗想要依靠集体来解决问题的念头。而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一个开放的、允许每个人独立地向政治规范提出疑问的公共空间的呼唤。(60)《四川好人》所表现出来的是两种不完整性:表演的最后一幕被迫中断,而观众则受到了自省的,或者是后设剧场式的挑战。该剧集中体现了布莱希特所构建的碎片化伦理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也体现了布莱希特将民主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只有个体的反省和集体讨论同时发生时——譬如在剧场里——民主的政治规范才会出现。(61)而若要让这种讨论的发生成为可能,文学便必须放弃它“神学式”的、与真理息息相连的特殊话语权以及地位。 鲁迅所处的历史背景,也迫使他特别关心民主制度下的民众这个颇有争议的层面。在许多知识分子眼中,辛亥革命并没有成功地孕育出民主文化。那么,如果说小说似乎能够培养个体的批判精神的话,这种精神是如何凝聚成具有合法性的政治体制的呢?阿Q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公民?当五四的社会活动家们确信,必须通过文学来建立新中国的时候,鲁迅的小说对文学在唤起读者的民主意识方面所能产生的影响力,却同时怀有着希望和质疑。 在《阿Q正传》中,在阿Q——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劳动者,和叙述者——一个后儒家的知识分子,两者之间最终的僵持状态,事实上得到了第三方的裁定:那就是在刑场上作为观众的看客,他们象征性地代表着读者,以及读者在阿Q故事终结时所感到的欢愉。和阿Q之前看革命党被砍头一样,当阿Q被处决的时候,看客也希望得到一种享受,而这种美学上的享受则是基于他们政治上的无知。鉴于这一点,鲁迅也对小说的本质作了如下说明:通过用他人的苦难来达到美学上的目的,传统小说总是将他的读者们转化成一群张着嘴巴的看客。(62) 那么鲁迅的小说又是如何打破这种享乐美学,从而构建一个民主辩论的空间的呢?阿Q被处决后,村民们的讨论仅仅是集中在用枪毙而不是砍头,而关于阿Q的罪行,“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故事末尾几行中这最后的谈论,再一次显示了村民们并没有抓住事情的关键;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将阿Q的一生以一个道德判断(“坏”而不是“有罪”)做了总结。然而,他们的讨论却至少表现了公共空间的一幅虚拟图景,而文学恰恰必须通过挑战社会政治规范的方式,努力把这个空间创造出来。而在这里,村民们对于行刑方式的关切和着迷,却阻碍了他们去责问事情真正的要害:阿Q被处决是否合理合法? 那么这样一种公开的讨论又该如何开始?阿Q没有为聚首的人群唱戏和表演,这不能被说成是阿Q自己不让村民们享受行刑时所常见的景观而故意为之的;但他的无能可以被解读为作者的一个策略,是作者不想让读者们获得那种通常会从阅读传统的小说中得到的快感。而且,正如布莱希特瓦解基督教的寓言故事那样,鲁迅也使用了碎片化的描述,让读者感到失望,以此来质疑自己文学创作的合法性。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写道:“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63) 为了对抗小说制造快感这种传统的机制,鲁迅让阿Q显得尽可能地无知并且无耻,而同时,也用他以虚构的方式来“再现”读者。(64)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谈到将《阿Q正传》搬上舞台的建议时写道: 果戈理作《巡按使》,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65) 通过这种布莱希特式的认同手段,作品违背着读者的意志,逼迫他对阿Q这样的角色产生共鸣;如果文学试图避免将其所描绘的痛苦转变成美学享乐的对象,这种认同也许是唯一的出路。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引起真正的公共讨论,而不只是仅仅将注意力放在行刑的美学层面。这种想法将民主化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读者个体身上,即使它并不能解决鲁迅的疑虑:在新的政治制度内部,公共空间是否真会存在而且被制度化。(6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缺少公共空间的现实,直接导致了以这种方式解读《阿Q正传》的不可能。 顺便可以指出,鲁迅所描绘的村庄广场这个公共空间,即村民们谈天说地的场所,和当地的地方戏有着明显的关联。而看地方戏,竟然是故事中阿Q喜爱的消遣方式,也是现实生活中的鲁迅的爱好(如在他自传性的文章《社戏》中提到过)。这种关联也许可以让村民借用本土文化作为基础来质疑政治合法性的问题。(67)当阿Q用地方戏剧的唱词“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只是为了耀武扬威的时候,在《社戏》中,鲁迅似乎想要暗示的,是地方文化和未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农村社群来扮演一种原民主角色的可能性。(68) 因此可以这样说,两部作品的结尾,均是以自我指涉性的方式,将故事放置在一个更广泛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通过布莱希特的观众和鲁迅的读者得到了具体的呈现。而在卡夫卡这部生前未发表的作品中,却没有什么可比性,虽然它的一个片段在一本相当政治性的、被中东欧的犹太和德语知识分子圈中广泛阅读的杂志上得到发表,也确实与鲁迅和布莱希特所关注的问题遥相呼应。(69)通过对传统美学形式完整性的碎片化,鲁迅和布莱希特并不想仅仅沉浸于一种自我指涉性的美学游戏中:他们把这些碎片放置在一个既是具体的公共讨论空间、又是文学被接受的现实空间内,以此来要求观众们质疑他们自己创作的这些文本的地位和合法性。 通过详细分析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的文本,本文认为这些作品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重新定义文学在道德、历史和文本的交际框架层面上所扮演的角色。它们从三个层面颠覆传统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虚构的完整性和伦理规范传播的关系,线性的叙事结构和线性的历史观的关系,以及文学作为私人、享受的活动和公共空间的关系。通过唤起人们对舞台与观众之间,因此也就是虚构和现实之间界线的疑问,布莱希特用将虚构世界碎片化的策略,让观众面对那些从剧中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并把它们带回现实中去。而通过将历史描绘成一种处在不同时态中的碎片和叙事的并列,卡夫卡所做的不仅仅是制造出一个自我指涉的形象,来显示文本的含混性:他想告诉读者的是,历史的意义并不来自于它本身,而是来自于它必须被人们阅读、阐释和重组的过程——即使这个过程无法保证能产生意义。鲁迅笔下这个让人不悦的故事,既嘲笑着它的读者,又逼迫他们面对自己扭曲的镜像。最后只有某种公共讨论,才可以解决故事结尾所出现的僵局。这三位作家均将小说的焦点移到了读者身上,而这样一来,小说潜在的自我指涉性,这个与文类的历史一样悠久的特性,便被用作为催化实现文学和文化民主化的酵母。 这三个文本也呼唤一种崭新的写作实践。正如民主可以理解为一种既未定义又举棋不定的反乌托邦世界的历史产物那样,这三个文本也试图解放政治秩序中的某个象征性核心,无论从意义的层面还是从合法性的层面。因此,当一部作品的作者不再是先知或者道德权威(“以天下为己任”),而其读者也有权对小说中未解决的问题进行个人反思和集体讨论时,这就可以视为将这部作品定义为现代主义作品的主要标准。如此一来,本文中提到的三个文本各自在其特有的现代主义和民主伦理之间建构起了一种类比关系。现代主义因此也许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民主的交际方式,作家们通过它将话语权的中心打开,将其推向各式各样的解释和公共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它也将这些文本向某种操控开启了方便之门,正如民主的开放性亦不能完全消除被某些意识形态“添补”的危险。 民主的社会伦理和现代主义小说之交际框架之间存在着类似的关系,这样的假设构成了对现代主义的重新定义。这种定义对以下的传统二分法提出质疑:一边是以西方特有的、自主的、美学的“极盛现代主义”;另一边是所谓五四中国典型的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即卢卡齐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这种对现代主义的重新定义,不应该被视为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尝试——它的目的是更加细致地审视东西方的现代主义作家的政治架构。这种定义也不想否定某些现代主义实验的重要性:正如卡夫卡的小说所展示,这些实验经常和在文本中心所开创某种象征空间的做法恰恰有关,而这个空间也许可以称为民主的空间。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主义既没有姗姗来迟也不是殖民地式的。如果我们将现实主义理解成一种风格,它将世界以完整、详尽、清楚明了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或如安敏成所言,它是作为一种最终依靠理性来启蒙读者的形式而存在——的话,那么鲁迅在很大程度上也并非一个现实主义者,即便把他理解为一个要来“扰乱他从西方学来的现实主义模式之秩序”的现实主义者。(70)相反,他的主要目的和卡夫卡一样,是要让现实变得模棱两可,从而模糊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界线,用旧的语言质疑现代的行为。 然而将这些权力转移到读者那里,并且象征性地转移到民众那里,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问题。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并不能保证政治决策可以增进民主。空虚的中心很容易被组织完备的党派所占据。民主本身蕴含许多可能性,然而并非所有的可能性都是民主的,正如卡夫卡的司法管理部门、布莱希特的血汗工厂,或者阿Q的革命计划所显示的那样:在他们所想象的民主范畴内,极权主义亦清晰可见。鲁迅,也许比卡夫卡和布莱希特更能代表对一整代作者的误读。他们在虚构里仔细构思的那些两难,一边抵抗一边又默许现代化,却被理解成是赞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抹杀了他们特有的、批判性的、民主的现代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许可以最终确认鲁迅现代主义中的一个特点:当布莱希特和卡夫卡将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司法机构描述为现代性被体制化的决定性因素时,鲁迅的民主空间也许是他们之中最“空虚”的——如果真的可以找到这样一个空间的话,那么在鲁迅那里也许只能是乡村文化。他对体制化秩序的不信任、对小型社群和地方文化的偏爱,更重要的是他将文学创作看作是一种处在党派政治和任何形式的组织之外的“纯粹行为”的态度。这些特征可能是中国现代主义中一个细微的特别之处,而它并不削弱中国的现代主义在全世界的现代主义思潮中的重要意义。 注释: ①本文首次发表于《疆界2》(Boundary2),2011年第38期第3号。 ②Fredric Jameson,"The-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no.15(1986):p.65.(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跨国资本主义时期的第三世界文学》) ③在本文中,像哈贝马斯的做法一样,我对“现代性”一词取其通常的意义,意指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理性化”和“目的理性的经济和管理行为的体制化”。Jürgen Habermas,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Zw?If Vorlesungen,Frankfurt:Suhrkamp Taschenbuch,1988,p.9.(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十二讲》)对于现代主义的定义,请以下马泰?卡林内斯库的定义。 ④Leo Ou-fan Lee,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⑤David Der-wei Wang,Fin-de-si è cle Splendor: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王德威:《世纪末的华丽:晚清小说之被压抑的现代性1849—1911》) ⑥Shu-mei Shih,The Lure of the Modern: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191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p.ix.(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 ⑦Leo Ou-fan Lee,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A Study of Lu Xu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史书美认为,鲁迅作为与新文化运动关系最密切的作家,只是通过自我憎恨式地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来接受(西方)现代主义。(Shu-mei Shih,The Lure of the Modern,p.84.) ⑧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在他所著的《现实主义的局限:革命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创造了“现实主义的局限”这一概念。(The Limits of Realism: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见David Der-wei Wang,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Mao Dun,Lao She,Shen Congwe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王德威:《二十世纪中国的虚构现实主义:茅盾、老舍、沈从文》) ⑨Leo Ou-fan Lee,"In Search of Modernity:Some Reflections on a New Mode of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Ideas Across Cultures: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Schwartz,ed.Paul Cohen and Merle Goldman,Cambridge: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0,pp.135,125.(李欧梵:《寻找现代性: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和文学中新兴意识模式的一些想法》) ⑩对于五四“权威式”理解的批判请参阅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和李欧梵早在1967年的一个座谈会上所发表的文章;也可见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前言;以上文献均在史华慈编辑的《对五四运动的思考:一次座谈》。(Benjamin Schwartz,ed.,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A Symposium,Cambridge: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3.)谷梅(Merle Goldman)编辑的《五四时期的现代中国文学》也并未朝着将五四描述为一场与传统决裂的运动的方向探讨该问题。(Merle Goldman,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11)C.T.Hsia,"Yen Fu and Liang Chi-ch'ao as Advocates of New Fiction," in 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Ch'ao,ed.Adele Austin Picket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p.221~57.(夏志清:《作为新小说倡导者的严复和梁启超》) (12)见汪晖《无地彷徨:五四回声》,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3)Jeffrey Kinkley,"Shen Congwen among the Chinese Modernists," Monumenta Serica,no.54(2006),pp.323~29.(金介甫:《中国现代主义者之沈从文》) (14)Matei Calinescu,Five Faces of Modernity:Modernism,Avant-garde,Decadence,Kitsch,Postmoderni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p.140.中文译文见: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1页。 (15)Walter Benjamin,Gesammelte Schriften,ed.Rolf Tiedemann and Herman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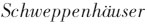 ,Frankfurt:Suhrkamp,1991,vol.1,pt.2,pp.537~569. ,Frankfurt:Suhrkamp,1991,vol.1,pt.2,pp.537~569.(16)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ild Melts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London:Verso,1983,p.16.(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 (17)肯定意义上的定义,见阿多诺《美学理论》;否定意义上的定义,见詹明信《单一的现代性:当下的实体论》。(Fredric Jameson,A Singular Modernity: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2.) (18)见亚历克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Alexis de Tocqueville,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1835-1840),2 vols.,Paris:Gallimard,1986,vol.2,pp.395~455. (19)Claude Lefort,"La question de la d é mocratie," in Essais sur le politique XIXe-XXe siècle,Paris:Le Seuil,2001,p.28.(克劳德?勒弗尔:《民主的问题》;此段由李金佳和魏简译) (20)另见戴维?格莱伯(David Graeber)的论述。他的观点与此稍有不同,他认为,所谓民主“植根于”的某种“根源”或者“文化传统”其实并不存在。见《可能性:关于等级、反叛和欲望的文集》,特别是,“论民主理想的兴起”以及“传统作为无尽重建的行为”。(D.Graeber,Possibilities:Essays on Hierarchy,Rebellion,and Desire,Oakland:AK Press,2007,pp.344~347、355~362.) (21)J.Habermas,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p.16. (22)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道德信条(在这个层面上说与一神论宗教颇为相似)在当时当然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钟爱的攻击对象。 (23)(24)Lydia H.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1900—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47、50.(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 (25)这个想法无疑是受到了许寿裳在和鲁迅讨论时所说的一些想法的启发。然而,根据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全集在线检索的文档显示,“国民性”这个说法事实上只有在鲁迅七篇杂文中出现,而在他的小说中却一次也没有出现。另外,在翻译本和私人信函中则出现过十一次。他自己从来也没有用过“改造国民性”这样的说法。见http://www.luxunmuseum.com.cn/lxFindWord/(2011年6月27日浏览)。 (26)戴维?凯利(David Kelly)在《至高无上的中国性:尼采和中国思想》也提及了这个观点。(David Kelly,"The Higher Chinadom:Nietzsche and the Chinese Mind,1907-1989" in Nietzsche and Asian Thought,ed.Graham Park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p.157~158.) (27)见鲁迅《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页。 (28)M.Anderson,The Limits of Realism,p.84.中文译文参考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29)David Der-wei Wang,"Crime or punishment? On the forensic discours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in Yeh Wen-hsin(ed),Becoming Chinese: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260.(王德威:《罪或罚?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公开法律辩论话语》,见叶文心编《成为中国人:通往现代性及以后之路》)与吴组缃的比较另见第272页。 (30)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四卷,第468~469页。 (31)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革命”一词的使用只取了它当时很普遍的一般意义。而因此不管是(亲)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政治力量都会使用这个词汇。对鲁迅来说,这个词只是等同于“进步”或者是“带有政治性的文学”。 (32)Tang Xiaobing,"Lu Xun's 'Diary of a Madman' and a Chinese Modernism," in Chinese Modern:The Heroic and Quotidian,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pp.49~73.(唐小兵:《鲁迅的〈狂人日记〉和一种中国现代主义》,《中国现代:英雄与凡人》)唐对《狂人日记》中的中国现代主义的观点与本文的颇为相似:特别是关于用“现代主义语言”对抗文学现代主义这部分,以及他关于“现代主义的历史问题”的论述。 (33)M.Anderson,The Limits of Realism,p.11.王德威也将鲁迅界定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并强调寓言在他现实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现实主义话语在当时激起了一种反话语,一种寓言式的潜台词,它将什么应该是真实和什么是真实之问张力展现出来。”David Dei-wei Wang,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p.4.以《阿Q正传》为例,本文认为作品中隐含的寓言自我分裂成混合的戏仿和开放的结局,从而破坏了王德威所描绘的那种连贯的现实主义形式。 (34)Bertolt Brecht,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Frankfurt:Suhrkamp,1964,p.144.(布莱希特:《四川好人》)中译名和段落皆参考丁扬忠译《四川好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35)(37)Bertolt Brecht,Arbeitsjournal,Frankfurt:Suhrkamp,1973,pp.52、227.(布莱希特:《工作日志》) (36)Hans Mayer,Brecht in der Geschichte:Drei Versuche,Frankfurt:Suhrkamp,1971,p.61.(汉斯?麦耶:《历史中的布莱希特:三个尝试》) (38)有些评论家,如安东尼?塔特罗甚至得出结论,布莱希特主张道家式的出世,即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隐退出来。见安东尼?塔特罗《邪恶的面具:布莱希特对中日诗歌、戏剧和思想的回应;一个比较与批判性的评价》。(Antony Tatlow,The Mask of Evil:Brecht's Response to the Poetry,Theatre,and Thought of China and Japan.A Comparative and Critical Evaluation,Bern:Peter Lang,1977,p.450.) (39)Volker Klotz,Bertolt Brecht:Versuch ü ber das Werk,Wiesbaden:Athenaion,1957,p.15.(沃尔克?科洛泽:《贝尔托布莱希特:作品试析》) (40)Jan Knopf,Brecht Handbuch,vol.1,Theater,Stuttgart-Weimar:Metzler,1980,p.206.(杨?科诺普夫:《布莱希特手记》,第一卷《戏剧》) (41)Klaus-Detlef Müller,Die Funktion der Geschichte im Werk Bertolt Brechts,Tübingen:Max Niemeyer Verlag,1967,p.60.(克劳斯?代特勒夫?穆勒:《历史在贝尔托布莱希特作品中的功用》) (42)汉斯?罗伯特?姚斯也提到过类似的观点,他提出的想法是:文学能够传授“尚待完成的规范”。他将这个问题与他对布莱希特的解读联系在一起,强调“布莱希特的问题是,如何向他的观众呈现行为的规范准则,但却又不能公开地或者是偷偷地强迫观众接受它们。”见姚斯《美学经验和文学阐释学》。(Hans Robert Jauss,sthetische Erfahrung und Literarische Hermeneutik,Frankthrt:Suhrkamp,1991,pp.89、185.) (43)鲁迅:《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6~17页。 (44)鲁迅:《小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57页。 (45)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97页。 (46)David Der-wei Wang,"Crime of punishment?",p.174. (47)如哈特姆特?宾得在《卡夫卡全集评论》中所示,卡夫卡对当代中国政治颇为熟悉。(Hartmut Binder,Kafka Kommentar z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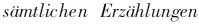 ,Munich:Winkler Verlag,1975,pp.218~22.) ,Munich:Winkler Verlag,1975,pp.218~22.)(48)(49)W.Benjamin,Gesammelte Schriften,vol.2,pt.2,pp.426~27、427. (50)Franz Kafka,Beim Bau der chineaischen Mauer und andere Schriften aus dem Nachla β,Frankfurt:Fischer Taschenbuch,1994,p.65.(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中文译文参考《卡夫卡全集》第一卷(短篇小说),叶廷芳主编,叶廷芳,洪天福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387页。该篇由叶廷芳译。 (51)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第378页。 (52)Ritchie Robertson,Kafka:Judaism,Politics,and Literature,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p.173.(利特池?罗伯特森:《卡夫卡:犹太教、政治和文学》) (53)Gilles Deleuze,Félix Guattari,Kafka:Pour un litt é rature mineure,Paris:Minuit,1975,p135.(吉勒?德勒兹和菲力克斯?瓜塔里:《卡夫卡:迈向少数文学》) (54)在本雅明的《弗兰茨?卡夫卡:十年祭》中,他写道:“在他和歌德那场著名的埃尔富特对话中,拿破仑认为政治取代了命运的位置;如果卡夫卡要重写此言,可能会把组织看作为命运。组织在此不仅表现为在《审判》和《城堡》中随处可见的官僚等级制度;对卡夫卡来说,它也在那些复杂和互相交织、以《中国长城建造时》为模范的建造工程中更具体地出现。”W.Benjamin,"Franz Kafka.Zur Zehnten Wiederkehr seines Todestages",Gesammelte Schriften,vol.2,pt.2,pp.420~421. (55)Hannah Arendt,"Franz Kafka," in Die verborgene Tradition:Acht Essays,Frankfurt:Suhrkamp,1976.(汉娜?阿伦特:《弗兰茨卡夫卡》,于《隐蔽的传统:八篇论文》) (56)卡夫卡的中国故事经常被看作是关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接触到的“东方犹太人”生活状态的寓言(详见罗伯特森的《卡夫卡:犹太教、政治和文学》)。但这也与将它作为关于“中国”的解读并不矛盾,在这两部作品中,对古老政治组织形式的描述虽然在某个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怀旧,或者是对政治组织具有神圣性质这一信念充满迷恋的表现;但也是个人权力的充分获得或者个体解放道路上的障碍(值得注意的是,从卡夫卡的生平来看,他始终支持布洛德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而非布伯的神秘主义观点)。 (57)唐的论述中也强调了这一点,见:《鲁迅的〈狂人日记〉和一种中国现代主义》。Xiaobing Tang,"Lu Xun's 'Diary of a Madman' and a Chinese Modernism",p.73. (58)见Pierre Rosanvallon,La démocratie inachevée:Histoire de la souveraineté du peuple en France,Paris:Gallimard,2000.(皮埃尔?罗森瓦隆:《未完成的民主》) (59)彼德?比格尔认为,布莱希特美学的这个层面显示了其作品的“先锋派”本质;但也许可以追问,在何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更为普遍的现代主义特征,包括其他比格尔也认为是对文学体制缺乏批判力的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或者马塞尔?普鲁斯特)。Peter Burger,Theory of Avant Garde,trans Michael Shaw,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 (60)汉娜?阿伦特也曾用类似的观点对布莱希特的教育剧《恶有恶报》进行伦理上的解读,见:《贝尔托?布莱希特》,《本雅明-布莱希特:两篇文章》。(Hannah Arendt,"Bertolt Brecht," in Walter Benjamin-Bertolt Brecht:Zwei Essays,Munich:Piper,1971.) (61)一如既往地,布莱希特在他的《工作日志》中对民主下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式的定义:“民主只能够在它不断地与官僚体系(red tape)、守旧和‘铁板纪律’战斗的时候才会胜出。”见布莱希特《工作日志》,第403页。 (62)鲁迅坚持认为小说有“吃人”的层面,这种观点可能来自于他对朱熹美学的批判有关。朱的美学提倡要“咀嚼”文学。 (63)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70~171页。 (64)刘禾亦指出,当叙事者强调阿Q的“不可思议的愚昧”(Lydia H.Liu,Translingual Practice,p.50),读者很容易地便得到了快感,即便他之后还是要有负罪感。在她看来,鲁迅像乐于讽刺阿Q那样乐于连累他的读者。 (65)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49~150页。胡志德最早开始关注并评述这篇关键的文本,指出其与鲁迅作者策略的关系。Theodore Huters,"Hu Feng and the Critical Legacy of Lu Xun," in Lu Xun and His Legacy,ed.Leo Ou-fan Le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129~52. (66)哈贝马斯假设十八世纪欧洲的阅读习惯和公共空间的兴起有关系,也受到了历史学家的深刻质疑。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当然可以同样质疑这个关系的实际存在。Jürgen Habermas,Strukturwandel der ffentlichkeit: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Neuwied:Luchterhand,1971.(哈贝马斯:《公共性的结构转变:探究市民社会类型一种》)而如何将窥视阿Q处刑的盲众转化为理性的公民这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 (67)王德威在讨论《阿Q正传》的“公开法律辩论话语”时(见:《罪或罚?》),并没有细谈“论坛”的空间表象,而是将“公共空间”和法庭戏剧的传统和晚清的其他文学类别联系起来。值得强调的是,不论是在鲁迅还是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这个空间都具有很强的乡土性。 (68)有趣的是,在被人们广泛讨论的老舍的话剧《茶馆》中,故事的三场分别设定在1898、1916和1946年,这样的设定似乎展现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如何从本质上限制了如北京传统茶馆这样的前现代时期的民主公共空间的。剧本题目中的茶馆和剧目上演时的剧院之间的对等关系显示了老舍的疑惑:1949年以后的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体制,是否能够容纳得下来自于地方文化的批判(或是民主的?)精神?关于《茶馆》中的政治批评,详见G.A.劳依德的博士论文“两层的茶馆:老舍戏剧中的艺术和政治”。(G.A.Lloyd,"The Two-Storied Teahouse:Art and Politics in Lao She's Plays",Ph.D 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2000.) (69)关于《自我防御》杂志,见哈特姆特?宾得的研究:“弗兰茨?卡夫卡和周刊《自我防御》”,《德国文学和思想史季刊》。[Hartmut Binder,"Franz Kafka und die Wochenzeitschrift Selbstwehr," Deut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vol.41,no.2(1967):pp.288~304.]有趣的是,根据宾得的研究,卡夫卡将登有他作品的杂志看作是一个论坛,在那里他可以和那些也在上面发表文章的朋友和同事们进行交流。 (70)M.Anderson,The Limits of Realism,p.92.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