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寥士一生诗学的最高造诣,并非体现在《单云阁诗话》及散篇文字中,而体现于晚年参与撰写的《宋诗选讲》,这应该是最好的宋诗读本了,甚至比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好。  《校辑近代诗话九种》 王培军 庄际虹辑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10月第一版 272页,54.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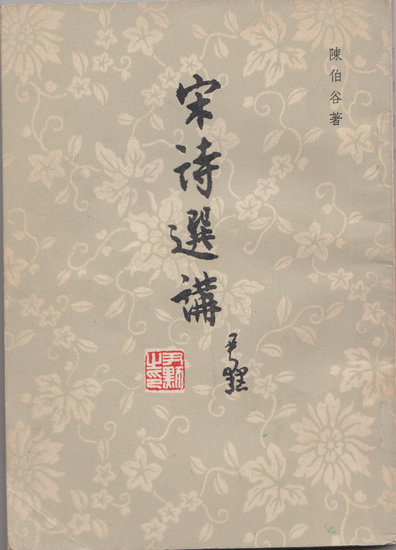 《宋诗选讲》陈伯谷著 香港上海书局 1963年出版  《单云阁诗话》书影一叶 新刊《校辑近代诗话九种》一书,收陈寥士《单云阁诗话》。陈寥士,原名陈道量,字器伯,号寥士。据整理者介绍,所辑《单云阁诗话》分别载于沦陷时期的两份杂志:“一九四〇年始刊于《国艺》,至一九四二年讫,凡载十七次。一九四三年又载《一般》一次。”经查,整理后的《单云阁诗话》,一七七则以前,载于《国艺》,一七八则至一九九则,载于《一般》。 不过,事实上,陈寥士的《单云阁诗话》并不只载于上述两份杂志。1942年10月,《中国诗刊》在南京创刊,中国诗刊社编辑,由陈寥士任社长。《中国诗刊》从10月到12月一共只出了三期,每期都刊登署名“单云”的《单云阁诗话》;该刊同时登载署名“陈寥士”的《单云阁诗》,则此《单云阁诗话》为陈寥士所作是无疑问的。 《中国诗刊》创刊号刊《单云阁诗话》十六则,卷第二刊十五则,卷第三刊十一则,共四十二则。此四十二则,与《校辑近代诗话九种》所辑《单云阁诗话》无重复者。 从时间上看,《单云阁诗话》最后一次刊于《国艺》杂志第四卷第一期,是1942年上半年的事情,而《中国诗刊》创刊于同年10月,12月即终刊,刊于《一般》则在1943年了。因此,合理的推测是,《单云阁诗话》写作及刊载的次序为:《国艺》《中国诗刊》《一般》。从内容上看,亦有支持此推测之证据。《校辑近代诗话九种》所辑《单云阁诗话》第四则(载于《国艺》第一卷第一期,1940年1月15日出版)云:“苍虬诗‘鸡鸣一何悲,众生不同晓’,又有牡丹诗‘睡足出严妆,午韵不如晓’,二‘晓’字甚警。”《中国诗刊》卷第二(1942年11月5日出版)所载《单云阁诗话》第一则云:“余谓陈苍虬,可以称为‘陈三晓’。因其集中有三‘晓’字,至为警策。其一,《鸡鸣寺怀朴生丈及四弟》云:‘鸡鸣一何悲,众生不同晓。’其二,《晨在崇效寺看牡丹》云:‘睡足出严妆,午韵不如晓。’其三,《寄怀陈师傅弢庵先生即题听水图》云:‘太白何睒睒,独与残月晓。’”对比可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从“二晓”到“三晓”,作者有了新的认识,改写了之前撰写的内容。 《中国诗刊》载《单云阁诗话》,所评古人有顾炎武、唐彦谦、史念祖、倪岳、毛晋、渐江等,所评近代诗人则包括王式通、夏庆绂、谭献、沈尹默、汪兆镛、金兆蕃、张謇、齐白石、陈曾寿、陈锐、赵熙、缪荃孙、杨寿枬、郭则沄等。《单云阁诗话》所存掌故及评语自有其价值,不过,从总体上看,以摘句为主,作者的诗学主张隐而未彰,阐论似嫌太少。 诗话之外,陈寥士还发表过诗论若干篇。我未专门收集过,只列闻见所及者如下:《从全唐诗说到天一阁秘籍》(载《逸经》1937年5月号)、《王湘绮诗及其说诗的一斑》(载1941年《作家》)、《海藏楼诗的全貌》及《关于钱牧斋》(分别载《古今》第7-8期及第18期)、《诗的味外味》(载《人间味》1943年3月号)、《双照楼主人之父汪玉叔先生诗及事略》(载《申报月刊》1945年4月号)。这些文字也许于诗不无所见,但谈不上精深,像《海藏楼诗的全貌》一篇,文章甚长,而精义无多。 在我看来,陈寥士一生诗学的最高造诣,并非体现在《单云阁诗话》及散篇文字中,而是体现于晚年参与撰写的《宋诗选讲》一书。 《宋诗选讲》,署“陈伯谷著”,1963年由香港的上海书局出版,后有重印本及台湾翻印本。当时《大公报·艺林》周刊的编辑陈凡为该书作序,称“书里所收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在《艺林》周刊上陆续发表过的”,又说:“《宋诗选讲》在《艺林》上发表时,原名《宋诗染鼎》,这次出版时,为了更求通俗,改用今名。作者陈伯谷先生,其实是两个人合用的笔名,两位都是老诗人;其中一位又是书家,另一位则曾经家藏万卷以上,都是在诗海浸淫过很久的老人了。” 2013年8月,后人整理的潘伯鹰著《冥行者独语》出版,内收《宋诗染鼎》谈杨亿《汉武》、晏殊《寓意》的两篇,使一般读者有机会知道共用“陈伯谷”这一笔名的两位“老诗人”中兼为“书家”的那位就是潘伯鹰。当然,2010年3月,《宋诗染鼎》谈杨亿篇的誊抄稿就曾在拍卖会上出现过,我是在那之后知道潘伯鹰为《宋诗选讲》作者之一的。 2012年2月,陈寥士之孙陈思同先生在博客上贴出文章《祖父与〈宋诗选讲〉》,其中讲到:“1960年,上海潘伯鹰先生应香港《大公报》总编陈凡先生之约,为该报副刊《艺林》撰写专栏文章,潘伯鹰以陈伯谷为笔名(陈伯谷就是祖父和潘伯鹰的姓名合成的),在写第一篇《汉武》时,就向陈凡推荐祖父续写,陈凡同意了,让祖父写几篇看看,祖父一蹴而就,很快完成数篇寄出,陈凡阅后大加赞赏,立即决定采用,从此祖父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专栏写作。” 陈凡说陈寥士“曾经家藏万卷以上”是属实的,陈寥士的藏书情形,可参考李军先生《变风变雅,朱印蓝印——四明藏书家陈寥士事迹稽略》(刊《天一阁文丛 》第八辑)一文。 《宋诗选讲》的两位作者分别为潘伯鹰、陈寥士,可其分工情况,尚难确知。从陈思同先生的说法推断,《宋诗选讲》的创作主力是陈寥士,而潘伯鹰写得较少。从我读《宋诗选讲》的体会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不过,潘伯鹰是否只写了已收入《冥行者独语》的谈杨亿《汉武》、晏殊《寓意》的两篇呢?我认为未必。 《宋诗选讲》讲黄庭坚的一篇提到:“潘伯鹰《黄庭坚诗选》导言,对于黄诗分析得很精细。他举出黄诗的特点如下:……”接下来所列一、二、三、四各点,均出自潘伯鹰选注《黄庭坚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之后又谈黄庭坚《次韵题西太一宫壁》,所引任渊注,亦见《黄庭坚诗选》该首注释。我们知道,潘伯鹰在用笔名写的文章里常提及自己的本名,自赞自誉的例子亦不少。因此,我疑心《宋诗选讲》讲黄庭坚的这篇出自潘伯鹰的手笔。试想若陈寥士来写黄庭坚,总未必肯照抄友人的结论罢。 杨亿、晏殊、黄庭坚而外,我猜测写陈师道的一篇,也是潘伯鹰写的,然无确证,只是从文风上推测而已,故略去不提了。两位作者文风不尽相同,大体说来,潘伯鹰的文字平实恳切,多围绕所选的一首诗展开,而陈寥士则喜欢摘句,较多发挥,常荡开一笔,上下古今。 《宋诗选讲》中较有把握确定为陈寥士所作者有两篇,一是谈司马光的,一是谈晁冲之的。谈司马光一篇中云:“我曾经到山西省夏县去展望过司马光的坟墓和祠堂,又读苏轼撰书的神道碑,不禁再三唏嘘太息。”夏县,距离运城很近。据潘益民《陈方恪先生编年辑事》,1953年,“山西省教育厅来南京征招中等学校教师,在家无业的陈道量主动报名参加……抵晋后,被分配在省立运城地区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师”。1959年,“因右派问题,年已60岁的陈道量被运城师范学校辞退,怅然回到南京。其夫妇和儿子陈孝祚均无工作,靠儿媳在小学任教的几十元工资和出售家藏古籍善本维持全家7口人生活”。潘伯鹰生平未履山西之境,因此,谈司马光的这篇只能是陈寥士所作。 谈晁冲之一篇中云:“四十年前,慈溪冯君木先生选宋人诗为《萧瑟集》,他曾指出二晁是宋诗的骨干。”冯幵所选《萧瑟集》为罕僻之书,非有特殊关系者不见得会引及。事实上,陈寥士正是冯君木的弟子。这一点,他在《单云阁诗话》中曾不止一次道及,另外不妨再补充一个少见些的证据:1942年10月《中国诗刊》创刊号有冒孝鲁《次和寥士见赠》一诗,开头两句是“楼高百尺卧元龙。心折回风一老翁(自注:君为慈溪冯君木先生入室弟子)”。此诗后收入《叔子诗稿》,但自注一句被删去了。谈晁冲之的这篇征引师说,当为陈寥士所作。 再从文辞、用语角度来考察。《宋诗选讲》谈魏野的一篇云:“七律以高调为正格,这种高调的造诣,不要说在隐逸诗人中绝无仅有,就是其他的人,没有浩荡而悲壮的胸襟的,也决不能有这种吐属。”对比《古今》杂志所刊《海藏楼诗的全貌》一文中的说法:“海藏主张律诗全首用高调,我以为他的七律,高调为多。”同用“高调”二字。 又如《宋诗选讲》谈王安石的一篇云:“从来登大位而诗有蔬笋气的,以他为首屈一指。”对比《人间味》杂志所刊《诗的味外味》中的说法:“达官诗而有蔬笋气,惟有王荆公。”同用“蔬笋气”三字。 倒不是说旁人论诗就完全不会用“高调”、“蔬笋气”这类词了,只是在确知《宋诗选讲》只有两位作者的前提下,我们有理由认定谈魏野、王安石的两篇亦为陈寥士所写。 以司马光、晁冲之、魏野、王安石诸篇为依据,可总结出陈寥士文笔之特征;复以此特征揆诸书中各篇,可推断出为其所撰者尚有甚多。此处不再一一详述。 《宋诗选讲》的选目颇有特色,如诗人魏野,见于陈衍《宋诗精华录》,然钱锺书《宋诗选注》、金性尧《宋诗三百首》、钱仲联《宋诗三百首》等较有名的近人选本均未采及。《宋诗选讲》的通例是每位诗人只选一首或一题,全书共选四十人,经与《宋诗精华录》比较,有二十四题未选入《宋诗精华录》。 书中选魏野《登原州城呈张贵从事》一首,即不见于《宋诗精华录》,而在解说时,陈寥士又摘句五言十九联、七言六联。从这些地方不难知道,作者所写虽为一篇短文,但必定是在通读整本诗集的基础上草就的,心得之深,非一般选本所及。 陈寥士此时说诗,解悟已超过四十年代,有时貌似常语而有至味。如王安石,选的是有名的《明妃曲》二首,开头两段说: 诗中有必要的三元素,就是“此时”、“此地”与“有我”也。“我”和“时间”、“空间”是绝对不可分割的。同一诗题,作者千万,何以内容各不相同呢?因为时代的不同,地位的不同,而作者的秉受和感想,就完全不同了。假使有“时”有“地”而没有“我”,就成为没有灵魂的东西。置之甲集可,置之乙集亦可。咏这个可,咏那个亦可。赠你可,赠他亦可。那就何必要这个作品呢。 古来作明妃曲的很多,即如欧公所作,极为自负(指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引者按)。但你自己说好,不能强天下人都说你好。譬如曾南丰《明妃曲》云:“丹青有迹尚如此,何况无形论是非。”便能道诸家所未道。王安石诗,好为自己写照,如咏北陂杏花云:“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这一类例子不少,而尤其是《明妃曲》,显著地为自己写照,写得十二分深刻。以汉帝与神宗相比,以明妃与自己相比。若在他人,无此感想,便不伦不类。 诗人当各有其吐属,本也是常识,但陈寥士此番解说,切合原作,而又能让读者领会这一首诗之外的东西,便觉有味。 也许有人初读《宋诗选讲》,会以为与时下鉴赏文章无异,平平无奇。我反复读此书,感想却不同。大胆一点说,《宋诗选讲》应该是最好的宋诗读本了,不仅比《宋诗三百首》《宋诗鉴赏辞典》之类书好,甚至比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好。《宋诗选注》中俏皮话很多,但对诗的作意、作法,解说甚少,初学无由悟入。而潘伯鹰、陈寥士则能将诗人的解悟心得注入《宋诗选讲》,令此书自有一种沦肌浃髓的透彻。潘、陈分别于1966年、1970年谢世,他们在人生最后的艰困之际,留下这样一部精粹的解诗之作,是值得后人珍重的。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