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荐读 | 陈毅:觉悟迟没关系,就怕觉悟早而不真
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每一个已经加入或希望加入这个组织的人,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岁月里,加入共产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它意味着,不但要面对无数的艰难困苦,而且还要舍弃个人利益乃至牺牲生命。但是,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一批又一批的先进分子,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共产党的行列,党的队伍也就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时至今日,老一辈革命家投身革命时表现出的坚定信念,以及为实现心中理想而体现出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奋斗精神,却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他们的入党经历,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文章讲述了陈毅入党前的心路历程。

首先讲讲陈家的历史。陈家最早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当时湖南宝庆府(今邵阳市)新宁县,有陈尧钦三兄弟随着湖南、湖北等地的老百姓迁往四川。虽然四川土地很多,但他们去得迟了,好地方被别人圈去了。走到乐至县,老大才落户。老二、老三嫌这个地方苦,又走到其他地方去了。这样,陈尧钦就成为乐至县陈家的第一辈。陈家是按照尧、舜、禹、汤、文、武、荣、昌、世、德、延、远、福、寿、绵、长的谱系,循序排辈的。到我(陈毅)这一辈是“世”字辈,所以我原来的名字叫陈世俊。
尧、舜、禹三辈都是农民,到“汤”字辈,出了个陈汤佶,发家成为地主。几代以后,这个地主家庭就慢慢走向没落,甚至破产,堕落为赤贫。这也是一个规律。
1918年,我和大哥陈孟熙一起考上了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二年又考取了官费留法,使我们得到一个机会,跳出四川这个小天地,见到了广大的世界。那时家庭已经破产,没有钱读书了,但又不愿意去当工人,几乎没有什么出路。得到去法国的机会是一个大解放,但实际上不过是到国外去做工。事实证明,在那个社会不参加革命是没有真正的出路的。当然,当时还不可能有那种认识。
到了法国,那是另一个天地,资本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改良主义的思想等,都在影响着我们。
1919年6月,我们离开成都到了上海,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中心。在这里,经历了思想上第一次的动荡。为了欢送我们这一批学生,同时也是为了在年轻人中造成他们的信徒,许多有名的人来向我们演说。比如吴稚晖说什么“四书五经”应该拿去糊窗子,《二十四史》拿去擦屁股。张继是无政府主义者,他鼓吹劳工神圣。日本留学生来讲“明治维新”,中国也要走日本的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青年来讲中国积弱、外国强盛,要讲科学、争民主,做白话文、白话诗。有人讲教育救国,还有人讲关税救国,等等。那时,思想真是一天一变,开始对反孔孟感到不平,对白话文、白话诗感到没意思,但很快就站过来了。读《拿破仑传》《华盛顿传》《孙文传》,感到很入迷。世界变了,中国也要变,但究竟怎么变,思想上还不清楚。
10月,乘轮船到了马赛,开始踏上法国的领土。这以后,我经历了一个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由崇拜到失望的过程,逐渐靠拢马克思主义,靠拢无产阶级。
刚到法国,觉得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是一钱不值了,再也不想读古书、作古诗了。但是实际生活打破了我的这种迷信。
到了巴黎,在补习了几个月法文后,就到史奈德公司的一个工厂做工,实际体验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开始当杂工,打扫卫生,搬运货物,工作很重,而且制度很严,迟到了就不得入厂,一天的工作就没有了。几天以后,就感到难以忍受。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多读几年书。不甘心长此下去,决心还是要搞一点积蓄再去读书。但时间长了,对工人阶级的遭遇有了深切感受,开始了解工人阶级了。法国工人中,社会主义思想流行,许多人说列宁好,希望在俄国。有一次我的手受了伤,只准休息3天,养伤费发得很少,工人们就来慰问,骂资本家没良心。这些活生生的阶级教育,使我们站到工人阶级一边来了。1920年“五一”节,法国工人举行大规模罢工,我们在工厂做工的几个同学开会,决定和工人一起行动,为中国争光。这个行动受到法国工人的热烈欢迎。
当时,在法国做工的学生,因感受到无产阶级的痛苦,自己组织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我们这个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最力者是蔡和森。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很赞成他的主张,并开始读《共产党宣言》。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尖锐的分析、新鲜的提法,引起了我们很久的思索和讨论,如说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揭露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不过是资本家的事务所,等等。这些论断我们感到是真理。我将参加罢工的事向留法学生团体报告,蔡和森很支持,他说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最有前途,它没有国界,它可以联合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头脑中高扬,于是我逐渐参加政治活动,向革命方面靠拢了。
但是,生活本身是按辩证法前进的,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们是官费派往法国的,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境遇又好一点。到工厂3个月后,被提为技术工,工资也增加了,没有什么额外的负担,开始有了点积蓄。这时候又自满陶醉起来,感到自己有办法、有前途可能爬上去,可以当个文学博士。所以又不大愿意和搞革命的人来往,怕被人利用,要自己走出一条路子来。下了工就补习法文,读文学作品,想搞文艺。只是后来法国发生经济危机,工厂紧缩,自己被抛上街头,后来又被押送回国,才被迫放弃了文艺救国的梦想,参加了革命。
1920年冬天,我开始参加工学世界社(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和外围)的活动,1921年春被工厂解雇,从此全心全意地参加学生运动。秋天,参加了向里昂中法大学的进军,蔡和森是湖南学生代表,我是四川学生代表。这个行动的结果,就是北洋政府和法国当局勾结,把我们104个学生代表武装押送回国了。当时押送的军警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分子。我们还是第一次被加上这个罪名。有的学生说:那好吧,我们就去当布尔什维克吧!
1921年11月回到上海,104个同学在船向中国驶近时,感到前途茫茫,除了依靠自己团结的力量外,别无出路。当时,我是学生干事会的成员,力主大家齐心,共同斗争,争取一个好的安置。船到香港时,一部分同学上岸去找孙中山,我劝他们不要分散,他们不听。后来他们在广州见不到孙中山,又跑到上海来找我们。那时,我说服了其他同学,把争得的安置费分给他们一份。
刚到上海时,我做代表向各界呼吁。经过与多方的斗争,结果是政府出一笔旅费让大家回家,另外允许学生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
为了进一步解决在法几百名学生的求学经费问题,同学们派我做代表回四川向各阶层交涉。在上海和蔡和森分别时,蔡劝我参加党,或去苏联。当时我没有下决心,还要回四川去试试,但答应发行党的书刊。我与蔡和森分别后的这段时间,家庭无地位,个人无职业,又目睹了军阀内部的腐朽,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什么出路,心情很苦恼。就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后来,给《新蜀报》写了大量的稿件,《新蜀报》的主编宋南轩聘请我为《新蜀报》的主笔,每月舆马费(即薪金)15元。应聘后,杨森的秘书长沈予白在请客席上婉转地说:“请陈先生在报上多谈点国际形势吧。”暗示我不要接触四川的实际,尤其不要触及军阀们的利害。由此可见,在那个社会上混一碗饭是不容易的。后来,果然因写了一篇批评军阀武装的文章惹了祸,被礼送出川。从此才下决心去找党,1923年10月到北京入中法大学,11月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一方面是自觉的,一方面又是被迫的,但主要是看到了新兴力量之所在,看清了形势,认识到不革命就没有出路。
入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入党后下定决心,坚决干到底,更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革命的转折关头。
我觉悟得比较迟,但一经觉悟就坚决干。那时候为党工作是很艰苦的,党组织不能维持党员的生活,反而要靠党员资助党组织的活动经费。每次支部会最后一项议程就是筹款,要拿出钱来资助党。我那时没有收入,只好到处投稿,翻译一点法国文学作品,得到稿费捐给党,同时维持自己的生活。我认定了一条,党内比党外好,同志之间可以互相帮助,党的事业可以发展,革命一定走向胜利。坚决干到底!
所以,觉悟迟没关系,有反复也没关系,只要真正觉悟了就好办。就怕觉悟早而不真,迟早会动摇。也不要怕犯错误,就怕犯了错误不改。
(节选自《陈老总和儿子的四次谈话》,《中国青年报》1981年2月10日、12日、14日)
推荐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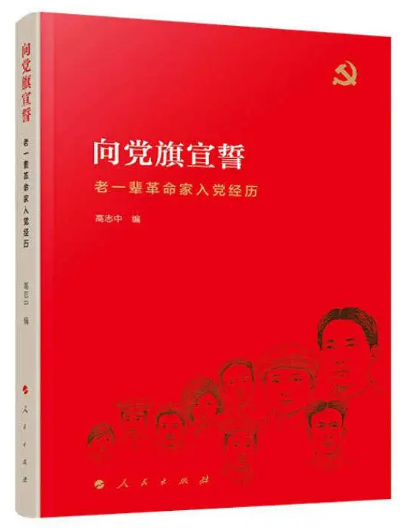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