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7月,《森林沉默》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2020年春节,疫情汹涌而来。在武汉封城前夜,湖北作家陈应松回到了自己位于神农架的家中。如今回想,他最新的长篇小说《森林沉默》似乎是对这场灾难的“文学预言”: “这部小说,写我居住的神农架。早晨听到密集的鸟叫,晚上听到孤独悠远的狼嚎……我们应当尊重人与各物种的相遇,互不干扰,互相尊重。如果我们把地球的资源当作杀戮凌辱的对象,必然激怒大自然,遭到天谴。人类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都有着自己的尊严。如果世界上所有的野生动物不复存在,人类将从这无尽的精神孤寂中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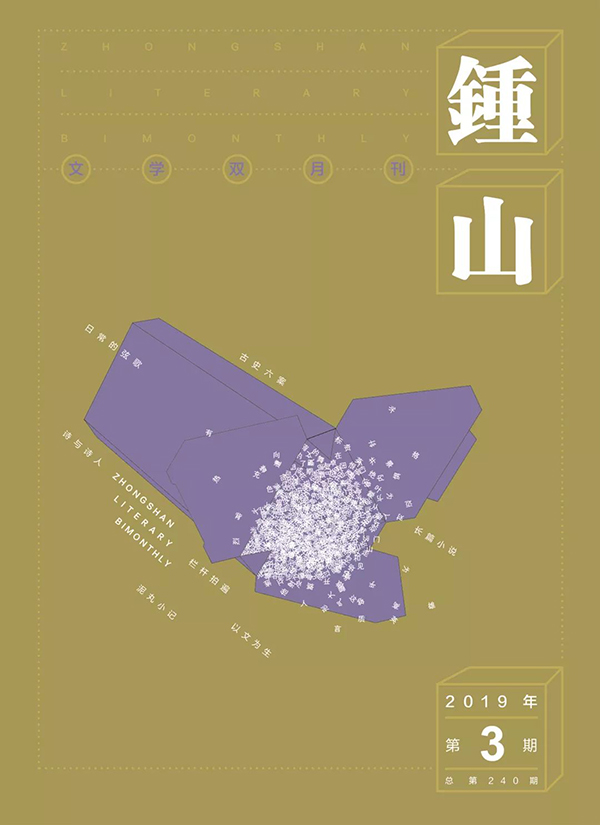 《森林沉默》首发于《钟山》杂志2019年第3期 《森林沉默》首发于《钟山》杂志2019年第3期,近日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单行本。这是陈应松深居湖北神农架山林二十年后,追问现实之殇交出的一份答卷。全书涉及近百种动植物,包括传说和神话中的奇珍异兽,以及大量物候、地质、气象和对森林的想象元素。作家贾平凹说读这篇小说感觉“就像在密林里,能闻到幽暗潮湿的气息,能听到飞禽走兽的响动,枝条蔓草牵扯得手脸生疼”。  陈应松在神农架 小说故事发生咕噜山区的浩瀚森林,主人公是神农架农妇与野人的后代——猴娃。他浑身长红毛,不爱穿衣,懂人语、兽语、鸟语、花语,与家人一起过着艰辛而平静的日子,直到村长带来了“天音机场即将在此破土动工”的消息。从此,这里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口号——“让山冈低头,河水让道!”“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保质保量,要咕噜献宝”,这里人声嘈杂,森林沉默:野兽开始逃难,村庄开始拆迁,河流开始堰塞,推土机沉重的履带将生活了千年万年的种子和根须埋入地下…… “六十岁之前是为别人写作,而《森林沉默》是为自己写的,不为任何规矩,不为任何人的想法。”在《森林沉默》中,陈应松将原始文明、现代文明、后现代文明置于显微镜下,重新审视了生存的酷烈、生命的异化与社会的病相。而从疫情到洪灾,陈应松又目睹了大自然对人类的一次又一次“报复”,因而感慨万千。 “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我相信大自然有很多未解之谜,它们是说不清楚的。”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这段灰色的时光里,即便不身处山林,也要开车去湖边,呼吸新鲜的空气,“大自然的山川草木是我活着的唯一乐趣。”  小说故事发生咕噜山区的浩瀚森林,主人公是神农架农妇与野人的后代——猴娃。 【对话】 澎湃新闻:《森林沉默》写了三年。当初怎么想到围绕“猴娃”,写这样一个故事? 陈应松:我一直在写“神农架系列小说”。神农架行政区划的全称叫“神农架林区”,就这五个字。全国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单位只有神农架,连东北的大兴安岭都不是。我写了三本关于神农架的中短篇小说,大概有100万字。长篇则有两部,一部叫《猎人峰》,还有一部叫《到天边收割》,《森林沉默》是第三部,都是写神农架的山民生活。 可以说,在《森林沉默》之前,我的所有小说都与森林有关,但一直没有专门写森林,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写一部这样的小说。批评家李敬泽在评论里说:“陈应松欠中国文学一个森林。”这句话深得我心,我也觉得我的确欠自己和神农架一个森林。 神农架最具传奇性的应该是那儿的野人,但野人写多了没什么意思。所以我根据自己的写作特点,写了神农架传说中那个个头高大、能讲话、但智力不是很高的一个人(猴娃)。他是神农架的农妇与野人的后代,他懂鸟语,懂兽语,认识所有草木,在自然界里如鱼得水,好像一个原始的神。但人们却认为他是一个唐氏综合征患者,一个低能儿。我就想到写这样一个人在森林里发生的故事。这个小说在2015年动笔,因为事情太忙,中间停顿了一年,但我发现自己一下子就能接上去,后来一口气就写完了。 澎湃新闻:这部小说里有六分之一的森林描写,还插入了大量诗歌、日记等文体,你怎么考虑这些内容的占比?会不会担心为读者带来阅读障碍? 陈应松:在上一部长篇小说《还魂记》中,我加入了一些散文、诗歌的元素。事实上,在《森林沉默》中我依然沿袭了这个路子,只是更加大胆了。长篇小说中的多种元素看起来会造成阅读障碍,事实上并不会。写作几十年了,我知道怎样占比不会让读者感到厌倦。一个好的作家实际上就是要把读者的心理研究透,知道读者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给读者留下什么样的空白。 我写的这个森林,因为从来没有这样写过,所以反倒有一种无所顾忌的冲浪感。过去写动植物的故事叫生态小说、动物小说,主要是浪漫色彩,奇特故事。但“用大量的笔墨来描写森林的景色”,这样的写法几乎没有,至少我没见到过。我擅长描写风景,描写森林山区,所以把它们加了进去。但依然有一些克制,不完全是泛滥的风景描写。比方说有一个章节,我加入了“花仙”的日记,其实引用日记这种方式在以往作品中已不少见,我只是把日记内容换成了风景描写,但又不完全是死板的风景描写,它是一种动感的、融入了感情的风景描写。那也是人物内心的风景,实际上是一种内在情感的外化。 澎湃新闻:能感受到你的文本语言中有诗歌的影子,哪怕是在描述那些动植物的时候,也有一种韵律感。这是不是也与你写诗有关? 陈应松:是的。我用诗的语言来写小说,所以读者在阅读中没有那种“隔”。此外我的小说本身就带有散文化的倾向,不是特别紧凑。我从来不像常规小说那样写,那没什么意思。把你的一本书用一个旋律来经营,是挺有味道的。写一首诗要找一个语感,一个旋律,我把这些办法全用来写小说了,发现真的很美妙,写小说也就成了写诗,写一首长诗,如此而已。 澎湃新闻:在写《森林沉默》时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境? 陈应松:没有。我写神农架没有任何困境。因为我太熟悉神农架。我在神农架待的时间不只有挂职的那一年,我每年都不停地去神农架,许多时间住在农民家里。而且我会时刻记录自己的真实感受,有时把它写成诗歌,写成一段一段的日记,慢慢地积累,等到写小说时信手拈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保持几十年的良好习惯。等到写作时,我不会有写不出来或是很难受的感觉,反而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写进去。而且现在还有大量的照片辅助记忆。只不过,有时照片也不太管用,因为你在那一个时刻记录的是稍纵即逝的感性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对神农架的了解或从神农架获取的素材,至少两辈子都写不完。 澎湃新闻:取“森林沉默”这个书名,有没有特别的用意? 陈应松:我一开始准备叫《沉默的森林》,后来觉得太过文青,别人可能会误会这是一本纯生态的散文。后来我改为《森林沉默》,显得更有力量一些,更小说化些。 森林里其实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响,只是我们听不到。我住在神农架,每天夜晚都能听到松涛声、林骚声,那是一种类似海潮一样的深沉响声,就是森林在说话。现代人全去了城市,离得太远,听不到了,所以森林终归还是沉默的。 当然这个题目也有另外一层意思。比方说花仙这个人物最后自杀了,因为她有好多话没说出来,带进了棺材。她跟她的学长有那样一种关系,她的导师又被坏人诬陷而死,她对整个社会、对现代文明的绝望,虽然内心如汹涌澎湃的林涛,但终归是沉默的。 而猴娃玃本身是一个哑人,他代表森林,他的沉默就是森林的沉默。森林里那些活着的人,包括他的叔父麻古、祖父蕺老泉,他们也都是沉默者,没有任何说话的地方,也没有人为他们说话。他们是森林里沉默的一群人,像石头一样活着,像植物一样活着,从生到死,谁都不知道他们。生生死死,生生不息。哪怕他们的生命力特别顽强,他们也“一句话说都不出来”。现代传媒世界里没有他们的一丁点声音,多少人就那么沉默了一生。 澎湃新闻:你曾说过,“在小说中,象征不是象征,现实不是现实,人物不是人物,故事也不是故事,它们表达的是另外的东西。这个‘另外的东西’才是小说的核。”那在这部小说中,“另外的东西”是什么? 陈应松:“另外的东西”是要留给读者的,留给时间的。好的小说肯定有大量另外的东西,就像《红楼梦》、《金瓶梅》,你永远说不清,那是留给未来的,留给那些有阅读能力和强烈感悟力的人的。当然,也留给一些钻牛角尖的人。 留给时间,就像一个精美的古物,最值钱的东西是时间给它的包浆。它需要慢慢地沉静。我认为,好的小说一定至少要给读者留出一半的空间来。说出来的东西永远不是最好的部分,最好的永远是没有说出来的,而且是你故意不会说出来的。好作家就是留下最好的东西不说,小说就是说话克制的艺术。 我相信每个人的解读都是合理的,你不能说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它没有标准答案。歧义是好小说的标准,解读的千奇百怪是好小说的标志。再者,“另外的东西”作家也说不清楚,那就让它留着,混沌和歧义泛滥也是好小说的特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是好作家不能进入的禁地,是他圈起来给读者享受的。 澎湃新闻:很多小说家说,他们只负责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或者提醒人们关注问题,但他们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在这本小说中写到了原始森林受到一些现代性的侵害,揭露了“原始-现代”这样一对矛盾,你觉得这本小说可以给出答案吗?你想要做的是什么? 陈应松:我没有答案。作家不是万能的,作家不是官员,也不是专家,不解决问题。他既没有技术,也没有资本,更没有权力,就是一群无能的人。他只提出和讲述问题,但他希望怎样,也是用形象来说明的,不会直接地去呼吁,那多没意思。 面对时代,你无法阻止一些东西,时代太强大,是钱塘江大潮,你还是别去惹为好,但你可以写它,描述它,赞美它或者诅咒它,都行。当下的社会,改革开放,就是开发与保护的矛盾。这个矛盾出现的时候,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甚至人的心灵都会受到裹挟和侵扰,造成一些无可挽回的破坏。比如,我写的这个小说里,把镇山石挖了,把保护人们生命的药王蔸挖了,生态破坏了,各种各样的灾难和疾病就都来了。我们地球的日子还很长,总要留几座自然的山脉给子孙后代享用吧。 前几年我到怒江去,感慨很多。那一条路生态保护做得很好。为什么很多热爱生态、热爱自然的人要到那里去?因为只有在怒江边上,你才能听到河流自然流淌的声音,才能看到河流原始的模样。 澎湃新闻:近几年你的写作是和神农架紧密相关。有的人可能出于某种便利性,给你贴上一个地域性的标签,说你是“神农架代言人”,你本人会不会接受这个? 陈应松:我不是神农架代言人,我没有这个本事和能量,神农架也不会找我。我现在是神农架的一个暂住者,神农架官方是什么人我一个不认识。只是说,我是一个神农架的热爱者,我喜欢神农架,我写神农架,神农架喜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过去我挂职时的领导较熟,但他们也不怎么喜欢我,说我专写神农架的阴暗面,后来我的神农架小说获了鲁奖,他们的态度才改变,不过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所有神农架的朋友都把我当神农架人。在改革开放30年时,我被他们授予神农架改开30年十大新闻人物,让我很高兴。神农架还是挺感谢我的,特别是有一批神农架的文化人,与他们是好朋友,学生也不少。我如果哪一天不在这世界上了,麻烦给我几尺地,让我永久长眠在那里吧,因为我太喜欢那地方,我的一生是她成全的,也是她塑造的。我愿意成为森林永远的瞩望者和守护者。 澎湃新闻:与国内外其他生态文学作品相比,你认为你自己的作品在哪些方面是有别于他们的?你怎么评价我们现在的生态文学面貌? 陈应松:把我归类为生态文学,我真的很高兴。中国当代的生态文学相对的比较弱,但是已经有很多作家做出了巨大的成绩,我不算最优秀的,也不算最吃苦的。我和他们的区别比较明显,他们更多写动植物本身,我不一样,主要写人,我也不会把动植物写的那么可爱、单纯、童话,我写兽的人性,人的兽性。 比如我有一个中篇小说《豹子最后的舞蹈》,写一只最后的豹子怎么向猎人复仇。说白了,这里面人就是兽,兽就是人。我为什么主要写高寒山区的人,写他们的生活现状?因为我本质上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有强烈介入现实的企图。而人的生存也是一种生态,整个生活在这片区域的植物、动物、人,都是大生态的一部分。 当然,国外的生态文学,他们和中国作家的关注点不太一样。他们关注地球的未来,思考地球和人类往哪里去,他们因为生态保护得较好,所以没有我们的这些现实矛盾吧,但中国作家必须写现实。说到底,生态问题是现实问题。 澎湃新闻:有人说你的写作走的是一条残酷的路,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你的温情,感受你对人物的恻隐之心。 陈应松:我的小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残酷,但深处甚至外表就有温热的怜悯恻隐,完全是一个正常人心,冒着人间的热气和烟霭。怜悯和恻隐是人类同情心的表现,一个人会油然而生。我虽然写生活残酷,但我从不会写一个人很坏、很阴暗,一肚子坏水。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这种心机,也没有这种心理。正视生活中的残酷和苦难,再正常不过,除非他的眼睛是野兽的非人类之眼,没有悲悯之情。正视别人的苦难,不过度渲染,不刻意夸大,不拿它攻击人,不制造仇恨,这没有什么不对。 我说的是20年前的神农架,是过去曾经有过的生活。你去海拔两三千米,白云飘飘如仙境一样地方,钻进人家的屋里,发现基本是家徒四壁。他们是怎么生存的?生病了怎么办?怎么种地?怎么把山下的物资运上去?真是无法想象。这样的生活你不去写就是犯罪,我不去问责是谁造成的现状,我写写还不行吗?这个地球上有十大难解之谜,有一个是“谁使大地上布满了人”。我写在根本无法生存的高山上却艰难生存着一群人,这多有意思,我其实就是这样写的,我在探寻是谁使高山上布满了人。 有一阵子,文学圈批判“底层叙事就是苦难叙事”很时髦。那一段时间,很多批评家都在声讨我,搞得我很沮丧。我后来发现他们根本没看我的小说,只是赶批评的潮流。 澎湃新闻:从“公安水乡系列”到后来的“神农架系列”,在你历来的创作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一以贯之的?或者说始终坚持的信念? 陈应松:一个作家肯定要坚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变的,守恒的,一生坚持的。我坚守的东西,一是说真话,二是讲人话,三是写自话。具体说来,就是真心,真性,真情。我认死理,不当墙头草,不搞时装秀,吃清水白菜,穿暖和衣服,不袒胸露背,不招摇过市,不炫耀身份,不大言不惭,不歇斯底里,不胡吹毬侃,不搞文学以外的勾当。能写多少是多少,适可而止,不虚报成果,不夸张本事,秉持“老实为文,忠于职守”的原则。别的,文学上的东西,我写底层,写偏远,写自然,写生态,一以贯之。特别写自然,犹如品美酒,有特殊嗜好。我希望自然的世界包裹我,无论是平原,是湖区,是山川,是荒漠,我都热爱。 康德说:“对自然美抱有直接兴趣,永远是心地善良的标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在《森林沉默》后记里也引用了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里的一句话:“那些感受大地之美的人,能从中获得生命的力量,直至一生。”真正去写大自然的人,内心一定是温热的、柔软的、善良的、美丽的。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