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国,是最亲切的名字。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唱给祖国的歌声,一直是音乐文学创作中最为动人的旋律。本文试图把当代有关祖国的歌词创作中的优秀作品来一次“史”的梳理,力求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以就教于大家。 笔者粗浅地认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爱国题材[①]音乐文学史,是抒情主人公(主体)“我”或“我们”与抒情对象(客体)“祖国”逐渐接近直至融为一体的历史。 一、祖国颂 当无数先辈用鲜血换来的崭新国家在我们手中建立的时候,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人是怎样的欢欣鼓舞。人们按捺不住这巨大的喜悦,只能最直接地唱出这种喜悦、最抒情地唱出对新中国无比的热爱。这期间,曾有大量的诗歌涌现。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郭沫若的《新华颂》等都是诗人情不自禁喊出的赞歌。王莘的《歌唱祖国》尤其以它所特有的音乐文学形式和情词并茂更易于接受的内容,获得了更高的普及率和更长久的生命力。歌者的目光掠过高山平原,黄河长江,对新中国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进行高度概括。“东方太阳在升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在迎风呼啦啦飘扬招展的五星红旗下,在“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的磅礴气势中,在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展望里,中国的音乐文学史以强劲激越的脚步,踏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当激动的情绪稍稍平静的时候,歌手的目光便变得深情,这种深情使他们的襟怀更加廓大,祖国的山川、祖国的历史、祖国的荣辱、祖国的兴衰、祖国的安危……在他们胸中动人地回荡着深情的旋律,祖国的形象也逐渐变得真切,祖国的面容也逐渐变得清晰。乔羽的《我的祖国》(刘炽曲)就是在这种情状下最优秀作品。 那美丽祖国的辽阔的土地、明媚的风光,词作者用“一条大河”的意象准确的涵盖,其词语的深湛、象征意蕴的奇妙深远,使祖国的赞歌具备了一种新的审美格调;那英雄祖国的古老的土地、青春的力量,用花朵般的姑娘、心胸宽广的小伙加以典型概括,使祖国的大地充满了刚柔相济的伟力;那伟大祖国的温暖的土地,遍布和平的阳光,使家乡人民的爱憎情感更加鲜明。整首歌词以纯正的口语区别于矫情的诗,以鲜亮纷呈的意象区别于空泛的词,以纯真质朴的感情表达了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也以足够的力量告诉人们:中国人已经从《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的怨怒中彻底地解放了,如今的祖国属于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高唱:“这是我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与其说《我的祖国》有某种象征意义,毋宁说更有预示和审美先导的意义,单从歌名看,祖国的定语部分“我的”,对80年代的“祖国”歌词创作有着潜在的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一点后面将论及。 “八大”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高潮期,“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正充满朝气蓬勃的生机,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迅速前进。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特点在我国的歌曲创作上也有鲜明的反映,出现了一批豪迈奔放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歌曲,歌颂我们伟大的党,歌唱日新月异的祖国建设,歌唱蒸蒸日上的新生活”。[②]最具代表性的是1957年乔羽创作的《祖国颂》(刘炽曲)。歌词对新中国的时代风采做了一个全景式的观照,以高超的概括力和宽广的诗人胸怀,把祖国山山水水、四面八方的火热的现实生活都包容在这首壮美的作品中: 太阳跳出了东海,大地一片光彩,河流停止了咆哮,山岳敞开了胸怀。啊,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 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高粱红呵棉花白,密麻麻牛羊盖满天山外。铁水汹涌红似火,高楼耸立一排排,克拉玛依荒原上,你看那石油滚滚流成海。长江大桥破天险,康藏高原把路开,三门峡上工程大,哪怕它黄河之水天上来…… 抒情主人公站在祖国晴朗碧透的天空下,俯瞰祖国的万千气象,投以由衷赞美的目光,报以纵情高声的歌唱。无论在内容巨大的概括力上还是在艺术形式的完美上,都标志着这一时期同类音乐文学题材的最高成就。此后,著名的作品还有王莘的《祖国颂》、石祥、刘薇的《祖国一片新面貌》(生茂曲)等,但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没能超越乔羽的《祖国颂》。 用“颂歌”或“赞歌”来界定这些作品,应该说是毫无疑义的。这些赞颂之作的产生是自然的,它与那一特定时代的心理定势相吻合。“最直接地表现内心感情的时候,也最有歌唱性。”[③]这一阶段的合唱歌曲较多,正是群情振奋使之然。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待那一段音乐文学史,也会发现,抒情主人公或者说歌词写作者及歌曲演唱者是怀着一种敬仰之情站在祖国这个伟大的形象之外的,缺少一种“切入”感。几乎每首歌都是比较客观地反映祖国的变化,词家们似乎来不及把自己激越的情绪沉静下来。然而我们不应该对此抱有遗憾,因为这一切源于既是真诚的也是无法抑制的激动,是真情实感的抒发。 二、祖国之爱 文化荒芜期的音乐文学几乎没有好作品可言。十年浩劫的结束,意味着社会主义祖国音乐文学的“二度梅开”。伟大而历尽沧桑的祖国在词作家心中成为更加可敬可亲的形象。人们歌唱她的坚韧刚强,祝福伟大的祖国永远如旭日初升。一首贺东久、任红举作词的《中国,中国,鲜明的太阳永不落》(朱南溪曲)唱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永不落”三个字浓聚了多少深情的寄托和含泪的祝福!每当听到它,我都想起何其芳的诗句:“我听见迷人的歌声,/它那样快活,那样年轻,/就像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在歌唱她的不朽的青春。/呵,它是这样迷人,/这不是音乐,这是生命!/这该不是梦中所见,/而是青春的血液在奔腾!”[④] 尽管这首歌在主调上没有脱出《祖国颂》的模式,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有了很大的新变。经历了一场浩劫的洗礼,人们对祖国今天的来之不易有了深入的认识,一种“敬”意已经渐变为一种殷切的“祖国之爱”。 瞿琮的《我爱你,中国》(郑秋枫曲)是这一时期此类歌词的代表之作。“我”似乎直接承接了《我的祖国》的气度,而“爱”则大大的超越了以往,甚至可以说,“我爱”,是祖国的音乐文学创作新时期的标志。抒情主人公与祖国的距离大大拉近了,情感的浓度和深度也大大加强了——“我的母亲”的形象在当代音乐文学史上充满爱心地挺立起来,几经沧桑却依然丰满强健。这首歌词不是客观地描绘祖国母亲,而是在每一句中都充分体现了执著的“我爱”: 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我爱你青松气质,我爱你红梅品格,我爱你家乡的甜蔗,好像乳汁滋润着我的心窝。 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森林无边,我爱你群山巍峨,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 张鸿喜的《祖国,慈祥的母亲》(陆在易曲),以“长江黄河欢腾着,欢腾着深情,我们对您的深情”、“蓝天大海储满着,储满着忠诚,我们对您的忠诚”的咏叹,把歌手的心灵已经深深地溶入祖国的身上,这种爱,已由外在深化为内在。 张藜的《祖国之爱》、《我和我的祖国》(秦咏诚曲)也是在群众中广为传唱之作:“我和我的祖国,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旋涡。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我最亲爱的祖国,你是大海永不干涸,永远给我碧浪清波,心中的歌。”把个人与祖国的关系诗化于词句里,既鲜明地展示了祖国对于“我”的意义又含蓄地表达了“我”对祖国的价值。 可以说,“我”和“我的祖国”,是不同于《我的祖国》年代的新时期词作家们的集体思考。张藜的这首作品的名字也恰好代表了这样一种新时代的创作取向:“我”不再是那种对祖国的敬而远之,而是投身于祖国的怀抱成为她的身躯的一部分。但我们又发现,这里仍然还有一种心理的距离,仍然没有达到血肉相融的“一体化”,“我和我的祖国”——一种并列关系。此间的优秀之作还有晓光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施光南曲)、刘合庄的《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李正曲)等。 “时代变了,或有许多东西,不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了,有许多基本上还适应新时期要求的东西,也要赋予新的内容和形式。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是一个潮流。”[⑤]在这变革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批佳作,我认为,正是它们把唱给祖国的歌声在80年代中后期引向了更具审美品格、更富思想内涵的新境界。它们是《我的中国心》(黄霑词、王福龄曲)、《我们拥有一个名字——中国》(叶佳修词曲)、《江河万古流》(苏叔阳词、王立平曲)等。 三、我们就是黄河泰山 我们的祖国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推动下,音乐文学工作者的视野空前广阔,思想触觉也格外敏锐。优秀的词作家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和创作气度,他们不屑囿于“小我”的情绪泥淖,而是在肯定自我对于社会的价值的基础上,把祖国的大我与个人的小我融为一体。正当人们期待着与时代合拍的创作的时候,传来了作为炎黄子孙的“我”那雄浑而优美的歌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中国人的血液中国人的心。化作长城黄河,他们有着无与伦比的民族自豪感和百摧不毁的民族气节:“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静脉是长城,动脉是黄河,五千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拥有个名字叫中国。再大的风雨我们都见过,再苦的逆境我们同熬过,就是民族的气节,就是泱泱的气节,从来没变过。手牵手,什么也别说,哪怕沉默都是歌,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苏叔阳的《江河万古流》则更简捷地表达了这种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自信心:“长江流,黄河流,滔滔岁月无尽头,天下兴亡多少事,莽莽我神州,情悠悠,思悠悠,炎黄子孙志未酬,中华自有雄魂在,江河万古流。”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我国的歌坛上,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通俗歌曲创作走向了繁荣。80年代中后期,成为爱国歌曲创作的黄金时期,大量的创作都表明,祖国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的成就就是祖国的成就,祖国的歌就是我的歌——我和祖国已合二为一,我们就是黄河,我们就是泰山。这种全身心的情真意挚的歌唱,达到了音乐文学创作上前所未有的艺术真实。 如果说曹勇的《我们就是黄河泰山》(士心曲)是一篇我们与祖国融为一体的宣言的话,陈奎及的《中华美》(郭成志曲)、任志萍的《心愿》(伍嘉翼曲)等则是更进一步,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同时作为歌者与被歌者,“我们”与祖国已无法分开,血肉连在一起,已经用不着“就是”来认定了。晓岭的《祖国赞美诗》(哲明曲)是一首更成熟的佳作: 我们是相同的血缘,共有一个家,黄皮肤的旗帜上写着中华,盘古开天到如今有多少荣辱和犹患,泪可以流,血可以洒,头却不能(没有)低下。 我们从蹒跚的冬夜,走向春的朝霞,脚步像咚咚咚的(沉重的)鼓点在大地上敲打,最痛苦的土壤会生出最幸福的希望,树要吐绿,草要发芽,古莲也要开花。 过细的分析已经多余,我们只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的祖国赞美诗,已从过去那种平面的祖国风光面貌的描绘或单一的情感抒发,发展到了立体的具有浓厚文化内蕴的词美境地;我们的音乐文学创作,已经伴随着祖国的成熟、伴随着新一代中国人的成熟而变得更加深沉。 这期间的较为优秀的作品还有王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谷建芬曲)、韩静霆的《今天是你的生日》(谷建芬曲)等。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一首刘毅然的《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刘为光曲)。作者准确把握住了祖国歌曲创作的新动向,大胆地把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得更加高大可亲,把“祖国”化为一个相恋的“你”: 在爱里,在情里,痛苦幸福我呼唤着你;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纵然是凄风苦雨,我也不会离你而去。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 你恋着我,我恋着你,是山是海我拥抱着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是血是肉我凝聚着你。纵然我扑倒在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晨曦中你拔地而起,我就在你的形象里。 这里,我们起码能够得出如下三个结论:第一,与“我们就是黄河泰山”比,“你恋着我,我恋着你”似乎多了一句“黄河泰山就是我们”,这种颠倒好像只是形式,实际上这是一种艺术创新,内容上甚至可以看做是一次小小的审美革命;第二,“是山是海是我拥抱你”与以往的“海和浪花一朵”的比喻又是一个倒错,仿佛“我”的形象有不逊于“你”的昭示,这是颇有深味的新意;第三,“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是对近年来歌词创作上关于“我”与祖国关系认识的一个明明朗朗的总结,这个总结是应当引起词作家注意的。 对当代祖国题材的音乐文学史的描述,王健《祖国您听我说》(谷建芬曲)中的一句词是比较恰当的,它概括了这三个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赞美祖国,热爱祖国,我们属于祖国。”几个阶段的演进,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政治反思、文化热、直至优秀民族文化的重新重视,使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了新的演化,一种新的“祖国观”也随着个体生命价值的逐渐确认,深深地融入了每个国家主人的血液之中。个体的自由解放、升华完善,汇成一股股力量,形成凝重的历史使命感和深沉的社会责任感,从而支撑着伟大的祖国刚强自信的形象,闪烁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精神的灵光。祖国大地到处回响着动人的歌声:“重整万里河山,这是我中华的心愿!” (原载《词刊》1991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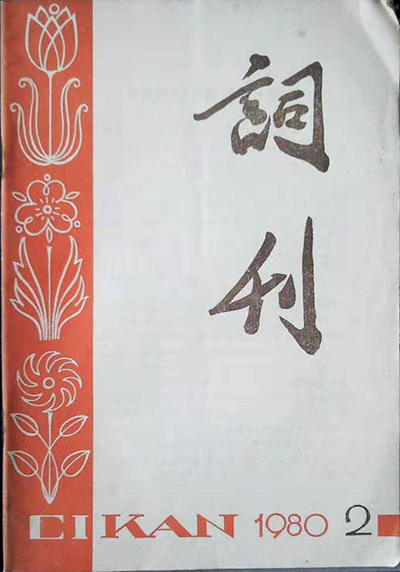 1980年的《词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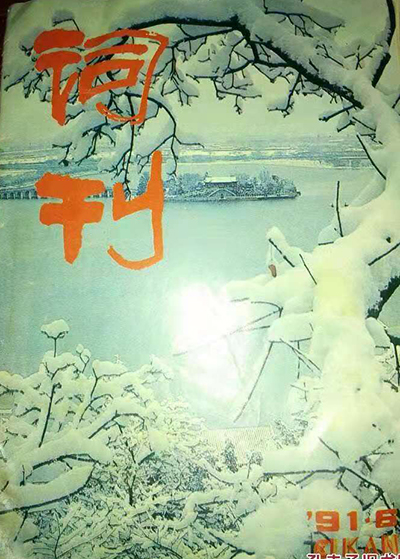 1991年的《词刊》 [①] 用题材划分这种表现的艺术是不很恰当的,这里是为了论述的方便才借用题材作为切入点的。 [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歌声中前进》解说词,梁茂春撰稿。 [③] 张藜《诗歌之路》第104页。 [④] 何其芳《听歌》。 [⑤] 张藜《诗歌之路》第48页。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