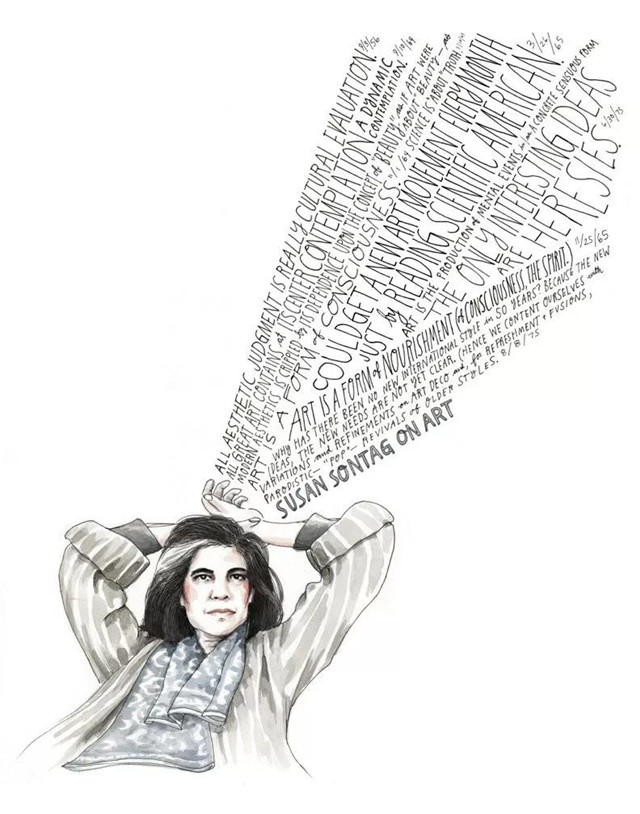 假如这个地球上有谁能决定不死的话,那么非苏珊·桑塔格莫属。她的意志是那么强烈,那么坚定,那么不愿意甘心接受普通人的命运,或者我们其他人注定要承受的结果。她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人,别人会认为人生在世,有些事情注定要做或者注定要经历,她并不把这种想法完全放在心上,因为她是——并且一直都是——超越芸芸众生的人。然而,就在圣诞前夕,她躺在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病床上,做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那些围在她身旁的人看起来,十分像是大限将至。 医生指出了可能出现的最严重情况:没有任何治愈或者缓解的机会。他建议桑塔格什么也别做,用剩下的六个月左右时光好好生活。 在苏珊的诊断结果出来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女管家苏基注意到她有时候会说“哇哦,哇哦”,然后闭上双眼。苏珊告诉她那是疼痛。 不可避免地,这次最近的疾病让人们想起桑塔格在1975年第一次恐怖的癌症诊断。当时她四十出头,被诊断出乳腺癌四期。在她最初咨询的那些医生中,没有一个认为她有一丝一毫的希望,但是她找到了侵略性的疗法,活了下来。从那以后,对平凡疾病和平凡结局的超越,成为了她身体的部分,生命的丝缕——她就是一个寻求治疗的人,她解答她的疾病,仿佛它是一个数学问题,或者是一个最高等级的逻辑拼图。“我闪烁着生存的光辉”,她在八十多岁时写道。与死神的冲突构成了她那黑色魅力以及作家姿态的一部分。在一篇关于摄影的文章里,她写过有关“死亡的性吸引力”,这就是她所呈现的一种性吸引力,那种不断靠近它、吸进它的气味,然后转身而去的危险与兴奋。 她的乳腺癌是极端凶险的,所以康复以后,她的心中更加坚定了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视作非比寻常的观念。换个角度看,是她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视作非比寻常的观念,坚定了她对待癌症的态度。莎伦说道:“因为她是如此生猛,因为她对权威是抗拒的,所以她的本能就是去对抗它。她立即判定医生们是错误的。在当时,第二意见的想法还不普遍……但是她非常勇猛,直接走了出去并且获得了一个(第二意见),然后活了下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她的身份和思想的确证。她没有循规蹈矩,而是我行我素,但是活了下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强化了她之所以是她的一切事物,以及她所作为的那种思想家。那意味着,当她下一次、下下一次再生病的时候,她认为她可以同样化险为夷。”确实,1998年她被诊断出子宫癌的时候,她竭力追寻各种辛苦的、侵略性的疗法,化疗、手术,然后她死里逃生。 在她的笔记中,你可以不断看到她自我神话的行为和努力,她坚持不懈地摄取各种生命的原材料,并把它们整合为一种观念:自己是非比寻常的。当然,每个人都这么做,但是桑塔格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比别人多了百万倍的投入,强度也更大,因而也更加成功。她的神话无所不包,充满诱惑。她的一个朋友评论道,她有一种“明星气质”,不是指她的美貌,而是指她寻求关注的欲望,以及对神话的自觉运用。她在日志中斥责自己:“不要有太多的微笑。”“软弱是一种传染病。强者理所当然避开弱者。”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她想成为那种人的意志,她不断地自我修炼,缝缝补补,仿佛这种意志是一篇文章。她二十四岁时写道:“在这本日志里,我更加坦率地表达了自我,这一点在我表达任何其他人的时候是做不到的,但是不仅仅如此:我创造了我自己。” 从少女时期开始,桑塔格的个人神话就通过她对普通事物的鄙视和疏远而得以预告。她曾经嘲笑她的好朋友斯蒂芬·科赫拥有存款账户和医疗保险,因为那是普通的、中产阶级的人们才有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不会拥有存款账户或者医疗保险。 在她乳腺癌康复后的早期访谈中,她看上去似乎沉醉于与死神的近距离接触。她在1978年《纽约时报》那场几乎令人眩晕的访谈中,是这样说的:“它给我的人生添加了一种凶猛的强度,而那一点一直叫人心旷神怡……知道自己要死了,真是奇妙;它真正地让你认清了事情的轻重缓急,并按序为之。那样的感觉现在已经有几分消褪了;已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我感觉不到彼时的那种迫切性了。某种意义上,我感到遗憾;我宁愿保留住一丝那样的危机感……我认为,同生命和死亡保持联系,是件好事。许多人穷其一生让自己防备生命是一场闹剧的想法。我认为,最好不要试图阻碍这些冲突……当你积极而自觉地面对它们的时候,你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能量。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种尽最大可能去关注的方式。” 在她接受乳腺癌治疗的过程中,她并没有停止工作和思考,也没有停止努力地去工作和思考。在化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她记下笔记,为了那本优雅的、有影响力的论著《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在这本书中,她反对那些围绕在疾病周围的各种各样的幻想。她指出,病人要做好准备迎接治疗的艰苦工作,真正需要的是头脑清晰,理性思维,以及医学信息,而不是诗歌和充满情感的信念。在病房里,她在日志中这样写道:“我已经变得害怕我自己的想象了。”而她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调查和拒绝的正是这种恐惧。她写道,我们赋予疾病的那种想象,那层浪漫,其本身就是暴力的,充满破坏性。 怎样才能不承认自己即将死亡,假如你身边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假如你的身体极尽所能地以生动而令人信服的证据展示着这个事实?毋庸置疑,药物、疼痛、焦虑,还有由于连续四个月躺在病床上而产生的绝对精神压力,都会让人的思维自然而然地受到蒙蔽,但是,也许事实远非如此。戴维指出,她母亲坚信自己非比常人,以及对自己意志的执着,也许已经使她的理解出现混乱,以至于在她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她不相信自己也有撒手人寰的那一天。即使理智让你明白,自己终有一死,你依然允许自己认为:不是这一次。你可以逃避死亡的绝对性,凭借着这样的理念:也许还有两年或者十年,又或是三十年的时光,总之自己不会死于当前的这场病。毕竟,一个四十五岁的人完全有可能感觉自己是二十五岁,完全有可能同自己的实足年龄没有内在的联系,没有从本质上把握住它;诚然,有可能自己要死了,但是感觉自己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 桑塔格也是一个对真理进行创造性叛逆的人。也就是说,她不诚实。她的许多谎言非常典型。她在戒烟问题上撒了谎,她在情人问题上撒了谎,她对一些朋友撒另外一些朋友的谎。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她撒谎是为了保护她为自己建造的神话王国。如果让她在明白无误的事实和她的神话之间做出选择,她一定会选择后者。这就导致了她撒一些奇怪的、不合逻辑的谎。例如,她会在她河滨大道公寓的价格上撒谎,因为她想要人们觉得她是一名知识分子,流浪进一间漂亮的公寓,并没有像更加布尔乔亚、更加普通的人们那样在房产上花大笔的钱。这种谎言很有趣,因为它们服务于她一直在意的那个自己创造出的自我形象;换言之,她会扭曲外部世界,以适应她内心为自己人生所设定的强大画面。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做。此处,人们想象她最大的谎言,就是她正在恢复,同时她迄今为止所设计的最大神话,就是她总能活下去,总能华丽地战胜死亡,并全身而退。当一个人撒谎是为了保护并且强化他的神话,他是不是也在自我欺骗? 看着自己的母亲一日不如一日,戴维内心在挣扎,充满矛盾:一方面是母亲对于疾病的智性态度,这种态度奉逻辑和理性为圭臬,以科学和明晰为准绳;另一方面,则是病房里阴郁的事实。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列出的那些理念,具有无法抗拒的纯洁和魅力,然而时过境迁,此刻的桑塔格如果有双慧眼,能洞察信息,那么她也许早就确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在这次与癌症的最终对抗中,她需要的不是隐喻,而是安慰,她需要幻想,她需要难得糊涂。最后,桑塔格无法在没有隐喻的情况下,同疾病共存;她需要战斗的理念,即使在战斗失败之后。看到她笔记本中有些只言片语被涂掉了,会让人觉得有些意思。在第一次生病期间,她写下:“我感觉就像是越南战争。我的疾病具有侵略性和殖民性。他们在我身上使用化学武器。”她把这句涂掉了,因为她决定不用这种方式思考疾病,因为她严格要求自己保持智性态度——不把疾病浪漫化。然而,就在这些钢笔字迹之下,我们还是能够看到那种运用战争和战役作为隐喻的思维方式,这是她的自然倾向:无法抗拒地想要成为一名战士的本能。 大家都有一个疑问:该如何告知大众。有一个官方立场,但是这个官方立场不能表达确切的真实情况,而要更加接近桑塔格身体健康时在脑中描绘的同疾病的英勇战役。不断有人打电话来问情况,例如《纽约书评》四大创始编辑之一的芭芭拉·爱泼斯坦,还有斯蒂芬·科赫,他们说苏珊更喜欢在纽约接受治疗,并且在当下的阶段,“斯隆·凯特琳”能够给予她与西雅图相同的治疗;他们不提移植手术失败了。事实上,他们给人的印象是移植手术没有失败。“也许这无关紧要,”莎伦在给戴维的信中说,“但是你知道流言蜚语,人言可畏。”一些剪接事实的行为是顾虑桑塔格的隐私;有一些也许反映了桑塔格自己观点的磁力场,或者那些身边人认为是她的观点:对乐观主义疯狂而不切实际的坚守,对死亡固执的蔑视。对外口径是她处于康复之中,并且这种口径不能改变。迟早,这会让她身边的绝大多数人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在该口径中她的位置不能改变。她卡在那里,固定在那里,就像琥珀中的虫子,不久以后会有一些推测、一些令人不安的想象和猜疑:她不再是写出那本书的人了,不再是睿智的、神通广大的、永远可以康复的理论家。 治疗确实在继续。毫无疑问,仅仅为了让她舒服点,也得这么做。戴维与医生们考虑了试验性药物。莎伦在谷歌上搜索两种被讨论过的药物:法尼基酰转移酶抑制剂(zarnestra)和氯法拉滨(clofarabine)。她给戴维发了一封电邮:“它们看上去都比较神奇……要是这东西管用呢?”在某种层面上,他们都还在等待灵丹妙药,因为当时苏珊从床上坐了起来,而且情况不错。在某种层面上,她的意志让他们深感敬畏,也深受影响。人们无法想象她将会死去,她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那个不死之人。 桑塔格过去一直都在绝境中工作。在1976年12月因为乳腺癌接受一轮化疗之际,她下定决心要在一月初以前完成《论摄影》(On Photography),她做到了。在第一次癌症的整个炼狱过程中,她一直在努力寻找将该经历付诸笔端的方法;她不断揣摩技巧的问题。在治疗最紧张的时候,她写道:“我现在知道该如何应对’我’,拒绝个人色彩、远离自传体。” 因而,她在病床上写下拉克斯内斯作品的导读:“时间和空间在那个梦小说(dream novel)中变动不居。时间总是能够被召回。空间是多重的。”临结束时,她不断地变换着文字。然而,这就是她一向的工作方式。当然,对于某一类人而言,导读一个冰岛的实验小说,将其引入世界,是一种肯定生命的行为。非常年轻的时候,苏珊在给一位情人的信中写道:“你务必先知死然后生,艾琳,务必要知道生命临近终结的脚步急促而紧密。”你可以看到,贯穿她那些随意写下的简短文字中,有一条主线,那就是不相信死亡,不接受死亡,仿佛人们可以选择。在一封信中,她提及她的法国编辑:“当我在巴黎时,我没有给保罗·弗拉芒打电话,不过我当然迫切地想知道《死亡匣子》的法文译本情况……我依然很难相信莫妮可死了,我猜想没有给弗拉芒打电话的一个原因是,打这样的电话会让莫妮可的死亡在我心中更加真实。”这就是标志性的桑塔格(不是写作《疾病的隐喻》的那个直面坚硬事实的桑塔格,而是写小说和笔记的更加狡猾的、一厢情愿的桑塔格),有着魔术般的思维:一个人可以撤销死亡,可以使其“不再真实”,可以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死亡。在被诊断出乳腺癌的很多年前,桑塔格在笔记本中写道:“几天前想到自己的死亡,我有了一个发现。我意识到,迄今为止我的思维方式同时具有太抽象和太具体的特征。太抽象:死亡。太具体:我。”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