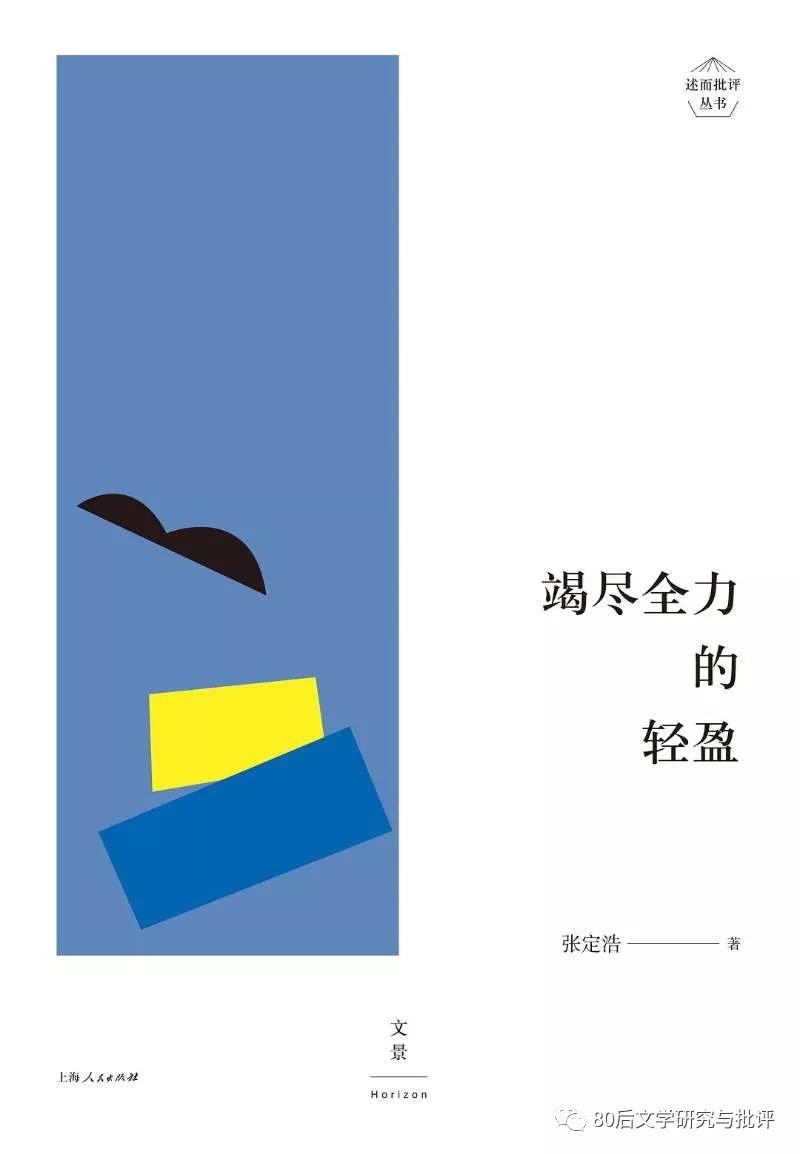 J.D.塞林格逝世之后,像对待任何一位杰出的已故作家一样,我们一直以两种方式在缅怀他,一种是重新咀嚼他乏善可陈的轶事,而塞林格拒绝轶事的隐居生活旋即成为最大的轶事;另一种是重新解读他为数不多的小说,貌似同情地理解霍尔顿和格拉斯家族的精神境遇,貌似公正地评价其社会意义。而这两者,很不幸,恰恰是塞林格本人深恶痛绝的。 站在一位杰出作家的个人生活和文字作品面前,为了不惊慌失措,每个评论家都有各自一整套固定的逻辑,和确定性的判断。而逻辑和确定性的知识框架,却是塞林格一生都力图在扔弃的东西。在《特迪》,这篇《九故事》中写作时间最晚也是压轴的小说中(此时是1953年,《麦田守望者》升起的巨大蘑菇云已经照耀美国两年),那个十岁的小男孩特迪教导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逻辑正是你首先要丢掉的东西……你知道《圣经》里说的亚当偷吃伊甸园里的苹果吗?你知道那只苹果里有啥东西吗?里面有逻辑和知识。那就是《圣经》里所有的东西——你所要做的,就是:如果你想看清楚事物的本质,你就得把这些东西全部呕出来。” 对逻辑和知识的弃绝并不令塞林格简单地走向宗教,作为一位艺术家,塞林格只是相信并尊重,生命之树的复杂、暧昧、模糊和不可化约,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生命最深处的不可交流,而这正是不可以被任何逻辑、知识乃至道德的取景框所捕获的、最真实的存在。面对最真实的人的存在,言辞是无力的,理念是苍白的,生命几乎是个无法表述的秘密,然而现代艺术家的任务,恰恰就在于讲述这个无法讲述的秘密。这几乎是一个悲剧英雄般的任务,而艺术家所能凭恃的,唯有诚实。“有一天,乔伊斯,”53岁的塞林格如是教导他那位18岁的情人,“你会只写那些实实在在的、真实的东西。诚实的作品总是使人们的精神紧张。于是他们想方设法把你的生活搞糟。从现在起的很久以后,会有一天你不再在乎去取悦谁,也不再在乎别人对你说什么。到那时你才能最终创作出你真正擅长的作品。” “修辞立其诚”,和“认识你自己”,这两句中西思想最深处的古老铭言,可以说回荡在塞林格全部的作品中,尤其是到了《西摩:小传》,这部几乎是塞林格最后的作品,在我看来,正可以视作理解塞林格全部文学思想的一个入口。通过让格拉斯家族的老二巴蒂为早逝的长兄和偶像西摩作一番精神素描的方式,通过叙述者极度自由、凌乱却忠实内心节奏的讲述,塞林格已经突破了所谓小说文体的局限,“跟着自己的心写作,写什么都行,一个故事,一首诗,一棵树”,这是西摩对巴蒂的教导,也是塞林格的自我证悟。 与此同时,又必须把塞林格的这种证悟和简单的意识流写作或者罗伯特•格里耶辈的自动写作相区别,后者归根结底只是一种写作技巧,从根本上已经背离了艺术家的诚实,而塞林格所谓的“跟着自己的心写作”,是在写作技巧层次之上的,它源自一个有志向的小说家在死之前会面临的、类似宗教式的终极问题:你写时确实全神贯注了吗?你是写到呕心沥血了吗?以及,你写下的,是你作为一个读者最想读的东西吗? 对这些问题的苦苦追问和探索,使得塞林格的诸多短篇小说显得如此精致。用精致来形容塞林格似乎有些怪异,因为表面看上去,那些构成塞林格小说主体的对话,都是凌乱、片断、言不及意和暧昧模糊的,然而,这些对话却是绝对真实的,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会说出的言辞,是从真实而丰富的存在中剥落的一地真实的碎片,而我们置身于小说内外的每个人,都只能通过这些碎片,去窥测另一个人,以及世界。有如林间错综小径,并不通向某个确定终点,而如果我们能俯视整个丛林,就会发现这所有看似芜杂的林间小径又呈现出某种精心建构的秩序。譬如《抬高房梁,木匠们》,那被塞进同一个车厢里的四五个陌生人之间所展开的穿插对话,宛若一部公路电影,追求的是此时此刻一个小空间内氛围和气息的准确还原,在这个意义上,塞林格直接秉承了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以来的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传统。 有一种意见,认为隐居生活和种种宗教修炼,让晚年的塞林格逐渐脱离现实生活,以致写作日渐枯涩。持这种意见的人,大概都没有真正写过小说。对一个小说家而言,正如詹姆斯•乔伊斯和朱天文都看到的那样,最重要的生活在25岁之前就已完成,剩下的岁月,只是在观察,以及不停地咀嚼过往。塞林格的低产,我想应当视作其诚实面对内心和认识自我的结果,他已经写下他最想说的全部话语,他已经写下了他在一个精神苦闷时代里感受到的全部善与真,他不必再为了取悦任何人而滥用文字。 “跟着自己的心写作”,这番塞林格的自我证悟,在一个文字过剩的时代,同样不断地提醒着我们每个把写作当作志业而不是职业的人。在我看来,这才是塞林格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 2010年3月 作者简介:张定浩,1976年生于安徽,现供职于《上海文化》杂志。出版作品有文论随笔集《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批评的准备》《爱欲与哀矜》《一种真实》《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诗》,诗集《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等。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