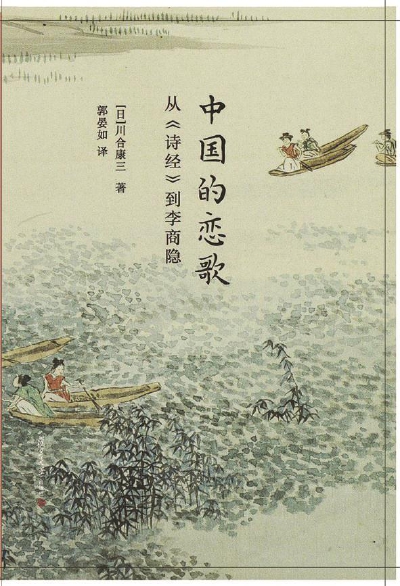 《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 川合康三 著 郭晏如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诗词一直是海外汉学界研究的热点,海外学者的研究不仅推进了中国古典文学在域外的传播,也为我们提供了富有新意的视角。一些学者努力尝试着去贯通殊异的文化背景,往往能从一些我们自己早就习焉不察的现象中寻绎出新鲜隽永的意味。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近著《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川合康三是日本汉学界名流,这一次,他从爱情这个人类共通却又很难沟通的话题入手,涵泳中国古代的恋爱文学,尽管考察的时限仅截至唐代,却涵盖了诗歌、神话、辞赋、小说等多种文体,试图既从中发现“所有文化圈共通的要素”,又揭示出“中国独特的要素”。 超脱于单一的文化背景,使他对李白、陶渊明、鱼玄机的看法别出心裁 全书最别开生面的片段,正是从 “世界文学”的立场出发,对古今中外不同的文学传统时时加以审视比照,特别着重评述了中日恋爱文学之间的异同嬗变,从修辞技巧、内容主旨乃及传播接受等多个角度着眼,深入浅出地考较评析这些作品同工异曲而又各出机杼的特色。 作者论及汉乐府《上邪》中罗列了众多匪夷所思的自然现象,诸如“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等等,以此宣示矢志不渝的情意,就说像这样通过讲述不可能的自然现象,来表达希望恋情持续的修辞手法,在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中就开始大量出现,是日本恋爱文学所擅长的,在中国同类作品中倒是比较少见,从中也可以看出中日在表达感情上的不同。在介绍唐代女诗人鱼玄机时,不仅提醒读者留意森鸥外的小说《鱼玄机》,还特意指出她在《情书寄李子安》里抒写对恋人的怀念,“像这种有特定的某人对某人的思念的诗,在日本的相闻歌里司空见惯,可是倒不如说相闻歌是特殊的,过去西欧和中国的情诗,都不是特指,而是普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鱼玄机的诗是珍贵的例子”。 有时候即使并未明确言及参照的对象,在解读中也时常呈现出新颖独特的视角。在讨论陶渊明的《闲情赋》时,作者就摆脱了以往用道德标准来加以衡量的窠臼,特别强调赋中反复铺陈个人愿望无法达成的憾恨,指出怀着妄想却实现不了的滑稽,“是陶渊明独有的怪异感”,而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谱系中,类似陶渊明这样“把失意的男性当作中心非常罕见。这种失意不是深深的绝望,而包含着自嘲和揶揄”。在评析李白《玉阶怨》中“玲珑望秋月”时,则指出因为语序的自由和暧昧,反而极大地拓宽了“玲珑”所指涉的范围,“不仅月亮’玲珑’,眺望它的女子也‘玲珑’,进而不仅是女子,在这以前提到的‘玉阶’‘白露’……女子和她身边的一切都蕴含在‘玲珑’当中”,由此使得作品的意蕴更趋丰富深永。这些别出心裁的分析评断,虽然仰赖于敏锐而细腻的文学体验能力,恐怕也和作者超脱于单一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从广阔的视野去考察“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文学”,也会造成过度诠释 不过在作者娓娓道来,涉笔成趣之际,有时也难免略有疏失错谬。比如在介绍西晋诗人孙楚将悼亡之作出示给友人王济时,他顺带说起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名号就来自和这两人有关的“漱石枕流”的故事,“这不在《世说新语》里,而是《晋书》卷五六《孙楚传》的记载”。其实“漱石枕流”一语最初正见于《世说新语·排调》篇,《晋书》的相关记载也是源出于此。夏目是日本的国民作家,川合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中日文化的共性,而其中出现偏差,则说明他讨论时对中国文献有疏忽。 作者在努力贯彻其初衷——既从中发现“所有文化圈共通的要素”,又揭示出“中国独特的要素”——之际,有时还不免偏执一端,过分注重“所有文化圈共通的要素”,而相对忽视了“中国独特的要素”。 比如在讨论阮籍《咏怀诗》中“昔日繁华子”一篇时,他就对其在整个《咏怀诗》中的意义感到困惑。诗作从安陵君、龙阳君此二人的角度出发,表达了“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的深切期盼,川合康三不解的是,《咏怀诗》的特征是思绪百般摇摆,但都是内省和思辨性的诗。相比之下,“昔日繁华子”歌咏的欢愉在 80多首《咏怀诗》中确实显得格外特殊。不过,亲历纷乱的阮籍在创作时本就习惯隐约其辞,此诗表面上虽然表现安陵君与龙阳君之间的爱恋,可其主旨恐怕正如前人所推断的那样,“言安陵、龙阳以色事楚、魏之王,尚犹尽心如此;而晋文王蒙厚恩于魏,不能竭其股肱而行将篡夺,籍恨之甚,故以刺也”(《文选》五臣吕延济注)。中国古典文学中一直就存在着以男女恋情来喻指君臣关系的悠久传统,阮籍也深深沉浸在这一传统之中,此诗不过是由此承袭衍生的一个变例而已。作者竭力要从以往的解读模式中挣脱出来,将其视作单纯表现其二人爱恋的作品,似乎缺少了对这一古典文学传统的同情之理解。 作者特别注重从广阔的视野去考察 “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文学”,可有时过犹不及,也会造成过度诠释。比如在研读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时,尽管提到清人冯浩曾认为此诗是“寄内”之作,但他也明确意识到,“在日本,有‘北の方’这种指妻子的词,但在中国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意思。从写作的时期来看,说是送给妻子,也有不妥当的地方”,可知无论从语言习惯还是从诗人行踪来看,“寄内”说都缺少确凿无疑的佐证。可惜兜兜转转纠结了半天之后,他却依然认定“‘北’这个暧昧的说法,似乎也暗示着对方是密不可宣的异性”,推测诗人寄赠的对象应该是某位不知名姓的神秘女子,潜意识中大概仍受到日语使用习惯的影响而以彼律此。将此诗视为“寄内”之作固然不足凭信,转而指实为寄赠给另一位私下爱慕的异性,似乎更是虚无缥缈而显得牵强附会,反不如近人俞陛云所说的那样,“诗本寄友,如闻娓娓清谈,深情弥见”(《诗境浅说》),解说虽然平实无奇,恐怕更可信据。探寻“共通的要素”,本来是藉此参照比较,以便更好地理解“独特的要素”,可一旦畸轻畸重,甚或本末倒置,却很可能事与愿违。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