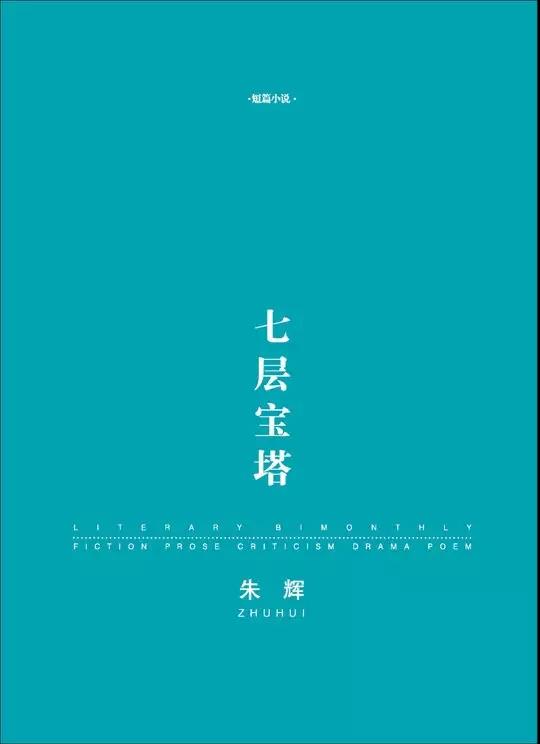 对于文学,我是想的时候多,写的时候少。每天写,日产几千字甚至上万字,对我而言,那是疯了。近年来我只写短篇,满负荷工作,一年最多四五个。大量的时间是读书,还有,乱想。 有一种迹象:为人不谈《红楼梦》,纵谈诗书也枉然。不谈《红楼梦》似乎已开不了口。好吧,我也来说几句。我奇怪的是,那么多人吃红楼饭,或者喝红楼茶,可为什么多考据,却绝少有人从写作学角度去研究红楼梦呢?谁写的,谁批的,谁续的,那是几百年前的事,大概永远也搞不清,是不是正因为有乐趣,无风险,才更令人趋之若鹜、乐此不疲?但我觉得,把红楼梦研究搞得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好玩是好玩的,但意义不那么大。一部伟大小说摆在面前,为什么不多研究它好在哪里,我们可以如何借鉴?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我更关心这个。 就说大观园吧。它是女儿国,是谈情说爱、拈酸吃醋之园,也是勾心斗角之地,但它不是空中楼阁,不是无所凭依的雾中楼台。元春是大观园建立的缘起,也是它上方的悬索,差不多就是命悬一线的那个索。大观园是相对独立的,但应该注意到,它同时却也通过几座“栈桥”,与外界相连。大观园富贵温柔,莺声燕语,但这几条与外界的通道,几次与外界的来往,却是大观园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社会背景。袭人从大观园回家,她的平民之家与大观园形成了通连和对比;晴雯被驱逐出园,那一番惨景,与袭人的家境一起,构成了环绕大观园的市民社会。这是近景。刘姥姥的三进三出,出尽洋相,却巧妙地为大观园布设了当时农村生活的远景。 元妃省亲让大观园和天家相接,袭人晴雯连接了市民社会,刘姥姥通向了农民农村,傻大姐捡到的“妖精打架”则暗示了不明确的更多隐秘通道。所以大观园不是全封闭的,它是活的。作者开的这几个门,通天达地,大有深意,也极尽巧思。 所以可以浓缩和象征,可以建设缩微景观,但是,它得透气。有气才活。 小说要塑造人物。可我们为什么轻忽了外貌描写呢?你要表现性格,外貌难道不是性格之表?哪怕表里不一哩。我们希望人物立得起来,希望他走进人心,那给他个外貌,有的时候简直就是前提。姑娘小伙相亲,讲究眼缘,第一眼看的啥?还不就是外貌?生活逻辑也是小说逻辑。姑娘小伙很有道理。 “脸谱化”当然不好,但没有脸恐怕也不好。一个面目不清的人,在小说里晃荡,这是现代派的路数,我也干过,我的小说,有主人公通篇没有名字。但是对所谓现实主义的小说,外貌有大用。京剧的脸谱,忠奸善恶,阴鸷豪爽,虽说简单化了点,其实也便捷。 小说家需要有画静物的能力,但小说从整体上说并不是静物。小说要动,灵动;小说人物也要动。要写好人物的性格,让他遇到事件、经受考验是个好办法,有的时候还要对他施加压力。要写水面,可以扔个石头;写锣鼓,最好去敲几下,“偷来的锣鼓打不得”,但小说家要会敲锣打鼓,能敲出花式更好。人家搞古董的经常在电视上示范,看瓷器是否有裂,用指关节敲敲,这一招连假专家都会的。只会用眼扒着看,何其笨也。 一个人,面对饭桌:拿起一根筷子,用力拗断,筷子的结实度,人的力量,都出来了;拿起一双筷子,啪的拗断,这是情节,有意思了;抓起一把筷子,用力拗,双臂肌肉凸起,面红耳赤,但筷子不断,这里头有哲学了。 好小说大多有一点哲学。有的时候,素材中自带哲学,另一些时候,哲思早已在跑在前面,等着材料围拢过来。这都没关系。但形而上是重要的。 《七层宝塔》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这篇小说对我来说是个异数,它本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某一日,我们去参观“农民新村”,看到那些目前尚还是农民的“新城市人”,我突然心中一动,觉得可以写个东西了。我想了一年多,终于找到了小说的 “关节”——我称之为小说的“腰眼”;真正打字,也就半个月,很顺。事后回想,写出这个东西是有因缘的:我17岁之前生活在小镇,我熟悉那里的人和事;我大学学的是农田水利;我的妻子是水利专家,专业是城镇规划,她难免回家跟我叨叨……这些都是准备。一堆柴火,只需要一根火柴。 2018年8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