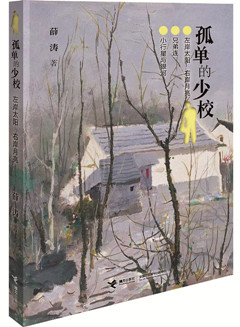 薛涛对于何谓写作、何谓童年,始终保持着一种醒觉。他对他笔下的文字心中有数。倾听、沉思、探索,寻找恰好的表达方式,抵达文学的核心地带和人性的核心地带,是他矢志不渝的追求。以文字对抗孤独和虚无,以文字培育勇气和力量,书写就真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意义追问的自然结果。薛涛骨子里是一个诗人,同时兼具哲学家的气质。他很率真,同时很深沉;他很幽默,同时很严肃。 小说《孤单的少校》反映了薛涛抵达童年世界的深度与广度。故事由实入虚,由写孩子们之间的“战事”起篇,逐渐深入童年精神生活的腹地,继而结束于充满形而上意味的隐喻之中。故事写得好看,并且耐读,行文简洁、幽默、有力量,是一部我愿意推荐给孩子们的书。尤其对于男孩,读过这本书就会更清楚地意识到,世界很大、很丰富、很有意味。当你投入到真实的世界中去时,这个世界的意义将会自动展现在我们眼前。 孩子,尤其是男孩,他们天生就着迷于游戏,着迷于“战事”。与其说他们着迷于游戏与“战事”,不如说他们对力量、智慧和风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迷恋。像小兽一样,他们需要在幼时演习未来生存的基本技能,也需要养成一种基本的生命格局。这正是小说的要旨,也是作家对于当今孩子的观察和寄望。他想告诉孩子的是,走进游戏厅的虚拟世界是一条狭路,终日与机器相对,终将毁了他们的现实感和现实生存能力。从游戏厅回归大自然,以广大天地及日常生活为背景,才能够真正长大和成熟。 为了突出广阔天地之于孩童成长的巨大意义,小说起篇采用的是与萨特的境遇剧相类的手法。作家创设了一个特殊的情境:让小镇上的游戏厅尽数被砸,让孩子们不得不从游戏厅里走出来,继而观察他们可能会做些什么。人们很快就发现,孩子们并没有因此消停下来,他们仍然“不着家”,成天“野”着,成天“胡闹”。然而,他们真的与游戏厅里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吗?不,他们有新“发现”,他们介入到现实生活的场景中,他们在与自然、与现实生活的接触中重新建立的“孩子国”使得他们寻找到了成长的原初资源和内在动力。 游戏厅被砸后,大街上的孩子们就多起来。他们把网络上的“战事”搬到广大的世界里来了。“最初我们无所事事,在街面上走来走去。后来出了镇子,走在林子里,走在河滩上,世界一下子变大”,“从前在一间黑屋子里”,“现在敞亮了”,“现在的战场真叫气派,大片的林子,长长的河,任凭我们排兵布阵”……从电脑屏幕中的“豆瓣孤城”、“谷粒传说”中走出来的豆子团、谷子团以及兄弟连,就在这广大的天地里制定“战争规则”,宣战、抢占大本营、发明新的战术、停战,再宣战……他们希望“战事”永远不要结束,希望放学后放下书包就往林子里走,往河滩上走,往山顶木屋里走,希望无论如何也要享受一下那个小小的树屋……孩子们乐此不疲,这是他们的“永无岛”,他们的“理想国”,他们自己解决纷争,自己面对尊严、荣誉、规则等问题。 孩子们一本正经,将“战事”弄得有模有样,就使得这部小说自带喜剧色彩;而同时,作家采用《堂吉诃德》式的戏仿手法,用战争小说的套路详细描述孩子国中每次“战事”的起因、过程和结果。豆子团、谷子团乃至后来的兄弟连,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大本营,各有各的辎重,各有各的计策和做派。于是,我们就在这戏仿中大笑,孩子们自己也在这戏仿里大笑、叹息、惆怅,热血沸腾,因为他们无一不在其中看到了那超凡拔俗、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逐渐地,戏仿的修辞意味就被我们觉察到了。 小说中,作家还原了一个本真的、生气盎然的孩童世界,塑造了一群各具性格的男童形象:兄弟连的“我”与乒乓,以上校为代表的豆子团、以少校为代表的谷子团,还有大男孩——那个地质大学毕业的护林员,以及傍晚时分出来打酱油的男孩等等。 他们在释放天性、释放想象,在较量智慧,展现风度。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系统,有自己的行事规则,涉及诸如“我是谁”的宏大命题,乒乓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豆子团还是属于谷子团,归属问题成为乒乓的一个巨大难题。这个孩童时的难题在乒乓长大后一定还会再次出现。坐在椴树下的不谙世事的孩童在鹞鹰的飞翔中悟出:不必依附任何人,你属于你自己。这孩童时的真实难题谁能说与他今后的人生没有实际关联呢? 孩童需在孩童国里长大,同时需要在具体的境遇中长大,他将很自然地在他身处的广大天地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小说中不容易被觉察到的是“大人世界”。这些生长在东北林地、河流边的大人们并不过于干涉孩子国的事务,他们对孩子国的语言和事务虽有点隔膜,却大体还是能够沟通的。他们知道,他们的孩子有一天“胡闹”够了,他们就长大了。他们较为放松地让他们的孩子在“大本营”睡觉,让他们的孩子吃饱了好有力气去从事孩子国的“伟业”。同时,他们把握着分寸,时不时地把走远了的孩子拉回来整一整。孩子国与大人国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和屏障,然而,大人国里的人并不因此而对孩子国的事情大惊小怪,因为,每个人都是从孩子国里走出来的。 当少校争夺木屋的目的被公开,故事就真正进入虚实难分的隐喻世界中。 少校何以非要带领他的谷子团攻下木屋作为大本营?除了“战事”实在好玩,还有一个更切实的目的,那就是,挖开木屋以确认他的姐姐“小行星”是否仍在木屋中。寻找“小行星”、解开“小行星”的莫名失踪之谜开始成为小说后半部分的主要情节,孩子国的“打打杀杀”也终于开始连接上更具体、更开放、也更阔大的现实人生。 乒乓给少校的妈妈留了一根香肠、急急地用嘴吹凉她的方便面——这是有血有肉的细节。这一点与乒乓把夜空看痴了,把待在树屋作为人生最高享受,都是极为感人的童年真实相。乒乓一方面固然对“战争”极为投入,另一方面他已经能够确切地感受大自然之美,也确切地喜欢他的语文和语文老师,甚至觉得要急起直追他那因“战事”而受到影响的学业。这就是长大,很自然地长大。而“我”,兄弟连的大尉,比其他孩子都更对“战事”抱有兴趣,但另一方面,“我”也比其他孩子都更自觉到“战事”终将结束。“我”与乒乓一起经历了对天地之美的重新发现的过程。他们发现了晨昏之别、夜色之美。“羊肠河晚上也不停歇,照样向下游流去。月光在水面闪耀,像一层细碎的银粉。我突然不敢相信桥下面流淌的是羊肠河了。你看它,白天流的是水,晚上流的明明是银子啊!上游银河镇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吧?同样一条河,白天和晚上差别这么大。我不认识你了,羊肠河,我不认识你了,一切。”这种发现自然,与自然对话、沟通的能力对于孩子来说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如果有机会让他们实际接触到大自然,并实际投身到大自然中去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对长白狼的故事那么感兴趣并且能够真正走进长白狼的故事中的原因。 长白狼是一个象征。象征的是逝去的传说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岁月。随着林地的减少,野兽们再无落脚之处,长白狼变成了孤单单的长白狼。当它虏获了在护林员木屋里躲猫猫的女孩“小行星”时,它只是希望“小行星”跟它玩,成为它的朋友,因为它实在太孤单了。然而,“小行星”如何能够理解一只曾在林中叱咤风云的野狼呢。长白狼守住“小行星”,守住的只是孤独和绝望,“小行星”也在孤绝中化成碎片。长白狼与“小行星”的恩怨是一种困局,与善恶无关。“我”在与护林员追逐长白狼的过程中,终于与狼和解,也与孩子国里那曾经轰轰烈烈的“战事”和解。“我”已长大,当“我”仰望头顶上的浩瀚星空时,似乎领悟到了浩瀚星空的神秘含义,“我”的生命在与自然的对话中获得了一种历史纵深感和超越感。 护林员作为一个重要的补充角色深化了作品的主旨。护林员既是林子的守护者,也是孩子国的守护者,更是梦想的追逐者。他是惟一一个完全能够用孩子国的语言与孩子们沟通的人。他知悉少校攻夺木屋的真正原因,他为他无意中所犯的过失(丢失“小行星”)而负疚在心,他是那个坚定地要寻找“小行星”、揭开“小行星”失踪之谜的人。他鼓励并且引导了那一群在林子里、在河滩边“战事”不休的孩子们。最后,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也实现了他的梦想,成为那个向着星空飞翔的人。 成长本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落地即与地接触,抬头即与天接触。在天地之间长养性情,顺自然规律成长,这是现代人习得的最重要的智慧,然而现代人也亲手摧毁了这种生活方式。这正是现代文明的悖论。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是建构的事业。《孤单的上校》呼唤孩子们重新建立与大自然的联系,与自然心性的联系。作家强调尽情地去生活,同时强调在生活中寻找启示,强调沉思和领悟。薛涛时不时借他笔下的人物之口发表他对万事万物的看法,这些看法非常有趣,也很有深意。 这本书用好看的故事和生动的细节建立起强有力的隐喻系统,给予当代人尤其是孩子以启示,这些启示将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