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仍保留口语词色彩。共有379例。如: 【半半拉拉】《二版》“<口>不完全;没有全部完成的:这篇稿子写了个~就丢下了。”——《三版》“不完全;没有全部完成的:工作做了个~就扔下了。” 【大肚子】《二版》“Ê<口>指怀孕。Ë<口>指饭量大的人(用于不严肃的口气)。Ì〈方〉对地主或资本家的憎称。”——《三版》“Ê指怀孕。Ë指饭量大的人(用于不严肃的口气)。” 【哭鼻子】《二版》“<口>哭(含诙谐意)。”——《三版》“哭(含诙谐意):输了不许~。” 3, 表现出方言词的特点。共有118例。如: 【背气】《二版》“<口>(~儿)由于疾病或其他原因而暂时停止呼吸。”——《三版》“由于疾病或其他原因而突然暂时停止呼吸:婴儿~了,要赶快做人工呼吸丨气得他差点儿背过气去。” 【串秧儿】《二版》“<口>不同品种的动物或植物杂交,改变原来的品种。”——《三版》“不同品种的动物或植物杂交,改变原来的品种。” 【耳塞】《二版》“<口>耳垢。”——《三版》“耳垢。” 以上口语词变动的情况用图表显示,即如下:  二、口语词的性质与地位 《现汉》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语文词典的典范是有道理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精心进行了对词语意义色彩的标注工作。“<方>”“<文>”“<书>”“<口>”所揭示的就是四种具有对称性的意义色彩。 普通话词汇系统是汉语词汇的一个共时聚合体,它由各个不同来源的词语汇集而成,形成了绝对的动态演变、相对的静态聚集,杂源而一统、同处而异彩的特色。构成普通话词汇系统核心的是那么具有“现代性”“广泛性”“通用性”特点的词语。把“方言词”“古词语”“书语词”“口语词”与普通话词语的关系稍作疏理,可以用以下两条横轴来表示它们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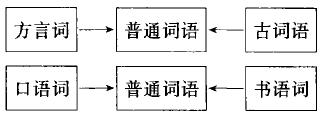 “方言词”主要在使用区域上的狭窄性上表现出差异,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地区;“古语词”主要在使用时间上的非现代性上表现出差异,它们存在于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只在现代语言使用的某个特定场合才会使用到。它们是普通话词汇系统的边缘部分。完全的方言词和完全的古词语是与普通话词汇无关的,只有那些刚刚进入而未彻底沉淀在普通话词汇系统的方言词、古词语,才是我们这里要予以评论的“方言词”与“古词语”。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方言词”“古词语”,及还有其它的一些来源,才使普通话词汇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才能够于动荡摇曳之中汇成词汇的汪洋之势。 “口语词”则是在使用场合上表现出差异,主要存在于非正式的、日常生活的、较随意的语言环境;“书语词”也是在使用场合上表示出差异,主要存在于正式的、书面语、讲究典雅规范的语言环境。显然,这两类词语主要是从使用环境与使用效果上所作出的分类,它们从一俗一雅、一诙一庄、一陋一典中,丰富了普通话词汇系统构成。有俗必有雅,有诙必有庄,有陋必有典,有口语词,必有书语词,二者构成了事物的两极,否则“世界将变得失衡”。不可能只有雅而没有俗,也不可能只有“书语词”,而没有口语词。 词语的分类如同现实事物的分类一样,交叉混杂是难免的,是正常的,追求“纯粹”、“单一”、“非此即彼”只能是一种理想。普通话说“喝茶”,广州话说“饮茶”,“饮”是方言词语,但这个“饮”又是古汉语中很常见的用法。广州话里有许多象“行路”“睇”“企稳”“着衫”这样来自古汉语的词语,故又有了广州话是保留古词语最多的方言的说法。在这里“方言词”与“古词语”就出现了交叉。但人们在一般情况下并不会把这二者搞混,因为一个是从地域的广狭落笔,一个是从时间的古今着眼。剩下的交叉是就是“方言词”与“普通词语”、“古语词”与“普通词语”之间的界线如何切分了。这是一条永远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界线,可却并不妨碍人们继续使用着这样一对概念,不妨碍人们继续在理论上清楚地辩析这两种词汇成分。 交叉混杂同样也会出现在第二种分类中。“口语词”与“普通词语”、“书语词”与“普通词语”之间的界线同样是难于进行非此即彼的切分。意义色彩分类的混杂还远不限于此,在“口语词”与“方言词”、“书语词”与“古词语”之间又何尝不是纠缠在一起呢。但如此种种,并没有使人们放弃这样的分类,其原因就是人们从这样的分类中得到收益。 上面把词语意义色彩的分类用两条横轴来显示,显然那是人为理想化、简单化了的处理方法。稍微逼真地一点地来显示它们与普通话词语的共有关系,可以用下图来示意:  有了上面的认识,再得出以下结论就不难了:为了更深入地认识普通话词汇系统,对词语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意义色彩分类是有必要的;每一种意义色彩的分类都是相对的;要求意义色彩的分类作到完全的纯化、净化是不可能的。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