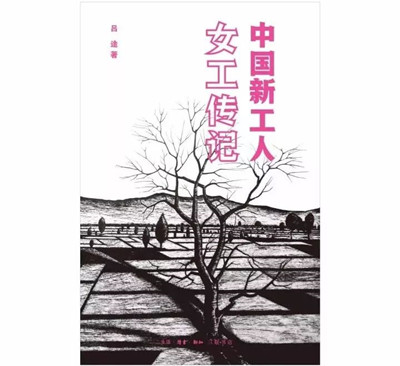|
《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是吕途撰写的“中国新工人”三部曲的第三部。在书中最后,吕途写出了她自己的故事《我的四辈子》。出于个人的抉择,2008年吕途告别了在欧洲的生活,来到北京皮村,参与工友之家的工作,她把这称为她的“第四辈子”。这十年间,她访谈了上百名相熟的或陌生的打工者,去苏州的台资工厂流水线打工,撰写《中国新工人》,任教于工人大学,教了每一届学员,参与新工人艺术团的演出和各项活动,每周还至少在农园劳动一天。她说,“我的一生走了这么久,经历了这么多,好像都是为了这第四辈子做准备”。通过和她接触,读她写的书,可以感受到她的个性中有非常强大的自信和勇气,支持她走了这么远的路,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在平静、琐碎的劳作中坚持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目标。 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这样评价吕途的研究,“她将自己融入新工人群体的命运之中,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心去摸索这个群体的劳作的身体及其痛苦、欢欣,记录这个群体的灵魂的轨迹”。
我的娘家:我的第一辈子 我祖籍是辽宁省岫岩县。听爸爸说,爷爷从小就特别聪明,当初县试,爷爷还得了第一名。奶奶是地主的小女儿,父母疼爱,没有裹脚,因为是大脚,就耽误了出嫁。媒人找到我爷爷的时候,爷爷说:“大脚好,走路稳当。”爷爷和奶奶年轻时正好赶上日本人占领东北,兵荒马乱的,奶奶很担心爷爷被日本人抓去当汉奸。当时,在岫岩县有一所丹麦教会开设的丹国医院,奶奶虽然是旧时代的女性,但是胆子很大,她一个人敲开教会医院的大门,向院长推荐自己的丈夫去学医。就这样,爷爷在丹国医院学了四年护士,学了四年医生,又在那儿服务了一段时间。新中国成立以后,丹国医院被接收为岫岩县人民医院,爷爷在那里当医生一直到退休。我对爷爷印象特别深,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回老家看望爷爷,他每次下班回来一定给我带一穗烤玉米,我最爱吃烤玉米了。 我姥爷是一个画家,我听爸爸讲,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届国画展里还展出过姥爷的作品。姥爷1949年前也做过生意,用做生意挣的钱还买下了几块薄田分给亲人们耕种。听妈妈说,姥爷打算盘是一绝,可以默打,就是说,不用真实的算盘,在脑子里就可以打算盘得出结果。姥爷去世得很早,我没有见过。我对姥姥印象特别深,她的脚裹得很小很小,走路颤巍巍的。小时候,姥姥来我们家小住过一段时间,晚上我经常帮她洗脚,每次我都会问她:“姥姥,脚还疼不疼?” 我爸爸叫林克胜,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学专业,毕业之后有很多经历,后来在《长春日报》做过很长时间的记者、编辑和副总编。爸爸文笔特别好,写过很多文章,出版过自己的作品,七十多岁的时候,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关于中国古诗词格律的三部专著:《诗律详解》、《词律综述》和《词谱律析》。我们小的时候,爸爸每周要求我们三个女儿背诵一首古诗词,然后他给我们讲解,他也出版了自己的诗集《青石山集》,里面还收录了爸爸在我15岁生日时赠我的两首七言古绝,《修身铭二则示三女》: 立国立家首立身,正言正行在正心。 灵境高洁人恒敬,举止文雅自受尊。 温良恭俭让行事,仁义礼智信做人。 当念民族传统久,无愧中华风俗淳。 我父母有三个女儿,我是老三,我大姐是化学博士后,我二姐是工商管理硕士,我是发展社会学博士。我选择了为打工群体服务的工作以后,再加上婚姻上的各种变故,我和爸爸的关系有些磕磕绊绊了。 我妈妈叫吕金华。当年考大学的时候,姥爷并没有被划为地主或者富农。因为姥爷把地分给兄弟们耕种,自己并没有雇用劳动力,但是,不知道是谁诬告,害得妈妈虽然考了很高的分数,却不能去心仪的大学,去了一所小院校学习俄语专业,妈妈能说一口流利的俄文,那个时候有俄国老师直接任教。后来,“文化大革命”了,妈妈随着爸爸走“五七”道路来到农村。妈妈有一个特点,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发出光和热,妈妈很快适应了环境,后来成为村小教师和赤脚医生。“文革”结束后,妈妈回到长春,做过不同的工作,最后一份工作是任长春税务学院的院报主编,同时兼任讲授一些文学写作课程。1997年11月底的一个晚上,妈妈突发脑溢血倒在讲台上,在医院住了十四天,一直没有苏醒过来。妈妈的一生非常平凡,但是她受到很多亲人、朋友和学生的爱戴,给妈妈出殡的那天,全校师生站在马路两侧送行,学生们打出横幅:妈妈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上 学 我1968年出生在长春。考上中国农业大学的生物学院,这是我的第一志愿,我的第二志愿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志愿是长春中医学院。当时的想法就是,或者学农或者学医,为需要帮助的人服务。我在大学的专业方向是植物生理生化,专业课阶段主要学习显微镜下面才能看到的东西,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学习了大田作物等农业基础知识。现在回忆起来,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年。那一年学校规定,刚留校的年轻教师要下乡锻炼,我们四个年轻教师被分到河北武安实习了一年,其实就是麻烦了当地政府一年,啥贡献都没做。没做贡献也情有可原,现在想起来最可笑的是那种“大学生”情结。大学生遇到农民,大学生必须比农民懂得多,不懂也得装懂。大学生学到了很多书本知识,那些知识应该是有价值的,是前人根据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但是那些知识必须和现实结合才是真知识和活知识。认真学习了专业知识的大学生如果愿意向实践学习、向农民学习,肯定比农民能够更全面和系统地理解和掌握农业生产技术。但是,在今天的体系中,农民是农民,大学生是大学生,学者是学者,彼此割裂,而且现在,在农业大学学习好像也不是为了农业、农村服务啊。 1993年到1994年,我在荷兰海牙的社会学院攻读妇女与发展硕士。开始去的时候英语口语和听力很差,头三个月,在课堂上无法参与讨论,因为听不太懂。语言是障碍,更大的障碍是思维障碍。我们每学一个课程,都会讲各种流派的不同观点,我就晕了,我该如何思考和判断哪?难道没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吗?现在回忆起来,我读硕士的一年半,自己的思想和思维并没有受益太多,但是,学习到了一些概念和理论,可以拿到国内生搬硬套。硕士毕业之后,我回到大学撰写教程,开设了“性别与发展概论”这个课程。我很喜欢大学的学习氛围,我教学也很认真,但是我那样的老师实在不合格啊,因为我并不真正领会我的教学内容。我觉得,尤其是对于社会学科来说,教师只有具备了一定人生经历和实践经验,在实践中掌握了真知识,才有资格当大学老师。虽然我的真知识不到位,但是我教学方式活泼,对教学认真负责。有一次出差回来,我获得了人生唯一一次优秀教师奖,而且是校级的,据说是学生匿名给教师打分,全校获得90分以上的教师只有十几个。 1997年到2003年,我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攻读发展社会学博士学位。我要永远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Norman Long教授,可以说,是他把我带入了发展社会学思维的门槛,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我越加理解他的教导。我非常认真严谨地在中国做实地调研,我研究的对象是政府的自愿移民扶贫项目,我研究的问题是:移民搬迁到底有没有帮助解决贫困问题。我选择云南和宁夏作为项目点,在每个地方我都去原居地和现居地做对比调查。攻读博士学位一共历时六年多:进行了两年的思考准备和阅读;进行了两年的实地调研;整整写了11个月的论文,平均每天写作6个小时,又进行修改、评审和答辩。这个过程的确对思维训练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也许自己今天之所以有这样的研究思路、分析能力和写作的毅力,都和那个时候的训练分不开。我的导师是荷兰瓦赫宁根发展社会学系的主任和教授,他是英国人,不会说荷兰语,他所有的博士生都用英文交流和写作。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向导师提问的时候,我永远不会得到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的答复,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一个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的拖拉机的故事:有一个扶贫项目给拉丁美洲一个项目点买了一辆很高级的拖拉机,一年以后,当项目官员去实地考察的时候,发现一头牛在拉着拖拉机的车斗前行,原来,当地农民根本买不起燃料来开拖拉机,拖拉机的配件坏了也无法进行修理,但是,农民没有把拖拉机全部丢弃,而是留下了可用的部分。他用这个小故事告诉了我很多道理。  广州番禺旧水坑,女工午餐的场景 大学教师和咨询专家:我的第二辈子 从1990年到2002年,我一直是大学的一名教师,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在这期间,我也在攻读着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同时,我也做过很多国际发展援助项目的咨询专家,做过很多扶贫项目,去过全国所有的省份和自治区,去做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计划、项目监测和评估。我可能执行过所有驻华的外国机构的项目,包括欧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计划、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国际爱心协会等,这中间当然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情。我觉得做国际项目是非常奇葩的事情。外国机构援助中国政府一笔扶贫款项,需要雇用专家团队进行项目考察和设计,专家团队由外方专家和中方专家组成。1996年,我们执行一个外援的扶贫与环境发展项目,去红河地区考察,我们来到了彝族村落。当一个外方专家和一个彝族村民交流的时候,需要经过下面的翻译过程:英语翻译成普通话—普通话翻译成当地普通话—当地普通话翻译成彝话—彝话翻译成当地普通话—当地普通话翻译成普通话—普通话翻译成英文。想象一下,经过这六道翻译,交流还是否存在?信息还有多少是准确的?遗漏的信息一定超过一大半。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我去湖北一个地区做农民培训,县乡的干部也被派来参加,培训做了一个月,大家相处得越来越好,甚至成了朋友。一个干部朋友告诉我,我们项目里面支持植树造林,亚行的钱来了我们造了一片林,世行来了验收的也是这片林,你们的项目还是这片林,这就是项目套项目。我当时就在想,我该不该把这个告诉外方的项目负责人呢?估计,即使我告诉了外方项目负责人,他也不会向上汇报,因为如果中国的项目没有了,那么他不就失业了吗? 当时做的所有的项目,目标和宗旨都是扶贫和服务农民。项目落实下来,从北京飞到地方,在省里大宴会厅一顿宴席;从省里开车到市里,市里大宴会厅一顿宴席;从市里开车到县里,县里大宴会厅一顿宴席……每到一级,加入几位领导和几辆越野车,等专家队伍从省里到了村子里,估计已经有几十辆丰田越野车的规模了。经历了这一切,当我去访谈一个农民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的双眼。从五星级饭店里面走出来的专家有什么资格谈扶贫和为农民服务哪?!专家又具备什么真知识哪?!但是,我当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甚至很得意扬扬,戴着专家的光环,挣着按天计算的高额咨询费,何乐而不为? 我也见过个别另类的项目和另类的项目负责人。一个国际机构把项目办公室设在偏远的山区镇上,我去做培训的时候,直接面对工作人员和村民。为了更好地达到培训效果,我带着项目官员一起做农民访谈,我来做,请项目官员观察和学习。我们去了一个瑶族村落,找到村医做翻译,他是村子里唯一会说普通话的人,他大学毕业后回家乡为村民服务。一起工作了一天,他从来不和我直接对话,背对着我,像一个传话筒一样机械地为我做翻译。第二天,我们去访问一个老大娘,我一定要坐得比大娘低,然后慢慢地问老大娘的生命故事,我问了她很多问题,后来问她:“你能回忆一个你开心的时刻吗?”老人家就哭了,那个医生陪着老人哭,我没有打扰,只是陪伴着他们。从那一刻起,村医如同变了一个人,和我聊天,有了笑容。 在这一辈子,我有了我的大女儿,她1999年出生。多年以后的一天,女儿长大了,我和她倾心长谈,说到她的出生,我对女儿说:“我不知道说出来你会高兴还是伤心,是你救了妈妈一命。当时,妈妈觉得如同生活在老鼠洞里一样,暗无天日,不觉得生命值得留恋。我找到各种机会买了十多瓶安眠药,就等着找合适的某一天结束生命。结果你出现了。”女儿说:“妈妈,我很高兴我救了你啊。” 外交官夫人和家庭妇女:我的第三辈子 2001年,我继续在荷兰读博士,那一年的圣诞节我去了德国,在艾克乐的家里度假。艾克乐成了我二女儿的父亲。艾克乐1992年到1997年期间在欧盟驻中国使团工作,我们在执行欧盟援华项目中相识。作为外交官,一般每四年轮值一个国家。2002年,我的二女儿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出生。年底,我带着两个女儿陪同艾克乐来到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就任,从2002年到2006年,艾克乐是驻印尼欧盟使团的政治参赞,而作为外交官夫人,是不允许在丈夫的任职国正式就业的。我开始了家庭妇女的生活。雅加达处于热带,一年四季繁花似锦。早上醒来,我从落地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花园里的棕榈树、香蕉树和各色的鸡蛋花,从卧室门出去可以直接走到后花园和游泳池,清晨,园丁早已把落到池面的花瓣和落叶清理干净了。但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是我最痛苦的时刻,我拼命地想,我这一天该如何度过,没有丝毫兴趣迈进几步之遥清澈见底的游泳池,也不觉得五颜六色的花朵美丽,当我的生命本身失去社会意义的时候,这一切美景和舒适又有什么意义?! 2003年我博士毕业了。每日无聊,就把博士论文翻译成为中文正式出版了:《谁搬迁了?——自愿性移民扶贫项目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分析》。这时,一件幸运的事情降临了,有一个亚洲社会运动的研究项目,我成为中国项目的负责人。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我选择了打工群体,因为我觉得打工群体是决定中国现状和未来的重大议题,是这个研究项目的契机把我带入了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北京工友之家。当时,机构叫农友之家,借住在圆明园西路一所打工子女学校的一个小房间里,我第一次见到孙恒就是在那里,一个生着炉子的小小空间,我对孙恒的印象是:一个没有一丝表情的人。第一次看到孙恒他们演出也是在那一年,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我带着印尼的合作伙伴一起去观看。孙恒在舞台上的歌曲和演唱深深地吸引了我。台下,孙恒告诉我,他个人不认为我们做的研究有什么用处,但是,机构其他同事对此感兴趣,他把我介绍给机构的其他人。当天,我就把孙恒的手机号从我的手机通信录中删除了,从此再没有任何单独的联系。 我第一次到皮村是2005年的冬天,北京工友之家在2005年7月建立了皮村同心实验学校并入驻皮村。那天,我开着白色韩国大宇车来到皮村,约好访谈王德志。王德志挺热情的,他手里拿着喷火枪在烤暖气片。同心学校的暖气被冻住了,如果不及时把冰烧化的话暖气片就会冻裂,第二天学生就无法上课了。虽然王德志热情接待,但我自己觉得非常不自在,看着王德志手里拿着冒火的烤枪在烤暖气片,我觉得我的访谈是在耽误人家的时间。更进一步说,我不觉得我这样做出的研究有什么用处,唯一的用处是可以拿到貌似很国际化的研究舞台上去分享,但是,这样所谓国际化的东西落地到皮村又有什么用处呢?当时机构的另一位负责人对我说:“你们这些外来的研究人员就像是拿了照相机来照相,相机里面有个取景框,用固定的取景框来看我们的世界,框到照相机里的就是你的认识,但是那个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是被你框进去的那块世界。”我非常同意这位负责人的看法。 这样的交流让我从本质上质疑外来研究的目的、真实性和有用性。外来的研究者跟皮村当地的工友处于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什么能够代表生活世界?衣、食、住、行。我穿着一件一尘不染的天蓝色的羽绒服,来到皮村脏乱差的环境里;我开着一辆自动挡的大宇车,停在狭窄破旧的街道空间里。按照我的研究目的访谈完了工友之后,我开着车走了,我和他们的世界有什么关系呢?我的研究就是为了亚洲社会运动的研究报告。我和工友之间有很多的距离,自然就会有很多不了解,在这样的前提下,就谈不上信任和有效沟通。面对皮村的生活世界,我的反思是:我如此无知。基于无知的研究,其结果必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如果我非要认为我的研究报告是有用的,那就说明我不仅无知而且不道德。当我说作为一个外来知识分子是无知的,研究的成果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并不是说工友自己可以写出研究报告。但是,工友写不出来,并不等于工友自己不知道,或者没有认识,他们是在不同的知识体系里。 我非常希望做一个好母亲,我也努力去做了。从怀大女儿溪溪第一个月起,我就开始做胎教,从溪溪有第一次胎动开始,我每天都会定时记录胎动次数。溪溪出生一个月,我就开始给她念书了。等到溪溪会爬的时候,每天睡醒了,她自己爬着去把书找来让我们读。后来二女儿泉泉出生了,她的小床里永远有一摞书,到了她会说话的时候,虽然不识字,但是可以凭记忆把我经常给她读的一摞绘本从头读到尾。我发现,孩子在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学习节奏和认知结构,年纪越小的时候,越喜欢在重复中学习。溪溪三岁到四岁的时候最喜欢小熊维尼那套绘本,有时候一个晚上要我把一套十多本念上两遍,有时候念一个小时,有时候念两个小时。泉泉四岁到五岁的时候最喜欢贝贝熊系列,念得次数太多了,现在,虽然她们早已不再读那些绘本了,但是我都不舍得扔掉,这些书有着太多的记忆。到了需要同时给两个孩子念书的时候,睡觉前,每人挑不同内容的四本书,轮流给两个孩子读,一直读到孩子们入睡为止。 参与北京工友之家的工作:我的第四辈子 2007年9月,孙恒来比利时开会。从2006年到2015年,艾克乐在驻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任职。2006年9月到2007年8月这一年期间,我在比利时一家银行做高级管理人员,9月刚好离职,有时间陪孙恒到比利时各处转转,那是我和孙恒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和沟通。从2007年到2008年,我经常回国参与一个服务家政女工的项目,叫“社区姐妹行”,项目最初也得到了北京工友之家的大力支持。 2008年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10点钟,孙恒给我发了一条短信,问我:“你有没有考虑过来机构参加工作?”我很吃惊,说:“机构没有洗澡的地方啊,每天晚上不洗澡怎么睡觉啊?我也不想上皮村的厕所,太脏了。也许等十年以后吧,那个时候孩子们就长大了。”但几个月之后,我就开始参与北京工友之家在皮村的工作了。 2008年到2009年,我组织开展了打工者居住状况的调研,撰写了《打工者居住状况与未来发展》调研报告。2009年和2010年参与流动儿童发展教育项目,分别撰写了《“流动的心声”:儿童发展教育项目行动研究》报告之一和之二。这些都为调研和撰写“中国新工人”系列打下了基础,这几份报告写作之初没有想过正式出版,只是为了现实工作的需要。从2010年到现在,我参与了机构的一些工作,重点任务之一是培训,参与了工人大学的教学工作;重点任务之二是研究工作,撰写了“中国新工人”三部曲。我的一生走了这么久,经历了这么多,好像都是为了这第四辈子做准备。  北京皮村,2万多打工者的聚居地,房屋不断拆和建,人们不断来和走 2015年年初,我的工作和生活地点从北京皮村搬到了北京平谷。2009年机构在平谷租下了已经废弃的原张辛庄小学的校园作为北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工人大学)的基地。2013年又在附近租下了34亩果园建设成为同心桃园。工人大学已经开办14期了,我一直参与教学工作。第1到第13期,我们采取面授的方式,学制半年,主要在工大校园里进行教学,在那期间,我主要教授的课程是“社区调查方法”。和学员朝夕相处是一个既快乐也苦恼的过程,太多的故事,说也说不完,一个人一个样,一期一个样,不过有一点没有变过,只要把应该做的坚持下去,总会有效果,学员一定有收获。工大第14期采取网络教学的方式,我承担起了课程设置和总辅导员的任务。我想说一下我和猫的故事。平谷的冬天特别冷,我们工大的房子非常破旧,屋里烧了土暖气还是非常冷,我专门做了很厚的棉被和褥子。我的教学任务不是天天有,所以,我断断续续住在工大宿舍。有一次,当我再次回到工大宿舍的时候,天啊,我的被窝成了耗子的安乐窝。更可怕的是,每天晚上,耗子们大摇大摆地在屋子里逛,我真怕它们爬到我的脸上来。为了治理鼠患,我决定从我们皮村大院子里抓猫过来。我们皮村院子里有很多猫,和大家和平相处,但是,大多数猫不和人亲近。一个同事把两只小猫仔抓到屋里养到了几个月大,和人很亲近,同事看到我急迫需要猫咪治理鼠患,就忍痛割爱把她的一只猫咪送给了我。这只猫咪很黏人,我给它取名“粘粘”,从来没有养过猫的我手足无措,我工作就够忙了,其实不想伺候一只猫。小粘粘每天睡在我的床上,慢慢长大了。有一天,我发现粘粘躲在我的办公桌下面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我一看,它在吃一只小麻雀,连毛带骨头都吞进肚子里。看着它餐后留在地上的血迹,想着它每天亲热温柔地舔我的手指,我明白了一点儿什么是纯洁的兽性。还有一天,它飞奔地从外面冲进屋里,眼睛里面放着凶光,我一看,它嘴里叼着一只老鼠,从它嘴角露出的老鼠尾巴还在摇动,我彻底吓晕了,也意识到我的虚伪和无能,养猫是为了治理鼠患,而猫吃了老鼠我又觉得可怕。后来,为了省事,我经常喂粘粘猫粮,秋天了,没有见到粘粘再吃小麻雀。动物一旦变成宠物,就失去了本性,人自己变态也把动物弄得变态了。希望我的粘粘不要完全失去猫性,它大多数晚上都出去,早上才回来,不知道干吗去了。 机构有一个规定,不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人员每周参加一次体力劳动,所以,我一周去农园劳动一天。到了2016年6月,《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初稿完成了,时间相对充足些,我就每天上午做文字工作,下午去农园劳动。去年(2015年)我们散养了800多只母鸡,想销售土鸡蛋赚钱,但是,我们没有打开销路。不过,鸡每天都把树下的草吃得光光的,去年就几乎不用除草。今年,我们没有养鸡,需要人工除草,因为我们果园杜绝使用除草剂,还有就是,如果是小桃树,也不能放鸡进去。今年春夏,我们有四个同事一起除草:我们园长国良,我们工大第12期毕业生海庆,厨房的厨师李姐,有时候还有我。国良和海庆天天在农园里劳动;海庆晚上还要承担工人大学网络教学的任务,包括视频制作、工大教学公众号的信息发布、周会的组织等;李姐忙完厨房的事情就来农园帮忙。和这些同事一起除草,再累也是快乐的。我知道,现在农民们几乎不用人工除草了,除草剂一喷,多省事,岂不知除草剂把草杀死了,也毒害了土地和健康。生态和人生都是一种平衡,图省事是没有好结果的。5月中旬,我们给桃树疏果,我干了三个半天;6月上旬大家给桃子套袋,我干了两个半天;6月中旬我们给小桃树嫁接,我们果园已经有200多棵大桃树,2016年我们新栽了1600棵小桃树,成活了1400棵。  北京皮村,四季变换,世事变迁 为了撰写《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中工厂文化的章节,我去苏州的台资厂做过流水线的女工,时间虽然短暂,但是记忆非常深刻。后来有一次再回苏州路过打工的那家工厂时,我的心立刻收紧了,真害怕再踏入那监狱一般的车间。我知道我这样说是非常不体贴的,因为现在我国仍有8000多万工友在工厂里日夜不停地劳作着。正因为今天中国打工者的劳动非常辛苦,没有劳动保障、也没有劳动尊严,所以,新工人艺术团演唱歌曲《打工打工最光荣》和《劳动者赞歌》的时候受到一些争议:劳动者地位如此低下谈何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劳动是人之成为人的本质需要,劳动者应该是世界的主人,“劳动光荣”是从这些意义上说的,而劳动者社会和经济地位低下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有了工厂劳动的对比,我觉得我们农园的劳动虽然也辛苦,却是一种奢侈,因为在这里,没有老板和雇员,因为在这里,我们的劳动成果归劳动者所有。 吕 途 2016年10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