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蒙特利尔“深圳人”与文学大师为邻

《蒙特利尔书评》(2017年秋季号)以薛忆沩为封面人物。

《深圳人》法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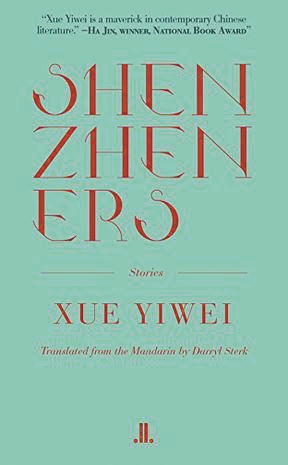
《深圳人》英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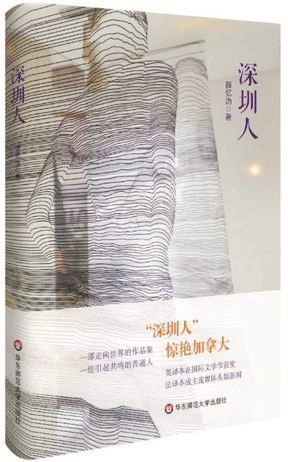
《深圳人》中文版
近两个星期来,人在蒙特利尔的薛忆沩每天都会去书店,从自己的《深圳人》面前走过。他每天都有与中国文学一起过节的感觉。
这事要从蒙特利尔当地时间11月8日说起,这一天《深圳人》法文版在加拿大法语区正式上市。加拿大法语区内所有的法语书店也因此将它摆放在入口处最显眼的柜台上,与中国读者熟悉的略萨、库切和帕慕克等大师最新译成法语的作品为邻。加拿大最大的法语报纸也给了它最高的“四星”评分。与此同时,英语《蒙特利尔书评》最新一期(2017年秋季号)也以薛忆沩为封面人物做了专题报道。在这座薛忆沩已居住了将近16年的异域城市里,英法两种语言同时为当代中国文学护驾,也算是前所未有之事了。
当代中国文学的突破
蒙特利尔是加拿大两座最具国际地位的文化重镇之一,而作为法语区的第一大城市,它在历史和气质上都比另一座重镇多伦多更接近欧洲,更具国际色彩。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英法双语城市,蒙特利尔也长期受到这两种主要西方语言之间文化差异和冲突的困扰。在这里,英法两种语言的文学界基本上是各自为政的。
而当代中国文学在这座城市不要说没有地位,甚至几乎都没有痕迹,直到薛忆沩的《深圳人》为当代中国文学打破了这种寂寞感。首先是《深圳人》的英文版在去年出版之后,便引起了当地人不小的阅读兴趣,虽然英文版本身并没有在实体书店里占据过显著位置,但依然创下了不错的销售业绩。这次法文版上市则受到了比英文版更高的礼遇,不得不说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在加拿大的一次突破。
除了英法两种语言为西方人打开了认识《深圳人》的视野以外,在当地颇有影响力的《蒙特利尔书评》也为薛忆沩和《深圳人》留下了重要的版面位置。
《蒙特利尔书评》不是像《伦敦书评》《泰晤士文学增刊》或者《洛杉矶书评》那样的国际名牌,国内的读者对其了解甚少。它是一份由魁北克的英语作家和出版家协会负责编辑,旨在推介当地英语作家和作品(现在扩充到翻译作品)的书评,每年分春夏秋三期出版,每一期有20个8开的页面(这一期因为是创刊20年的专辑,增加到24个页面),每一期的印数是4万份。它面向加拿大全国发行,在加拿大全国主要的大学书店和重要的公立图书馆都设有发行点(在大蒙特利尔区内的发行点就多达近50个),供读者免费取阅。
《蒙特利尔书评》的封面人物每一期都会选择一位在加拿大全国引起关注的当地英语作家。而这一次,他们打破了20年的惯例,让薛忆沩这位非英语作家的形象在封面上出现。
每一期用三个月(春季号甚至有六个月)的时间编辑和出版,《蒙特利尔书评》的质量在加拿大地区属于上乘。也是因为编辑和出版周期比较长的缘故,编辑部对新一期的上市是极其重视的,他们会在一个著名的书店为这一期书评举办发布会。发布会的主要节目就是邀请当期被评论到的三位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去年夏季号的发布会上,作为获得好评的《深圳人》英文版的原作者,薛忆沩第一次被邀请上台朗读。而作为此次书评的封面人物,薛忆沩的朗读也被安排为发布会的压轴戏,把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中英法三语的互文与影响
去年《深圳人》英文版甫一上市便获得了可喜的反响,现在,该书法文版又成为加拿大法语区的热点。而在今年夏天,“深圳人”系列作品也“衣锦还乡”,改以《深圳人》为名在国内重新出版。读者能看到三个语种的《深圳人》版本,那这三个版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薛忆沩称这三个版本的关系是有点复杂的。《深圳人》的英文版是译自中文原版的,但是,它不仅没有包括其中《文盲》《同居者》和《女秘书》三篇,在翻译其中那些篇目的时候,也做了一些改动,包括改变了具有明显文体特征的分段方式。薛忆沩说,他对这种改变一直持保留态度。不仅如此,英文版也打乱了中文原版篇目的编排次序。
法文版是在英文版的基础上翻译出来的。但是,它增译了《女秘书》一篇,又完全恢复了中文原版的文体特征以及篇目的编排次序。它在风格上比英文版更接近中文原版。薛忆沩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他在与法文版译者切磋翻译细节的时候,发现了中文原版《母亲》中的问题,对它做了三处细微却又关键的修改。因此,《深圳人》的中文版又可以说是受到了法文版的影响。
一部好的作品除了有地域的特色,更应该有国际视野与人的共性。所以薛忆沩一直把文学的魅力着眼于“人”的层面上。正如他所说的,“文学是人学”,这是关于文学与人的关系的金科玉律。所以“人”本身是超越地域的。《深圳人》吸引法语读者的地方就是因为它面对卑微的生命和关注了人们细腻的内心。这一点不仅让世界读者产生情感激荡的心理共鸣,也是令薛忆沩深感安慰的地方。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在西方只是被当成历史学、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辅助材料。毫无疑问,随着《深圳人》法语版的持续升温,这种状况也正在改变。
薛忆沩:好作品才是好作者的真实身份
晶报:你于2002年初移居加拿大,但是直到去年夏天《深圳人》英文版出版之前,你都只是“隐居在蒙特利尔皇家山下的中国文学秘密”。是《深圳人》的英文版让你开始显露真身。而现在,随着《深圳人》英文、法文版受到欢迎,你在加拿大文学界的地位应该更加稳固。我好奇你现在会怎样看待自己的身份:你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位中国作家,还是更像一位国际作家?
薛忆沩:在全球化和大数据的时代,“身份”问题一方面变得越来越需要回答,另一方面却又变得越来越难以回答了。很多年以前,《作家》杂志的宗仁发主编就曾经称我是中国仅有的两位“无法归类”的作家之一。后来,深圳的报纸又干脆给我贴上了那个著名的“异类”标签。还有,黄子平教授曾经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在国外生活很多年之后,评论家仍然没有将我划入“海外作家”的另册。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身份”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
在我自己看来,我从来都是正宗的中国作家,也永远都是正宗的中国作家。这不仅因为我出生于中国,成长于中国,以及坚持用母语写作……更重要的,还因为我全部的中国经验都与我精神深处的敏感和悲悯纠缠在一起,或者说我与中国的关系从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学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因为我开始受到国际的关注或者我已经没有在本土生活等等表层的因素影响。当然,我的文学身份肯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像它从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样,因为大家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可能从根本上就有冲突。还是多写些作品吧。还是少谈点主义吧。好作品才是好作者的真实身份。
晶报:你在西方国家生活,每天都面对着多元的族群,体验着不同的文化……这种生活对你的文学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薛忆沩:我在1992年第一次去欧洲旅行,那一年我28岁。那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在我的印象中,托尔斯泰也是在28岁那一年第一次游历欧洲和第一次走出国门的。在那个时候,尽管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西方生活“单纯而不单调”的性质就已经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真正定居下来之后,我对这种“单纯又不单调”的生活就有了更具体的体验。“单纯”的生活既能让人对事业专注,又能让人对生命谦卑。而专注和谦卑是保证文学质量的充分必要条件。同样,“不单调”的生活不仅能够丰富人的鉴赏力,还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对作为文学天敌的“陈词滥调”也能够起到防范的作用。我最近六年来有点不可思议的“爆发”显然与所在地的生活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晶报:以你的国际视野,你觉得目前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存在着哪些差距?
薛忆沩:鲁迅先生当年在《中国小说史略》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实际”的生活态度对艺术发展的阻碍作用。与西方文学相比,当代中国文学理想主义的色彩比较淡;与西方作家相比,当代中国作家世俗的趣味比较多、世俗的野心比较大。这也许就是一种差距吧。还有一种与“实际”的生活态度密切相关的,就是“等级观念”。我感觉中国社会里存在着太多的等级,文学界也不例外。这种人为设定的等级很容易让文学创作的环境变得既不单纯又很单调,让文学这种本应该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事业充满了功利的气息。
晶报: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有审美的优势吗?
薛忆沩:全世界的“古典”都在失去优势。在英美各级的文学教学大纲里,莎士比亚都已经差不多没有容身之地了,更不要说希腊神话和罗马史诗。这既是文明的悲剧,又是历史的趋势。这也许并不是坏事。记得对美国文化持开放态度的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曾经这样比较英美两国对“经典”的不同态度,他说,在美国作家的心目中,“最伟大的美国小说”不是某一部被某一位最伟大的作家早已经写成的作品,而是自己挽起袖子,正准备写的“这部”作品。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文学里才会不断有大师出现,而且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也能够获得很高的声誉。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学传统的国家。但是,过度地厚古薄今肯定并不是积极的文化态度。在不久前的一次活动上, 一位在蒙特利尔当地有丰富汉语教学经验的老师走近我,说她近年来用“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作品做教材,英法两裔的学生都很感兴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个细节说明当代的作品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可能发挥特殊的作用。我自己是崇拜“古典”和“经典”的,但是我同时对当代作品也怀有强烈的兴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