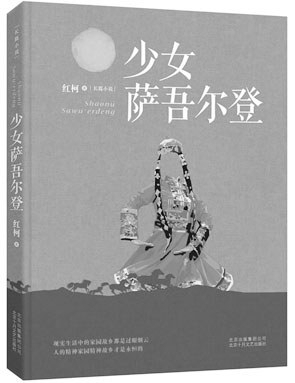《少女萨吾尔登》在接通西域与中原时,以夸父逐日的神话贯穿“东土西天”的主题。夸父逐日神话不仅是生命力量的彰显,更是西域与关中以及天地人的大融合。 《山海经》夸父逐日神话出现在红柯1998年发表的中篇《金色的阿尔泰》中,他的长篇新作《少女萨吾尔登》同样延续了“天山系列”小说中的神话思维,内含《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逐日神话包含的不同的生命阶段:夸父逐日、夸父渴饮、夸父之死、夸父重生;分别喻示着《少女萨吾尔登》主人公周志杰、周健叔侄二人的生命追求、生命能量、存在困境和生命意志。以此再现了夸父逐日神话的全部神采。 《少女萨吾尔登》的主题之一是寻找家园,以“奔跑”为意象,从两条线展开还乡叙事:叔叔周志杰在新疆度过了刻骨铭心的岁月之后举家迁回陕西,却遭遇了一系列的挫折,被同事谋算,被亲人侮辱;侄子周健大学毕业之后屡屡受挫,有家而不敢回,这是两个在夹缝中生存的人:周志杰介于西域与中原,周健介于城市与农村,他们在两个世界中都体味着“异乡人”的孤独。红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近似《奥德赛》的故事——一个关于“艰难的还乡”的故事。从两方面重构了还乡:一方面是周志杰和周健回乡过程中的重重阻碍;一方面是现代人重回精神家园的艰难。 《少女萨吾尔登》以人性与人情界说西域与中原。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交流、感知、意会,是人性范畴;而人与人的交往、算计则是人情范畴。红柯在探讨两种迥异的生命存在状态时,将新疆卫拉特土尔扈特蒙古族与周原人的历史片段引入文本,以此对两种文化进行了溯源。于是土尔扈特人东归与周原人伐纣的历史成为小说中又一暗线,在红柯的叙事中,二者均以英雄史诗的面目呈现,并传递作者对生命的思考:周人吃了血水一样的臊子面,成为亲兄弟的将士们长途奔袭夺了殷纣王的江山;土尔扈特人唱着《我的母亲》,跳着萨吾尔登从伏尔加河回到天山母亲的怀抱。同时贯穿的另一史诗,大月氏人受匈奴压迫背井离乡到达伊犁河谷,冲出匈奴和乌孙夹击抢占天山达坂。红柯在对不同文明的历史巡礼中发现了共同的生命形象:奔跑。奔跑成为生命强力的象征,是夸父逐日神话的核心。 他们生命的最初都执着于“奔跑”,但这两个世界最终分流:土尔扈特人的气血凝聚为萨吾尔登,天地、人神、草木融为一体,成为永驻的生命力;周人却沦陷为异化的人,逐渐开始运筹帷幄机关算尽,不再是凌厉强悍的苍鹰,而是圆融巧媚的猫,是柔软的蛇。 《少女萨吾尔登》中贯穿着蒙太奇手法,周氏叔侄在人情世界中艰难跋涉的身影与远古英雄们的奔跑剪接组合到一起,最终凝聚为奔跑的生命洪流。《少女萨吾尔登》有着鲁迅《过客》的神韵。过客不停息地向着日落的方向行走。周的后人们不能成为隐身于土地的蛇,不能成为只寻求温暖而不顾秽气的猫,这样的男人们,成为红柯笔下的夸父。 红柯的生命诗学建立在天地、自然与人合一的体系中,秉承着神话中的“化生”意志,呈现出人与物互生的生命图式。《山海经》中夸父追逐太阳而最终以身体化为万物而灵魂不死。《少女萨吾尔登》从头到尾都围绕着周健的身体进行书写,从危难中的腿,到想尽办法保护腿,到失去了腿,到新的生命获得了完整的腿。这一结构正对应着夸父逐日神话结构:夸父逐日、夸父渴饮、夸父之死、夸父重生。《大荒北经》记载:“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是后土的后代。“后土由‘地母’神演化而来”。夸父源自大地最终归于大地。化用过夸父逐日神话的《金色的阿尔泰》,成吉思汗就正是从黄土中重生,《少女萨吾尔登》中周健的回乡“就是看望母亲”,“寻找母亲”。“故乡就是娘”,这一将母亲与故土合一的叙事方式并未越过我们熟悉的审美规范。但红柯的大地绝不拘于“母亲—故土”模式。相较于早期的任情狂飙和诗性快意,红柯越来越倾向于“融合”与“皈依”。 《喀拉布风暴》将西域与关中接通,《少女萨吾尔登》在接通西域与中原时,以夸父逐日的神话贯穿“东土西天”的主题。夸父逐日神话不仅是生命力量的彰显,更是西域与关中以及天地人的大融合。小说中,周志杰的学术研究将张载《西铭》设计的“民胞物与”的“大同”世界与卫拉特土尔扈特人的萨吾尔登结合在一起。对于红柯来说,西域与关中是他人生铁轨的两根枕木,并行的,难以割舍,一边是对天空的向往,一边是对大地的乡愁,西天与东土合一才是生命的真正完整。 在《少女萨吾尔登》中,周志杰的远行新疆接通了新疆与周原,周健也是从故乡出发,经过跋涉,伤痛,超越,最终经由萨吾尔登的指引寻到精神家园。因此,红柯的创作是灵魂之旅,朝圣之旅,更是寻根之旅,其中贯穿着对于生命“源头”和人类童年的追问,红柯从萨吾尔登追溯至土尔扈特人的奔跑和守护家园,从臊子面追溯至周原人的祖先血性激昂和亲如兄弟。历史由“起源”而获得了类似族群记忆的性质,也由此获得神话性。所以,在对周原人现实面貌的慨叹批判中,《少女萨吾尔登》整个文本浮动着对于元初神话世界的乡愁。红柯试图以现代小说还原远古神话的精神旨归。他的笔力大开大合,以此唤醒古老大地的童年记忆,将人性从年深月久的文化的斧钺之下拯救出来,红柯赋予萨吾尔登一种生命原乡的召唤性质。 红柯赋予萨吾尔登几近巫性的能量,萨吾尔登跳起来的时候,以回环咏叹的抒情指向生命与万物合一,人与神话交融而获得了生命之初澄明的童年的眼睛,将人从“人情”、“关系”的沉沦中拯救出来,萨吾尔登便成为异乡人灵魂的“招魂仪式”。当它开启时,外在的现实世界像快速向后退去的电影镜头,里面豁然现出的新疆正是一个遥远的神话世界,而这个充当人与天地与神话世界相接的启示者的,就是兼具着母性和情人性质的女人。很明显,红柯在创造一系列现实与神界的通灵者和启示人。《大河》写人与熊,《生命树》写人与树,《乌尔禾》写人与羊,《喀拉布风暴》写人与骆驼,红柯更想表达的是启示和指引,甚至神谕。《少女萨吾尔登》延续这一模式,写人与天鹅。跳萨吾尔登的女性就是白天鹅,就像是但丁《神曲》中的贝缇丽采。小说的最后,甚至有了周穆王漫游昆仑与西王母相会的意味。红柯其实是将夸父逐日神话与周穆王西游会西王母结合在一起了。红柯认为《穆天子传》是周人的怀乡之书,《少女萨吾尔登》也正是以一个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现代故事寄托对“西天”和“远古”的乡愁。周人的后代与渥巴锡汗的后人相爱的故事隐含着红柯将西域与关中这一西天东土的生命链条衔接到一起的宏愿。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07月01日1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