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外行走——侦探小说的必然选择
|
|
|
|
|
|
 经常被人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喜欢读侦探小说?”实际上,我很难一下子给出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回答,尽管自己确实读过不少侦探小说。同样,当我把这个问题提给我的朋友时,得到的答案也很难令我满意。听到过最多
的一个回答是:“侦探维护了法律,侦探小说维护了法律。”很遗憾,我必须以苏格拉底的方式评价这个答案——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我知道你的答案一定是错误的。从侦探小说诞生的那天起,这种文体,这种文体中的主人公,就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地代表过法律;恰恰相反,侦探往往都是在质疑法律、对抗法律,甚至是颠覆法律。我很乐意从侦探文学发展历程的角度阐释一下这种文体之所以始终“法外行走”,却备受读者青睐的原因。 经常被人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喜欢读侦探小说?”实际上,我很难一下子给出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回答,尽管自己确实读过不少侦探小说。同样,当我把这个问题提给我的朋友时,得到的答案也很难令我满意。听到过最多
的一个回答是:“侦探维护了法律,侦探小说维护了法律。”很遗憾,我必须以苏格拉底的方式评价这个答案——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我知道你的答案一定是错误的。从侦探小说诞生的那天起,这种文体,这种文体中的主人公,就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地代表过法律;恰恰相反,侦探往往都是在质疑法律、对抗法律,甚至是颠覆法律。我很乐意从侦探文学发展历程的角度阐释一下这种文体之所以始终“法外行走”,却备受读者青睐的原因。
“侦探”一词在英语世界最早出现于1194年(至少目前是这样),当时写作“sleuth”。这一词汇最初的含义是足迹、踪迹,既可以指人类,也可以指各种动物。到了15世纪,这个词有了“狗追踪目标”的含义,例如现在的“猎犬(sleuth-hound)”一词便是由此引申而来。在19世纪,这个词的名词形式正式有了“侦探”的意思,动词形式则表示“搜查、调查”。而在今天,“sleuth”则指代侦探小说中所有的调查行为和解决事件的主人公(也就是侦探)。我们现在更多使用的“detective”一词要年轻得多,是在19世纪中叶才出现在英国大文豪(也是侦探小说先驱人物)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中。
与很多文明的历史一样,关于侦探小说的历史起源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在有组织的警察和私家侦探出现之前是没有侦探故事的;另一种则认为早在《圣经》或古希腊神话中便纠结着各式各样的调查与反调查,而这些就是早期的侦探小说。如果支持第一种说法,那么侦探小说应该始于1841年。这一年,美国作家、诗人、评论家埃德加·爱伦·坡创作了第一篇侦探小说《莫格街凶杀案》。毫无疑问,尽管这篇小说以今天的观点看来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不可否认它已经具备了当今侦探小说的三个最基本的元素——侦探、谜和逻辑。小说的人物塑造和气氛渲染也相当成功(当然,这是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得出的结论)。这样,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赞同第一种说法,那么侦探小说似乎变成了不符合进化论的“怪胎”。但是,任何一种新生的文学题材都没有如齐天大圣般“横空出世”的道理。因此,即使爱伦·坡在1841年发表《莫格街凶杀案》真的可以看作侦探小说诞生的标志,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在这之前的林林总总。何况,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的根源肯定要远远早于1841年。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举足轻重的一部书,《圣经》在第一部分《创世记》一开始便为我们讲述了两桩罪案——金苹果疑案和该隐杀弟案。第一桩罪案中,夏娃触犯了人类最早的法律——“不可以偷吃智慧之果”——这条法律是由上帝制定的。且不论这条法律是否合理,单单只看上帝的审判,我们便会觉得实在有失公允。完全无辜的亚当被赶出伊甸园,终身劳作以求温饱;更不可理解的是,当时还未出世的亚当和夏娃的孩子——我们今天的人类受到牵连,世世代代与天地苦斗;而且,不管后世的人类多么优秀,多么恭敬上帝,也无法得到生命之果,无法拥有和神一样的永恒生命。在第二桩罪案中,上帝的裁决更加莫名其妙。残忍的该隐和亚当得到了一样的惩罚——这表明偷窃和杀人受到的惩罚在“法律”面前竟然完全一致!试问,这种由无所不能的上帝制定的“法律”有什么意义呢?可以说,它除了可以随意制裁上帝讨厌的人之外,不能给人类带来任何保障和幸福。
离开犹太民族的经典,我们会发现欧洲文明的起源“希腊神话”当中这样的“不平事”随处可见。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中,两场家族阴谋使得众神的统治稳定下来——先是克洛诺斯颠覆了老爸乌拉诺斯的统治,而后宙斯变本加厉地让父亲品尝到了祖父不久之前的失落。此后,神界、人界以及冥界便都在宙斯——这个暴戾、专横、淫虐的主神——制定的“法律”之下悲惨地生活着。所以,我们会无限尊敬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会为赫拉克勒斯的12大丰功伟绩喝彩,会很高兴地看到第一智者奥德修斯将众神戏耍得团团转。可见,在人类最早的文学作品中,所谓的“法律”就是作者和读者“唾弃”的对象,人们在不断证明着法律的偏失和缺陷,在不断歌颂“法律的践踏者”。
当然,文学不可能总是停留在传说和神话阶段,文学中人物的“反抗”也不应该停留在“武装反抗”上,那样就不必侦探小说大显身手了。历史进入了启蒙时期。思想家伏尔泰在他的小说《查第格》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王后的狗和国王的马不见了,查第格说自己并没有看见它们。但他却说母狗长了一对长耳朵,左前腿瘸了,而且最近怀了小狗;马则有五尺高,马蹄很小,尾巴有三尺半长。他还说马的蹄套是用银子做的,而那用金子做的马嚼上还有装饰物。当他坚持说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狗和马时,国王和王后因为无法相信他的话而鞭打了他。在动物被找到之后,查第格的解释被证实是真实的。母狗下垂的耳朵和乳房在沙子上留下了记号,而且一只蹄子留下的脚印比另一只深;马吃光了五尺高的拱廊上的叶子,它的尾巴扫过的灰尘有三尺半长,石头上留下的记号则说明了马嚼和蹄套的情况。这个精彩的片段伏尔泰借用了梅利骑士30年前发表的传奇故事。他的最初目的并不是想说明推理的力量,只是在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讽刺。一方面,国王和王后的“法律”依然“蛮不讲理”;另一方面,逻辑推理的效用第一次体现了出来——尽管还是反抗法律,但显然已经比希腊神话时代更加保险,也更加有效。在《一千零一夜》的很多故事里都有诡计和谜团的因素,通常被作为利用机智摆脱困境的例子,像在乔叟的《修女和牧师的故事》里一只公鸡被狐狸抓住,它说服狐狸张开嘴巴然后逃走。而类似的故事我们在另一本脍炙人口的小册子《伊索寓言》中更是屡见不鲜。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和英国人的骄傲莎士比亚的一些作品中对犯罪与斗智桥段的描绘则更加生动深刻。
在这个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里,恶魔披上了“宗教”与“法律”的外衣,肆无忌惮地蚕食着人类的心灵;而文学作为当时最为“先进”一种生产力,毫无疑问正试图拼命摆脱这种阻碍与束缚。因此,就像当时所有落后的、愚昧的、反人类的东西都无情地遭到文学作品的批判一样,虚伪的、只为少数人服务的“法律”也是批判的靶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出现的侦探小说的“法外行走”,实际上起源于西方社会这一惯有的传统,是西方主流文学作品共性的一种集中体现。
接下来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我们千万不要被什么“自由、民主、博爱”的口号蒙蔽。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初期,这个制度可以说是漏洞百出的。君主、贵族、主教等特殊阶级依然拥有特权,所谓的新制度下建立的新型刑侦机构完全是维护特权阶级、保护其私有财产的“走狗部门”。因此,由特权阶级制定、由“走狗部门”执行的所谓新型法律是何等货色就可想而知了。
这里我仅举一例。著名侦探小说作家、“福尔摩斯之父”柯南·道尔曾受人之托调查过一桩冤案。一位牧师因为是有色人种,故一贯受到歧视和非议。一天雨夜,牧师村子的一匹马被杀,警察马上逮捕了牧师。他们粗暴地把一块从马的尸体上割下来的肉和从牧师家找到的雨衣放在了一个袋子里,因此得出了牧师的衣物上有血迹的结论;他们把牧师的皮鞋强行按在现场泥地里留下的鞋印上,得出了足迹完全一致的结论……就这样,牧师被判定有罪!而且,在判决引起社会民众强烈不满、纷纷要求重审此案时,政府竟然委任当时力指牧师有罪的一个人作为“中立人物”负责重审此案!要知道,这是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相当成熟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奇事”。因此,在这一制度建立之初,法律是何等模样也就不言而喻了。值得一提的是,柯南·道尔在此案中是以“福尔摩斯”化身的形象出现的。这也说明,侦探小说中神探的“法外行走”在福尔摩斯时代已经不可避免。
制度的阴暗,官方的无能,造成了民众的极端不信任和唾弃,或者说至少也是“敬而远之”。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所有文学作品都极尽所能对警察、法官、检察官进行讽刺挖苦,也不止一次对法律表示出无奈与愤慨。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环境里,侦探小说诞生了。
作为大众读物,作为一种急需获得读者支持的新兴文体,侦探小说的初衷和立场从一开始便一目了然,且别无选择。小说需要引起读者的共鸣,需要在虚幻的世界中为阅读者寻找慰藉和希望。毫无疑问,“法外行走”是最好的原则。因此,我们总是在侦探小说中看到一个正直且智慧的神探,一个正直但愚蠢的伙伴,一个(或一群)无耻且愚蠢的警察;我们总是看到神探一次次“践踏”法律,按照自己的原则处置罪犯,按照民众的呼声解决问题。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侦探小说中的侦探往往会触犯法律,但既然是文学创作,“违法”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违法”是读者需要的,是民众需要的。
这里我可以再举一例来说明侦探小说“法外行走”的特质。法国人尤金·弗朗索瓦·维多克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并不是一位作家,也不是某部作品中虚构的人物,而是一位真实存在的、对侦探小说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传奇人物。他在十几岁时偷了母亲的两千法郎,后来参了军,在6个月时间里进行了15场决斗,再后来被判入狱8年——那时维多克22岁。在这段时间里,他决心重新做人,并对祖国表现出了无比的忠诚。他被安排“越狱”,然后被任命为安全局的长官——恐怕只有分不清危险和浪漫的法国人才会成全维多克这样的人。在这个职位上几经周折、取得辉煌的成就后,维多克选择了急流勇退,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位私家侦探,继续与形形色色的罪犯打交道,乐此不疲。维多克对侦探领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首创了许多调查方法,如形体观察、足迹鉴定、乔装易容、逻辑推理等。他还是第一个建立犯罪索引档案的人,为后来的追随者省去了无尽的麻烦。维多克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经常光顾那些臭名昭著的房屋和街道,有时这样乔装,有时那样乔装。的确,迅速改变的衣着和方式都说明了一个人渴望隐藏起来,不被警察发现,直到我每天都遇到的流浪汉和小偷坚信我和他们是一伙的。”的确,维多克的重要性在于他本质上是一个罪犯和英雄的混合体。对罪犯的界定和对一个人究竟是英雄还是恶棍的怀疑,是侦探小说的基本特征之一。他的这种属性影响到后世侦探小说的创作和侦探人物的塑造。歇洛克·福尔摩斯在某种程度上便是维多克化身——一个经常为维护正义而犯罪的英雄。大文豪巴尔扎克是维多克最好的朋友。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经常把维多克映射到某人物的身上——《高老头》中的沃特林(又名杰克斯·柯林)便是其中之一。
“维护正义而犯罪的英雄”——正义、犯罪、英雄,应有尽有,但与“法律”无关。最初侦探小说就是一种从此类人物身上获得灵感、讴歌此类人物的文体。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法外行走”是侦探小说与生俱来的特点之一吗?
我们再来看一下侦探小说产生的一些“具体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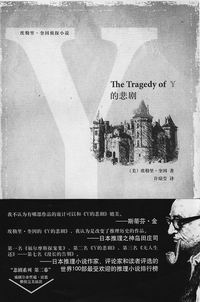 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有着自己的特色,侦探小说也不例外。只不过,侦探小说在登场的初始,便有着更多的与众不同。前面已经提到了,埃德加·爱伦·坡是侦探小说的创始者。他是一位天才,而且是一位极端病态的天才。父亲出走,母亲早逝,与养父不和,爱妻患病,事业坎坷,朋友背叛……诸多不幸加于埃德加一身,他的心境是常人不可想象和承受的。可以说,爱伦·坡创作侦探小说不是出自什么文学追求,更不是出自任何经济考虑,更是一种自我的证明与救赎。他要证明自己的精神没有错乱,他要证明自己具有超人的智慧、有着巨大的存在价值。因此,我们看到,爱伦·坡的5篇侦探小说中充满了喋喋不休的理论分析和卖弄,充满了对任何人的不屑一顾,这点在他创作的侦探奥古斯都·杜宾身上尤为明显。所以,侦探小说在被创造伊始便注定,它首先是一种卖弄,是一场智力游戏,是侦探向读者的挑战。作为解谜游戏,侦探小说中的侦探自然视任何规则为无物。这一侦探小说独一无二的特点一直延续至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等大家的作品无不如此。 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有着自己的特色,侦探小说也不例外。只不过,侦探小说在登场的初始,便有着更多的与众不同。前面已经提到了,埃德加·爱伦·坡是侦探小说的创始者。他是一位天才,而且是一位极端病态的天才。父亲出走,母亲早逝,与养父不和,爱妻患病,事业坎坷,朋友背叛……诸多不幸加于埃德加一身,他的心境是常人不可想象和承受的。可以说,爱伦·坡创作侦探小说不是出自什么文学追求,更不是出自任何经济考虑,更是一种自我的证明与救赎。他要证明自己的精神没有错乱,他要证明自己具有超人的智慧、有着巨大的存在价值。因此,我们看到,爱伦·坡的5篇侦探小说中充满了喋喋不休的理论分析和卖弄,充满了对任何人的不屑一顾,这点在他创作的侦探奥古斯都·杜宾身上尤为明显。所以,侦探小说在被创造伊始便注定,它首先是一种卖弄,是一场智力游戏,是侦探向读者的挑战。作为解谜游戏,侦探小说中的侦探自然视任何规则为无物。这一侦探小说独一无二的特点一直延续至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等大家的作品无不如此。
进入20世纪中叶,金融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侦探小说。作家们发现世界已经满目疮痍,面对社会的剧变,原来的英雄已无用武之地,要么同流合污,要么“站着死去”。无论选择什么,我们都会发现,侦探必然要继续“法外行走”。
侦探文学的“法外行走”是西方文明史发展的结果,是西方文学共同的特性,是侦探文学必然的特点,是侦探文学史自然的选择。这当然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文学和社会框架完全一致,我们还需要文学吗?如果人人都是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还会有今天的不朽吗?
|
原载:《博览群书》2009-9-17
(责任编辑:admin)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