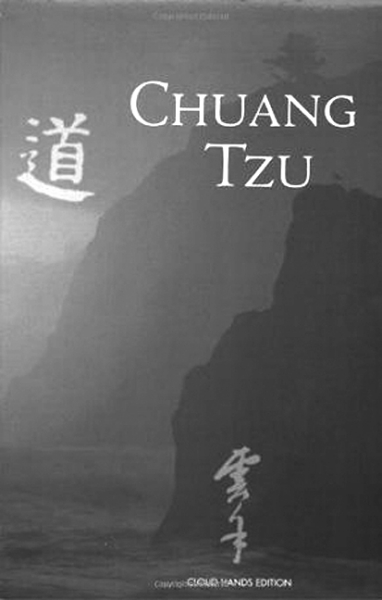■本报记者 康慨 瑞典学院10月6日赞扬80岁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oemer)“以其凝练而透彻的意象,带给我们对现实的全新感知”,为此授予他20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个准确的评价,也是一个公允的选择,特朗斯特罗默遍布全球的读者皆可为此欣喜而释然。然而,大多数中国读者注定难以分享这份喜悦,因为糟糕的汉译,我们无力参透他“凝练而透彻”的精妙,更无从获得“对现实的全新感知”。表面上看,两部已经出版的汉译特朗斯特罗默全集可算对读者有了一个交待,可惜对他的诗,我们依旧并且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这种雾里看花的状态。 释然的快乐和怨毒的指责 特朗斯特罗默是继1996年获奖的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之后,十五年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诗人,也是继1974年的艾温德·约翰松和哈里·马丁松之后,三十七年来获奖的第一位瑞典人,以及十七年来的第十四位欧洲得主——仅去年获奖的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03年的南非作家JM·库切和2006年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例外。 特朗斯特罗默的英译者之一、苏格兰诗人罗宾·罗伯森告诉《卫报》,特先生的获奖是“一次漫长等待的幸福结局:解脱的快乐。特朗斯特罗默不仅是斯堪的纳维亚最重要的诗人,也是世界级的作家——这一点终于得到了公开承认”。在为《纽约客》网志撰文时,罗伯森写道:“世界诗坛终于能够举怀同庆,敬祝这个谦卑的人,这个卓越的诗人。”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在斯德哥尔摩宣布特朗斯特罗默获奖后,首先否认了学院将大奖赠予同胞有任何不妥之处,因为瑞典人已经“四十年”[原话如此]没碰过这个奖了。去年解密的诺贝尔委员会投票记录显示,1959年,学院曾以北欧作家获奖过多为由,不遵从下设诺贝尔委员会的投票结果,剥夺了丹麦女作家卡伦·布里克森几乎到手的桂冠,转授意大利诗人萨尔瓦托雷·夸西莫多。 谢尔·埃斯普马克院士罕有地获得准许,对此事公开评论说,学院对北欧中心主义一向怀有罪恶感。这也是许多特朗斯特罗默支持者过去深以为憾的原因所在。几个月前,78岁的荷兰大作家、特朗斯特罗默的荷兰语译者J·贝恩勒夫告诉我,诺贝尔奖早该授予特先生,但是瑞典人有心理问题,羞于把奖颁给自己的同胞。 今年,院士们不再害羞。但即便为特朗斯特罗默戴上桂冠不算北欧中心主义,也仍有欧洲中心主义遭人诟病。美国文坛对此怨愤最切。十八年的漫长等待已经让该国主流媒体大大失去了正面报道诺贝尔奖的兴趣。菲利普·罗斯、托马斯·品钦,乃至歌手鲍勃·迪兰的名字尽管一再出现在赌博公司赔率榜的前列,却年年成为赔衬欧洲大红花的绿叶。 正像某些华文媒体将“特朗斯特罗默”称为“川斯楚马”一样,也难保有英文读者以为今年的获奖者是“变形金刚”(Transformer)。《华盛顿邮报》在报道开篇如此描写美国读者的反应:“谁?啊?” 英语世界今年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批评,已经由过去的怀疑、失望和冷嘲热讽,转向了肆无忌惮的大批判,炮打司令部,矛头直接对准了该奖的总后台瑞典学院。《彭博商业周刊》刊发赫夫齐芭·安德森的文章,指责诺贝尔文学奖“对那些晦涩、政治正确或绝无可读性的作家有一种变态的偏爱(上述三种特点,艾尔弗丽德·耶利内克全都具备)。” 英国小说家、卡尔维诺的译者蒂姆·帕克斯亦刊文于《纽约书评》网志,说十八个或十六个瑞典人——大多数是老头子——搞搞瑞典文学自然没得说,但没有哪个团队能对不同传统的无数文学作品做出终身宣判。 另一位英国小说家菲利普·亨舍尔则在《每日电讯报》上说,时间将证明,每一位瑞典的诺贝尔奖得主只要迈出自己的国门,都会成为“无人关注的小现象”。这是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1980年获奖后,某位心怀不满的评委对他所下的论断。 秃鹰看着自己:黑匣中的琴 特朗斯特罗默远没有攻击者所的那么糟。但既使有心反击,他也已无力发言。由于1990年中风导致的半身不遂,特朗斯特罗默的语言表达受到了严重制约。他含混的语言,往往需要太太莫妮卡翻译或代为表述。10月6日午后,年年在他家门外守候的记者终于一拥而入。在被问到获奖感受时,老诗人勉力说出了两个字:“很好。” 尽管身有大不便,但他从未停止写作,先后于1996年和2004年出版了新诗集《悲舟》和《大谜语》。《悲舟》成了瑞典当年的畅销书,销出三万册。这可不是斯蒂格·拉松的《龙文身的女孩》。在人口小国瑞典,一部诗集能卖到这个数字,真可谓稀见的盛事。在其中的第一首诗《四月与沉寂》中,他写道: 我被装入我的影子, 像一把琴 在黑匣中。 黑匣中的琴可视作特朗斯特罗默困于病体的自我描述。他的作品质朴,少有“祖国”、“人民”这样的大词;用语极简,却有极大的空间。“他写大问题。”恩隆德常秘说,“他写死亡,他写历史和记忆,还有自然。读完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诗,你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它们只是]小诗。” 特朗斯特罗默笔下的瑞典充满了宁静的喜悦。如1958年所出诗集《途中的秘密》里面的一首《天气图》,非常瑞典,也非常北方: 一块琥珀的幽光,临于村庄之上, 所有的声音,在缓慢飞翔。 另一位与他同龄的瑞典诗人拉斯·瑟德贝里说过,特朗斯特罗默是“秃鹰诗人”,以此形容他的高度与深刻。正所谓飞得高,看得狠,在他鹰一般的目光之下,世界纤毫毕现。 特朗斯特罗默本人则说,他的诗是“交汇处”:暗与光、内界与外界在此碰撞,并与世界、历史和我们自身生出突然的联系。“语言总是与刽子手们步调一致。因此我们必须获得一种新语言。”他说。 《晨鸟》一诗见于1966年出版的诗集《音与轨》,描写了诗歌的诞生: 奇妙地感到我的诗在生长, 而我在萎缩 它生长着,它取代我。 它推开我。 它把我扔出巢外。 诗已成。 翻译的败坏 特朗斯特罗默是同代人中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作品已有包括汉语在内的六十余种语言译本。但是我们目前拥有的两种汉译全集,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诗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已不再是诗,至少不再是好诗了。 在诗歌翻译中,失什么,留什么,并非所有译者都明白。“通常而言,可信赖的译者会取其意而弃其音,”美国大诗人罗伯特·洛厄尔曾经引述帕斯捷尔纳克指出,但是,“在诗歌中,音必然就是一切。” 读目前的两种汉译,音几乎尽失,而意也常有错会。具体的批判文章可参见诗人北岛的随笔集《时间的玫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他的指摘要远为刻薄。 “我为中国的诗歌翻译界感到担忧,”北岛哀叹,“如今,眼看着一本本错误百出、诘屈聱牙的译诗集立在书架上,就无人为此汗颜吗?” 北岛只通英语,他另译的几首特朗斯特罗默,皆由英语转译(但从不提英译者的姓名),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译诗是“瞎子领瞎子”。事实上,二十多年来很多我们熟悉的中青年译者,都被他拿来做了反面教材。 他对诗人和翻译家王家新的批评几近于贬损,在论及策兰作品的汉译时,北岛写道,王家新等人“把诗歌降到连散文都不如的地步”。这种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姿态,远远不能服人,也暴露出北岛仍然缺乏伟大诗人应该具备的胸怀、涵养与自知之明。他还要走多远的路,才能像特朗斯特罗默那样登临殿堂呢? 对冯至所译里尔克的《秋日》,北岛只改动廖廖数字,便作为自己的新译。连他自己也承认,他的版本是“在冯译本的基础上‘攒’成的”。 冯译是这样的:“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北岛的新译如下:“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如今的汉语译诗,绝大多数已不再有价值。它们失去了血和骨肉,只留给读者少许无味的皮毛。写诗的人不译诗,译诗的人不懂诗,而只有不懂诗的人在读这些劣译的诗。这不仅是译者的问题,也是诗人的问题,甚至是当代汉语的一个大问题。劣译不仅败坏原作,也持续败坏着我们心爱的母语。 特朗斯特罗默全集的英译者、苏格兰诗人罗宾·富尔顿认为,特先生绝非晦涩的诗人。“有些诗人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时过于繁密,这些人压根就不能翻译。特朗斯特罗默不在此列。”他对《卫报》说,“从许多方面来讲,他所使用的语言相对平淡和简单,但他写出了非同寻常的意象,有时非常令人吃惊,让读者感到震撼。这才是诗人该做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斯特罗默容易翻译。特先生的编辑尼尔·阿斯特利指出,他的诗具有高度的乐感和多层含义,每个词,或每个片语,都能激起瑞典读者特殊的共鸣——他独特的遣词造句,有时可将许多关联的意义汇聚一处。 罗宾·罗伯森则为《纽约客》网志撰文说,对翻译家而言,特朗斯特罗默相当复杂。“他精雕细琢的压缩,生动的电影化的意象一下子就能抓住人,但其语言本质上的质朴常被认作呆板和乏味。原作灵活的节奏难以复制,同样,像‘domkyrkoklocklang’[咚-雪了抠-嗑蝼嗑烂]这种瑞典语单词所具有的爆破音的音感,在译成‘教堂钟鸣’后,也失去了所有听觉上的共振。他笔下空灵的景观对北方诗人而言再熟悉不过了,但把对这种景观所做的形而上学的解析写成极简的瑞典语,那往往就太难了。”罗伯森的翻译之道是,走中间道路,既不冒重写之险,也未字字直译。他保持原作的句态,更为清晰地呈现其含义,同时力求其音。 《联合报》报道,瑞典学院院士、汉学家马悦然翻译并作序的两部“川斯楚默”诗集——《悲伤的凤尾船》[《悲舟》]和《巨大的谜语》[《大谜语》]将于下个月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 诗人·心理学家·左手钢琴师 特朗斯特罗默有三种身份:心理学家、钢琴师和诗人。心理学是他谋生的专业,弹钢琴虽属业余,却是终生的爱好,即使中风后,他仍然可以左手弹奏,而写诗将使他不朽。 1931年4月15日,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生于斯德哥尔摩,1950年毕业于索德拉拉丁文法学校,而后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研读文学史和诗学、宗教史,以及心理学,随即供职于该校的心理测验学院,1958年与莫妮卡·布拉德结婚。1960年到1966年期间,他在林雪平附近的罗克图纳少年犯心理矫正中心工作。自1980年起,特朗斯特罗默效力于韦斯特罗斯的劳动力市场学院。 他的首部诗集《十七首诗》出版于1957年,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文学新作之一。第一首诗名为《序曲》,开篇写道: 醒来宛如伞降,跳离了梦境。 旅人解脱于令人窒息的骚动, 向清晨的绿区下落。 随后出版的《途中的秘密》(1958)和《半完成的天庭》(1962)确立了他的声望。1972年的《波罗的海》则是一部回忆性质的长篇组诗。1993年,他出版了自传性随笔集《记忆看着我》,其书名取自十年前的诗集《野市广场》里的一首同名诗作。 特朗斯特罗默的早期诗作倾心于自然和音乐,意象澄澈,后期则细小和凝练,也更富个人色彩,反映出他丰富的爱好,如音乐、旅行、绘画、考古,以至自然科学,晚近的作品近于俳句,且转趋灰暗,往往直抵病痛、死亡和生存的意义。他的诗大多不长,产量极低,忙活了一辈子,不过一百六十余首,因此将其全部作品结为一册时,通常只有两三百页。 李笠译《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和董继平译《特兰斯特罗默诗选》分别在2001年和2003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特朗斯特罗默曾于1985年和2001年两次访问中国。出版于1989年的《为生者与死者》中,有一首《上海的街》。最后一句写道:“太阳当空照,我们喜洋洋,而我们一无所知的伤口正在流着血,直到死亡。”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将于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按照惯例,获奖者将发表长篇答谢演说,目前还不知道特朗斯特罗默将以何种形式发言,最大的可能是由太太莫妮卡代读,但他的老友、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亦有希望再做他的传声筒。就像他以往外出参加朗诵会时那样:别人读他的诗,他在一旁弹琴。曲子是作曲家专门为他写的左手钢琴曲,这是欧洲诵诗会上不可错过的一个胜景。但愿他不会用一首俳句向学院交差。如果他拿出一篇标准长度的讲稿,那或许就是他此生写过的最长的文章。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他能亮相于盛会,对着诺贝尔奖的证书、奖章和一千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94万元]的奖金,再嘟哝一句: “很好。” 注:文中所引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之诗句,均转译自罗宾·富尔顿(Robin Fulton)的英译特朗斯特罗默全集《大谜语:新编诗集》(The Great Enigma: New Collected Poems,新方向出版社,2006)。此书所选纳的篇目,与董继平译《特兰斯特罗默诗选》大部分相同。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10月12日0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