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尔维拉·纳瓦罗 埃尔维拉·纳瓦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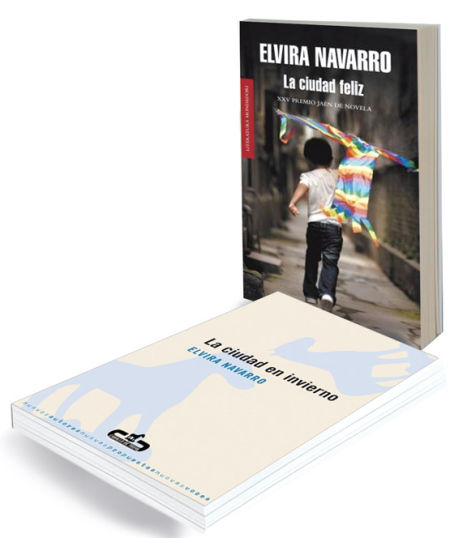 《冬季之城》 《幸福之城》 西班牙文版 《冬季之城》 《幸福之城》 西班牙文版埃尔维拉·纳瓦罗(Elvira Navarro) ,生于1978年。2007年出版首本著作《冬季之城》,获得好评。出版于2009年的《幸福之城》获得第25届哈恩小说奖、第4届风暴奖最佳新作家奖,并选入《大众日报》文艺副刊年度图书榜。她为报纸撰写稿件,写作文学评论,撰写博客“茶杯里的风暴”。《格兰塔》杂志将她评为22位35岁以下西班牙最佳作家之一。本文由纳瓦罗在6月24日北京举行的第二次中国-西班牙文学论坛上的演讲翻译整理而成。 自我写作,就多次被问及一个问题:是否存在女性文学。我总是回答,我是个女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作为作家看问题的角度,也正是一个女人看问题的角度,这并不表明我相信纯粹女性或纯粹男性的题材,我也不认为只存在一种女性创作手法和一种男性创作手法。但很多时候,确实存在着女性文学和男性文学。事实上,文学史中就有一些例子,在文学评论界存在着观念因素。譬如,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评论简·奥斯汀:“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如此高度评价奥斯汀女士的小说,在我看来,这些小说有一种平庸的矫揉做作、缺乏艺术想象力、受英国社会常规的束缚,没有特点,也没有才华和对世界的了解。人生从来没有如此渺小和狭窄。这位女作家脑海中的惟一问题……就是婚姻。自杀行为还更值得尊重。” 我的首部小说《冬季之城》出版于2007年,讲述了主人公在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虽然评论家的评论并非像爱默生谈论简·奥斯汀那样,但不得不承认,有些男性读者向我表示,该作品可归类为“女性文学”。当我问他们为什么认为该作品可归类为女性文学以及他们对女性文学的理解又是什么时,他们提出的依据仅仅是小说故事的主人公、一位名叫克拉拉的女孩是一位女性。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我这样问他们。不说明什么,这是他们的答复,顶多是那些主角为女性的小说叙述了她们的阅历。我又问,男人难道不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他们的回答让人不安:男性和中立相关联,并且任何一本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都试图普及化,而并非试图说明真相。 一般认为,一个女人在写作时,其实是在发表言论,其中心思想通常受到自身条件的影响(这里所指的条件并不具有普遍性),事实上,很多女性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扮演了她们的传统角色,在文学界,最好的例子就是“鸡仔文学”的存在。鸡仔文学就是白马王子的故事外加职业女性(但添加的这味调料,并未让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变化,因为她们仍旧屈服于一个英雄救美的角色),西语版的维基百科这样解释鸡仔文学:“以前那些雍容华贵的少女,被年轻的、独立的、具有魅力并且希望找到其真爱的职业单身女性所取代,她们每日需要克服在职业领域和个人生活中所出现的问题和精神压力,同时还在寻找她们心目中的理想伴侣。游侠骑士被表现出其感性和温柔一面的商业或专业男士所取代,这无疑是更符合当今时代的一种男性范本。通常情况下,他们都住在都市,比如伦敦,纽约或都柏林”。 最奇妙的是,鸡仔文学的创作者是女性,读者也是女性,最典型的例子是《BJ单身日记》。很应该问一句:这类文学作品的存在,究竟会如何影响读者对远离这一标准的女作家作品的接受程度。第二个问题是,在文学领域里,男性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女性平等(当然,还有其他领域里的女性平等)。一位男作家就有关西班牙报纸副刊上列出的全年最佳小说名单对我和另一女作家表示,由于大部分评审员都是男性,所得结果也几乎全是男作家的作品。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认为,选出的名单是公平和公正的。我回答说,如果重新查看小说名单,总可以发现,女作家一般更会将女作家而非将男作家的小说列入该名单里。对此,那位男作家回答说,这也许是强迫性作出来的决定,他认为,女性作家之所以会选择女性作家的作品,是因为她们觉得有义务这样做,而并不是因为她们觉得女人比男人做得更好。 这无疑说明了男性所认为的顺序,“因为你自己是女人,你自然会仅仅为了维护权利而首先选择女性作家,而并不像我们男人那样,基于真真实实的文学角度而选择她们。”这说明存在着一种看法:没有一个女人可能会比男人更优秀。这是一种保守和天真的立场,但我们的男性同行中不少人都支持这种立场,而阻碍了他们对排外问题进行深思:在视角方面给予平等条件,如此,我们可真正领略到一本文学作品里被忽略的元素,文学才能够升华到一种纯粹的、单纯的和不受传统观念影响的水平。 那天,那位男作家和我们争论了好久。他一再坚持,在整个聊天过程中,我们提到的男性作家比女性作家多。而另一位女性作家则表示,在聊天过程中她提到了多位女性作家,她还指出,她之所以提到了喜欢的所有女性作家,并不是因为她想到了人数比例、为了支持女性作家或是其他类似原因,而完全是因为她读了那些女作家的作品并且崇拜她们,而且她对她们作品的兴趣并非是一样的,就好像她对于所读过的男性作家的崇拜也并非相同。她是要告诉那位男性作家,他之所以会提出前面的那番看法,无非是因为他本人更喜欢和偏爱男性作家的文学作品,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才会认为女人之所以选择女性作家列入最佳作品名单,仅仅是出于比例问题。那位男性朋友用愤怒的口气表示:“不是,不是。我喜欢所有文学作品,不分男女。而这正是区别所在:我不会去想男人还是女人,我也从来不会这样想‘很好,我已投票选择了一位女人。’然而,你们每次看到列出一份名单但名单里却没有女性作家时总是激怒不已”。 我认为,这番讨论使这个话题的尖锐性暴露无遗。女人和男人在文学界或其他领域里不平等,但女性如果以被迫害的心态来获取权力,也绝对不是什么好策略。几年前,西班牙《文化》副刊刊登了一份最佳文学博客名单,其中无一女性文学博客。这让我担忧,倒不是因为名单体现了大男子主义,而是因为因特网是自由空间,任何人都无法阻拦女人作出评论,但在文学评论领域里,就我本人而言,竟不知晓任何由女人写的文学评论博客。依我看,许多女性对掌握权力都有恐惧感,而这无疑是一个文化和社会问题。尽管私下里女性作家也会聚在一起评论小说,但并没有女性代表着因特网上的评论趋势。由于盛行着一种观点,认为男性的视角和看法近似中立,从而引起了女性的犀利评论和愤怒,与女性作家打交道的任何人都不会愿意加入到这类聊天里。女人应当停止抱怨男人不把女性作家列入名单,这种被迫害心态,只会把权力拱手让给对方。 虽然我主张男女平等,但我大部分小说的主角都是女性,在我看来,这和战斗精神无关,更是一个坦然不做作的问题。此外,我的大部分小说都基于自传,我并不是一位厌恶自己的女作家。 在我的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另一个题材是都市。 2009年12月,我收到了漫画家莱安德罗·阿尔萨特的邮件。莱安德罗表示,他很喜欢我在铺展都市故事情节时所采用的方式。我看过莱安德罗的漫画,在往来邮件中,我提到了他那些模糊不清和近似空白的场景给我带来的不安——因为没有头绪而感到的不安。可能会在明天拆毁的大楼、已关闭的工业厂房、幽巷和后院,总而言之,废墟一片,叫人不要回首过去,而应当在现在和未来之间加以平衡。 我坚信都市题材会激起我足够的兴趣。当我说到“都市”这个词的时候,会立即沉浸到故事里去。在一定程度上,都市对我而言具有神话般的吸引力,能从中挖掘出许多神秘题材。 当我想到如何通过写作来描述都市时,脑海中重复出现的是“中心-边缘式”这一概念。我将都市的所有组成元素称为中心,而不仅指地图中称为中心的那个空间。回望20世纪80年代的西班牙,瓦伦西亚等都市的老城区是难以通行的,诚实善良的人极为厌恶流氓无赖和历史中心地区的古老大楼,所谓的中心不过是纯粹的边缘地区罢了;只有资产阶级有权决定都市曾经是怎样的,以及曾经不是怎样的,资产阶级既不会踏过这片土地也不会去提及它。那些无修建计划的古老街道逐步成为下水道,而距瓦伦西亚南部10公里左右的滨海湖景区,无疑比老城更像中心地区。 很可能我杜撰出来的任何故事情节都不会发生在一个中心场景里。回忆一下传统中心地区的场景画面,在文学作品和电影里已被描述了不知多少次——巴黎的整条河左岸、圣路易斯岛以及远处可以望到的埃菲尔铁塔,或者是曼哈顿或马德里中心地区。中心地区体现当今的传奇,继续成为故事情节,它们被过度诠释了。但对许多作家来说,过度诠释也是手段,归根结底,文学不过是用新的方式来重新叙述相同的故事。我并不是指古老的故事情节,而是历史曾经以及继续在社会中起到的作用。几个世纪以前,《圣经》说明了世界的起源,而现在小说也以同样方式向读者说明一些事情,比如通过父亲的过世来试图说明我们是如何构成的以及父母和子女间的关系。 都市的中心无疑被过度诠释了,它们代表着一个阶层,体现了价值观;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边缘也被过度诠释了。在巴黎的某部影片里,通过摄影机可充分了解街道;但在电视频道的庸俗喜剧里,我们总是走不出别墅或是吉卜赛人纪录片中蒙托亚家族的小茅屋。 安德罗·阿尔萨特在给我的邮件中表示,我的叙述思路完全以在城市空间里的感受为依据。有时候,我甚至感觉我的写作和闲逛是同义词。我构思出来的故事情节纯粹是一种借口,用来证明笔下人物走过某些场地而得到的感受。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我挖掘荒凉地带;当然,这和缺乏认识有关,有时候我认为由于城市模式的失败,边缘地区似乎能更好地代表我们。 都市能提供不同的人物形象。和边缘地区相比,中心地区的人物已被写烂;但这些范围会出现变化,也可能给我们造成影响。一些象征性的地方决定了人物和处境,如果叙述的故事情节发生在塔拉韦拉-德拉雷纳或特拉加塞特(西班牙的两个城镇),这恰恰是因为它们并不是什么中心地区,并且有时候与某些读者所期待的正好相反。我认为,就这一点而言,触犯是指与大众口味背道而驰,而当我提到口味时,我指的是美学,同样也指的是伦理学。 我的两本小说标题都包含了“都市”:《冬季之城》和《幸福之城》。这两本小说相互补充,都源自于同一个城市:我童年时代的瓦伦西亚以及我少年时代的瓦伦西亚。在两本小说里,我从来没有确切地提到是哪个城市,但通过它叙述了一些进入青春期之前的少年们是如何对抗感情、道德和成年人世界的观念界线。在《幸福之城》的第一部分,我讲述了一个华人移民家庭,这个故事起源于瓦伦西亚的小街,我曾经在这些小街与一群孩子玩耍,我的一个好朋友是街角华人餐馆老板的儿子。这番回忆,再结合对华人家庭的皮毛认识,促使我下决心叙述华人的移民问题。我并不奢望写成现实主义的小说,这不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因为我既不会说中文,又属于另一个文化范畴。促使我下定决心创造一个华人世界的是文学。在文学领域里,现实主义和科幻一样虚假。 原载:《文艺报》2014年07月04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