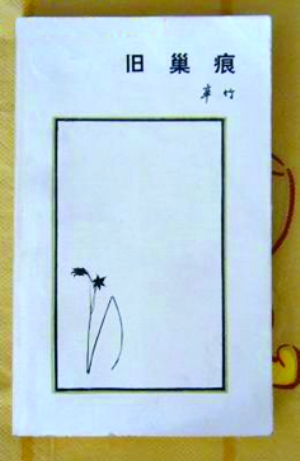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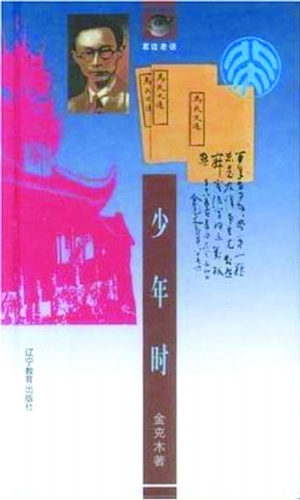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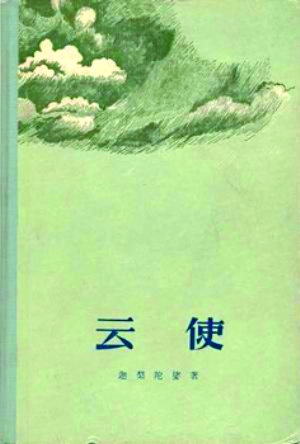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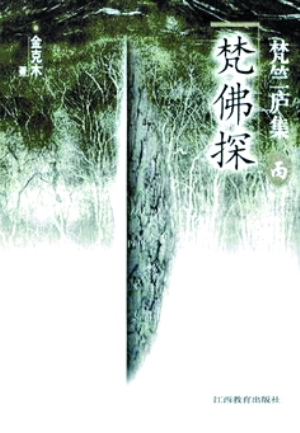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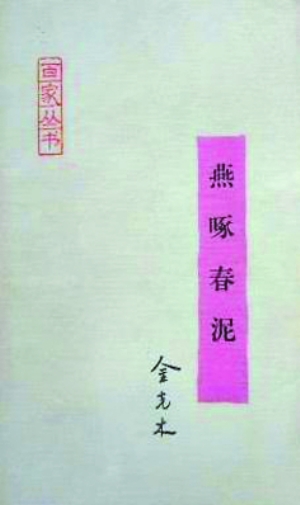 金克木是举世罕见的奇才,靠自学精通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文字。但如此奇才,却并不高高站于云端,倒是总能与最普通的读者交流思想,分享心得。在《读书》杂志最具影响力的年月,这位80岁的老人是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所以陈平原称他为“《读书》时代的精灵”。不过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最熟悉的大概只是他的文化散文,对于其他,却未必了解了。我们撷取老人生命中的若干侧影,不求全面展现金克木的文化成就,只希望能由此抓住老人若干思想余绪…… 【偷师】 燕园四老,小学毕业 关于金克木,流传最广的当然是陈平原那个标签“《读书》时代的精灵”。而在陈平原的回忆文章之前,人们提起金克木,最习惯的称呼,是“燕园四老”之一,另外三位,是季羡林、张中行和邓广铭。不过虽然名列四老,金克木的学历可不怎么样,他只上过一年中学,论文凭,不过是小学毕业而已。 小学生而能成为一代大家,自然是奇才。不过在金克木自己那里,更看重的,不是所谓才能,而是自学的精神与动力———好奇心会驱动一个人自然而然去探求知识,探索世界。且看他是怎么利用北大图书馆的———那时候他的运气好,正好在北大图书馆当馆员。 “这里大多是文科、法科的书,来借书的也是文科和法科的居多。他们借的书我大致都还能看看。这样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我便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读借回去的书”。“借书的老主顾多是些四年级写毕业论文的。他们借书有方向性。还有低年级的,他们借的往往是教师指定或介绍的参考书,其他临时客户看来纷乱,也有条理可寻。渐渐,他们指引我门路。” “这些读书导师对我影响很大,若不是有人借过像《艺海珠尘》(文艺丛书)、《海昌二妙集》(围棋谱)这类书,我未必会去翻看,外文书也是同样。有一位来借关于绘制地图的德文书。我向他请教,才知道了画地图有种种投影法,经纬度弧线怎样画出来的。又有一次,来了一位数学系的学生,借关于历法的外文书。他在等书时见我好像对那些书有兴趣,便告诉我,他听历史系一位教授讲‘历学’课,想自己找几本书看。他还开了几部不需要很深数学知识也能看懂内容的中文和外文书名给我。他这样热心,使我很感激。” 金克木还特别谈到,一位从几十里外步行赶到北大图书馆来的鼎鼎大名的教授,“他夹着布包,手拿一张纸往借书台上一放,一言不发。我接过一看,是些古书名,后面写着为校注某书需要,请某馆第准予借出。借的全是善本、珍本。由于外借需有馆长批准,而馆长那天又刚好不在,这位老先生又一言不发地离去了。待这位客人走后,我连忙抓张废纸,把进出书库时硬记下来的书名默写出来,以后有了空隙,便照单到善本书库中一一查看。经过亲见原书,又得到书库中人指点,我增加了一点对古书和版本的常识。我真感谢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给我用一张书单上了一次无言之课。当然他对我这个土头土脑的毛孩子不屑一顾,而且不会想到有人偷他的学问。” 【通人】 哪里都有“发现的快乐” 金克木的专业,是东方语言,北大东语系,他是初创者之一。而专业之外,文学、历史、翻译等等,都算是他的爱好。他写诗,写小说,都相当有成就,而最不一般的,是对天文学的研究。 早年金克木对于天文学有特别的兴趣,不仅翻译过英国天文学家秦斯的《流转的星辰》,以及《通俗天文学》等著作,还发表过天文学的专业文章。文理兼通,本来是老一代文化人的通例,算是如今已然失落的传统之一。不过金克木却尤为不同,他不但兼通,而且兼精,这也就给他的思考带来更多天马行空的色彩。老人晚年的文章能如此吸引读者,这大概是原因之一。早些年,人们回忆起去金克木府上拜望的情景,总对他天马行空无所不知的博学与思维惊叹不已,说起来,他年轻时还差点真的就干上了天文这行当,把他拉回文学的,是戴望舒。 上世纪30年代,著名诗人戴望舒非常欣赏金克木的文学作品,他写了一首《赠克木》,让他在星辰天空之外,更多看看人间,算是帮金克木确定了人生的选择。不过放弃天文学爱好后,金克木颇有遗憾,他曾在一篇随笔中感叹,“离地下越来越近,离天上越来越远。” 除了天文学,数学也一直为他所好,金克木早年即同数学大家华罗庚很谈得来,华罗庚也是文理兼通。金克木曾钻研过费尔马大定理,临终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还涉及高等数学的问题。他还曾和著名数学家江泽涵教授在未名湖畔讨论拓扑学的问题。他还曾就具体的数学问题请教过丁石孙先生,并从丁石孙先生的解释中判断出他所擅长的数学研究领域。 及至晚年,武汉大学教授李工真去拜访他的时候,“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谈起他近年来对世界数学发展史研究上的心得。他发现15世纪以后所有近代初期的西方思想家和科学家几乎都是数学家,而数学可以说是科学的神经,显示着文化的缩微景象。” 接着,金克木又与李工真谈起作为学者应有的精神状态问题,李工真想起爱因斯坦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行的马克斯·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探索的动机》,便背给他听:“……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金克木很满意,便笑了笑说道,是的,我这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发现的快乐”。 【教书】 从语言到哲学 金克木擅长多门外语,他曾经凭借历史学家傅斯年(被人称作“傅大炮”)赠送的一本书,掌握了拉丁文。在《忘了的名人》一文中,他生动记下了当时的情形。 1939年暑假,进入湖南大学教法文的金克木到昆明访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常培,罗给了他一张名片,介绍他去见在昆明乡间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 在一所大庙式的旧房子里,一间大屋子用白布幔隔出一间,里面只有桌子椅子。傅斯年叼着烟斗出来,彼此在桌边对坐后,两人开始交谈。 傅斯年讲了一通希腊、罗马,并说,不懂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究什么希腊史。他忽然问金克木,你学不学希腊文?我有一部用德文教希腊文的书,一共三本,非常好,可以送给你。金克木连忙推辞,说自己的德文程度还不够用作工具去学另一种语文。用英文、法文还勉强可以,只是湖南大学没有这类书。傅斯年接着闲谈,不是说历史,就是说语言,总之是中国人不研究外国语言、历史,不懂得世界,不行。后来,傅斯年再次说到用德文教希腊文的书如何如何好,想送给金克木,金克木再度拒绝。 忽然布幔掀开,出来一个人,手里也拿着烟斗。傅斯年站起来给金克木介绍,这是李济先生。随即走出门去。回屋后,傅斯年放了一本书到桌子上说,送你这一本吧。李济一看,立刻笑了,说这是二年级念的。金克木拿起书道谢并告辞。这书就是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的《高卢战记》。金克木试着匆匆学了后面附的语法概要,就从头读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来兴趣越大。据此,他掌握了拉丁文。 上世纪40年代,著名学者吴宓任武汉大学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又是校务委员会委员,他推荐金克木到外文系教梵文。当时,武汉大学找不到教印度哲学的合适人选,而这门课程又是必修课,文学院长刘永济就把金克木安排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 这样一来,吴宓不放心了。他十分认真地对金克木说,你教语言文学,我有信心。到哲学系去,我不放心。金克木回答说,到哲学系对我更合适。因为我觉得,除汤用彤先生等几个人以外,不知道还有谁能应用直接资料讲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而且能联系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哲学,何况我刚在印度度过几年,多少了解一点本土及世界研究印度哲学的情况,又花过工夫翻阅汉译佛典,所以自以为有把握。吴宓仍不放心,还特意在教室外听了金克木的第一堂课。结果后来,金克木连语言带哲学,就这样讲了下去。 【艺文】 写诗译文最轻灵 鲜有人知道,金克木是上世纪30年代新诗坛的重要一员,他和戴望舒、徐迟等人交往很深,其《蝙蝠集》和《雨雪集》是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文献。金先生晚年还写作了大量古体诗。除诗歌外,他还写有小说《旧巢痕》、《难忘的影子》,以及多部散文集。他曾写有《少年徐迟》一文,论及两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都向施蛰存先生主编《现代》杂志投新诗稿,并经过施蛰存介绍相识的情形。 诗人杜南星1939年曾作《忆克木》一文,追忆了金克木创作新诗的情形: “……某一夜,我在《现代》上见了金克木的诗,生疏的作者,凝练的诗篇。那题目是《古意》,字句已经完全遗忘了。我对这诗坛新人起了一些微微的遥望之情。过几天,一位姓张的同学告诉我说有人愿意见我,问什么时候有工夫,那位客人正是《古意》的作者。 有了主客三人的我的小屋里灯光亮了,语声也繁密起来。我初相识的诗人是一个身材不高,眼睛和嘴唇充分露着捷才的青年。十分健谈,毫无倦意。. 第二个晚上他又来敲门了。我们很快地熟起来,毫无拘束。我们谈了许多关于文艺思潮,写作技术,和诗歌的新形式及内容的话。因为我把自己的小文给他看请他批评,他也就把他的诗歌和散文带了来,说是‘投桃报李’。那些散文写得明快犀利,文如其人,论文杂感居多,都是从他和一个朋友合办的周刊上剪下来的。诗歌可是珍贵的手稿,达到轻灵自然的最高点,这特色一直在近三四年的诗人之群中露着头角,无人可及。” 金克木第一次翻译一首诗中的一节,是从世界语译出的,30年代初发表在北师大一个学生编的周刊,当然没有稿费。以后,金克木和黄力给另一家报纸编了几期文学周刊,只有每月六元的编辑费,没有稿费。为了凑数,他从世界语译出了两篇短篇小说,《海滨别墅》和《公墓》。两位世界语者,蔡方选、张佩苍,办起了只有名义没有门面的“北平世界语书店”,出版了两小本《世汉对昭小丛书》,一是蔡方选编的《会话》,一是金克木的这两篇小说。他得到一部世界语译本《法老王》的上中下三大本作为报酬。由此,他进入译匠时期。 此时,金克木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每月工资40元。他一年译两本书就够全年天天上班的收入了,他想何必还要坐班?自《通俗天文学》开始,金克木下决心以译通俗科学书为业,计划半年译书,半年读书兼旅游。哪知人算不如天算,“七七事变”爆发,他的译匠只做到了1937年。 ■ 金克木说书 对绝大多数读者而言,金克木关于读书的文字,是最亲切也最有实用价值的,他的相关随笔,甚至被编成一部《书读完了》,影响颇大。这里撷取金克木论《礼记》的部分文字,从中可以看出金克木读书法的一斑,他对读者的思想触发,大抵类此。 与书对话:《礼记》 有要求人跪着读的书———神圣经典,句句是真理,在真理面前只有低头。 有必须站着读的书———权威讲话。这是训话,没有讨论余地。受教育的人只有肃立恭听。 有需要坐着读的书———为某种目的而读的书。这样读书不由自主,是苦是乐,各人感觉不同,只有坐冷板凳是一样。 有可以躺着读的书———大多是文艺之类。这样读书,古名消遣,今名娱乐。 这是以读者为主,可拿起,可放下,可一字一句读,也可翻着跳着读。通常认为这不算读书,只是看书。有人认为有害,主张排除。有人认为可以保留。 还有可以走着读的书,可以一边走一边和书谈话。书对读者说话,读者也对书说话。乍看是一次性的,书只会说,不会答。其实不然。书会随着读者的意思变换,走到哪里是哪里。先看是一个样子,想想再看,又是另一个样子。书是特种朋友,只有你抛弃它,它决不会抛弃你。你怎么读它都行,它不会抗议、绝交。 所以经典也可以走着读。 …… 忽然想起《礼记》。为什么?因为在大学里多年以后才记起了《大学》这部书。这本来是《礼记》的一篇,宋朝晚期朱熹才把《大学》和另一篇《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和《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从元朝起受到特殊的尊重。可是直到今天好像也没有人追溯这两篇互相独立的文的来源《礼记》,不问为什么“三礼”(《周官》、《仪礼》、《礼记》)之一的书会包含这两篇政治哲学文丛。《礼记》是由西汉戴氏叔侄传下来的,本身是一大“文丛”,讲说礼的种种规定,解说各种礼的意义,还记录孔门弟子的言行,以礼为核心而不限于礼。讲儒家而不讲《礼记》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天朝大国”不是“礼仪之邦”吗? 二十世纪的人类学对各民族、各种社会、各种人的“礼”,或说是社会关系的行为符号,非常注意,从调查其表现形式到解说其内容意义和所起的作用,逐步深入、扩大,而且由“野蛮”转向了“文明”。近些年来对于西藏的密宗仪轨的兴趣越来越大,心理学家容格简直入了迷。调查南美的列维。斯特劳斯慨叹未能调查理解佛教,他还不知道儒家更与他相近。孔子一眼看出了“礼”是社会结构的外在表现,把制礼作乐和礼坏乐崩作为治和乱的两种符号形态,这实在是一大发明。“忠字舞”、“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等等都是礼乐的“破旧立新”的失败尝试。古礼仿佛很繁,实际上有增减变换。磕头改鞠躬,长袍变西服,意义一样。 本世纪二十年代,我还年幼,已经参与过残存的婚丧交际礼仪,大体上还是如《礼记》所记。书上繁琐,做起来并不麻烦。后来接触佛教徒,又知道行为戒律第一要紧,是生活的规范,团体的生命,分派的条件,轻易破坏必自受其害。行为第一,不是理论第一。基督教做“弥撒”、做“礼拜”,伊斯兰教“五拜”、“朝圣地”,都是“礼”。“嬉皮士”留长发,男扮女装,不过是用一种礼替换另一种礼。连“女权运动”着眼的也是礼。大会示众、批判、检讨也都是行“礼”。礼就是共同的风俗习惯,比法律更为有力。社会无礼,不能安定。《圣经·旧约》是犹太人的《礼记》,《梵书》是古印度人的《礼记》。 以上独白是从我和《礼记》的对话来的。不妨抄下几段原始记录,书人对话。 书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定是非也。 人 我明白了。这句话的第一点是民法,第二点是刑法,第三点包括国籍法、移民法,第四点连所谓“法哲学”都有了。思想很现代化呀。 书 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人 了不起!这不是兵法的“知己知彼”,避免片面性吗?情人、夫妻之间若遵这条礼,大概离婚率可以降低了吧? 书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 人 这里大有文章。“言”不能决定本身性质归属。只会说好听的话不能算数。 书 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人 这是国际准则也是人际习惯吧? 还有来回讨论,不能记了。这只是第一页里的几处句子。 书是好朋友。与书对话,其乐无穷。连干燥的古书《礼记》都能活跃起来,现代化。不会读,书如干草。会读,书如甘草,现代化说法是如同口香糖,越嚼越有滋味。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