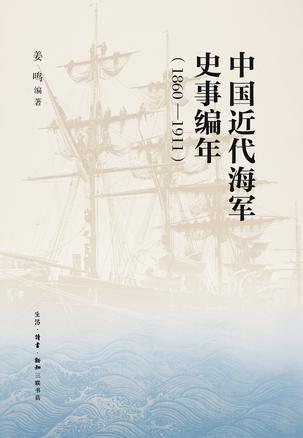|
文 | 姜鸣 *本文原为1994年版《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跋语。 我说不好自己是怎么会迷上海军史的。我没有当过一天兵,家族里也没有军人的血缘背景,许多朋友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我只能笼统地说,这是一种兴趣吧。 回想起来,几乎每个男孩,都有过对军舰、大炮、飞机着迷的经历。我开始迷恋军舰,是在 1965年“八六海战”之后。那时,我刚上小学。大家把小炮艇打败猎潜舰的故事听了一遍又一遍,又看了电影《海鹰》,心中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激情,经常步行十几里路,到南京西路“翼风航模商店”去买制作舰艇模型的木料和胶水,把断钢锯条磨制成锋利的小刀,认真地制作船模。还到处收集关于军舰的图片资料。邻家孩子有本旧杂志,上面刊有 1956年苏联太平洋舰队“德米特里·巴日尔斯基”号巡洋舰访问上海的照片,这成了我们研究外国军舰的宝物,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三联装的主炮塔,从此意识到巡洋舰的凛凛威力。那会儿,我做了艘鱼雷快艇,邻居孩子做了艘“里加”级护卫舰,大家玩得很开心。 我的少年时代是个没有书读的年代。往前推溯若干年,出版社也只出版介绍苏联海军的读物。所以,我当时对西方海军几乎一无所知。 70年代初,我随母亲下干校,那里的图书馆尽管堆满了从各机关集中起来的书籍,我能读到的,仍是苏联人编写的从彼得大帝创建俄国海军到十月革命后红军舰队击败进攻喀琅斯塔得要塞英国舰队的故事。在反复放映的电影《列宁在十月》里,我有机会看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发炮的雄姿。 1977年重映《甲午风云》,我看到电影里的邓世昌在“致远”舰望台上披着斗篷,举起指挥刀,发出气壮山河的最后命令“撞沉‘吉野’!”时,激动得血脉偾张、热血沸腾。  “致远”,在英国阿摩士庄船厂定制的巡洋舰。 甲午战争中,因管带邓世昌英勇作战、与舰同沉而出名。 中学毕业后,我进了一家航空工厂,参加制造我国第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天天在飞机上钻来爬去,摆弄驾驶盘、襟翼、副翼、方向舵、升降舵之类玩艺儿,自然也关心中国的军事工业。我从《航空知识》一直读到《简氏飞机年鉴》,把美国、苏联的飞机性能指标背得滚瓜烂熟。想到中国主战飞机与国外的差距,便黯然神伤。听说要进口英国“鹞”式飞机的传闻,就禁不住怦然心动。空闲下来时,工人们常常放言阔论国际关系和国防战略,虽非肉食者,却不乏闪光的真知灼见。我也爱掺和其中,以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相信,如我从小开始从未有人着意灌输的那种期望富国强兵的潜意识,显然是多数国人皆有之,且是从古到今贯穿之的。 1981年底,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二年级。大约是我在听沈渭滨师讲授中国近代史课时喜欢频频发问的缘故吧,有天课后,沈师把我叫住,问我晚上是否有兴趣参加一个学术聚会,我自然说可以。当晚我便按照沈师告诉的地址,找到学生俱乐部二楼的某个房间。原来,沈师有意在中国近代军事史荒疏的处女地中独辟蹊径,正指导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教师和高班学生做专题研究。那时四年级的刘申宁兄,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属校内知名人士,在俱乐部里独占一屋,这次便借他的宝地来作学术活动场所。我津津有味地听了申宁兄作的关于江南机器制造局武器生产的报告,郭太风兄作的关于清军粮饷制度的报告,以及沈师对近代军事史宏观研究的演讲。接着,沈师问我是否有兴趣研究近代军事史中的某个分支课题?我脑中的军舰飞机记忆在一刹那间全部复活,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由于觉得空军历史实在太短,于是选择了海军史,当我从俱乐部出来的时候,心里有种畅快的感觉,对着清冷的满天星斗作了个深呼吸。但我当时未想到,后来我会在这个研究领域倾注如此多的精力。 从大二便进入专题研究,似乎早了些。但 80年代初,校园里正弥漫着读书气氛。莘莘学子都想把被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写论文搞创作都是文科生的时尚。不能发表,贴在墙上也很满意。交谊舞刚开始流行,且被限制在周末。谈恋爱为校规严禁。到校外“扒分”,更是闻所未闻。每天晚饭后,图书馆门前照例挤得水泄不通。为争夺阅览室的座位牌,几乎可以打架。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投奔怒海”。 刚开始研究时,沈师给我定了个指标:用十年时间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海军史专著。同时又做规定:从专题研究入手,先做大事记和资料长编。没有完成大事记和资料长编不写论文,没有完成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专题论文不写专著。从此,我便在中国近代海军史的研究领域中开始了艰辛的耕耘。 历史犹如散落在沙滩上的破碎镜子,赶海者不用太费力便能拣到一些残片。在不同的光线下,镜片都折射着熠熠光彩。问题是,当细碎的镜片与石英砂混杂的时候,赶海者能收拢多少残片并在多大程度上复原那面镜子?收集是复原的前提,靠的是勤奋;复原是收集的成果,凭的是智慧。而复原的目的,则是为了给现实提供借鉴。夫子们教诲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说一句空”,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从《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和《李文忠公全书》入手,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爬梳,以建立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直接感受。啃书本是很枯燥的。悬梁刺股,只是种形容。放弃中午休息,抱着书本忍不住打瞌睡,却是人之常情。复印对穷学生是奢侈享受,大量文献只能手抄。好在当时复旦图书馆对清末的线装书控制得还不太紧,只要有复本,学生也能借走;孤本书可以调到阅览室去看。《清实录》嘉业堂抄本,属于复图的宝物,备战备荒时被装箱,后来不再开启。但有台湾华文书局的影印本,使用反更方便。这种研究条件,至今仍使我怀恋。记得高班某兄认真钻研了几年《李文忠公全书》后,不无得意地向我宣称:那些研究甲午战争的先生,其实没有认真通读过《李集》。《李集》里蕴含着丰富的宝藏,足以重写历史,足以向学界前辈挑战。此话说过,转眼十余年矣,我自己早已离开学界,也未与某兄互通音问,不知他境况如何。但回想起他那时的野心,确也觉得孟浪有趣和纯真可爱。  李鸿章、周馥等人主持起草的《北洋海军章程》 我不敢生取巧之心,只有埋头读书。倒不是书中有黄金屋颜如玉,而是从枯燥乏味的字纸中看出了趣味,看出了一段段活生生的故事和一个个水灵灵的人物,按照自身的逻辑在喜怒哀乐,在寻求发展,在思维决策。不管是大人物还是普通人,都和今人有相通之处。中国人的民族秉性和思维特点,如同遗传密码,会在冥冥之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过去中国走过的道路,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所以,我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以为后人应当设身处地地理解先人、再现先人,研究他们的思维逻辑、强点和弱点,以及这一切给历史带来的影响;而不是随心所欲地曲解先人、强奸先人,把他们当作表述自己观念的传声筒。这个观点自然算不得新潮,但真正以此指导学术,说真话,抒真情,不欺世,不欺己,却是很不容易的。1984年5月,在我大学业之前,《复旦学报》发表了我的首篇论文《北洋购舰考》。同时,我在最后一个学期,按照毕业论文的要求,写成了两篇论文:《北洋海军训练述论》和《北洋海军经费初探》,并一直在做海军史大事记。留校执教后,我住单身教师宿舍。不论寒暑,不问气候,每天早晨7点15分起床。漱洗完毕,背上书包,拿上一个碗袋,先去食堂吃早饭,再去图书馆看书。中午11点45分,去吃午饭,12点15分又回图书馆。晚5点,吃晚饭,踏着校广播台播出的音乐节拍散步。至6点,重返图书馆,直至9点45分,工作人员打铃,才拖着疲乏的步履回宿舍。只要没有会议,没有课程任务,天天如此,周而复始。就是在这段日子里,我完成了一堆海军史论文和本书的初稿。生活很平静,但很充实。同时,我还大量阅读海军史料以外的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我钦佩黄仁宇对体制及操作层面的独到思考和曼彻斯特结构浩瀚史料、再现社会生活场景的天才。 平心而论,我以为自己是个能耐寂寞、能坐冷板凳、能吃苦做学问的人。但我又是个理想主义者,总有轰轰烈烈做番事业的雄心,总想多涉猎人生,以使有限的生命更丰富多彩。记得还在工厂的时候,几位师傅劝我不要考大学,以为读书必定吃亏。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说,我想读大学,并不是为了摆脱工人身份。而是4年的工厂生活,已经使我看到了继续待在厂里,30年后大概是什么模样。同样,留校当教员,虽然正是我毕业时的强烈愿望,但当这个愿望实现之后,也立即使我看清了生命的终点——矻矻碌碌,从助教爬讲师、爬副教授、爬教授、爬博士生导师。我相信,这确是条灿烂光明的路,但何尝又不是条泥泞艰辛的羊肠道呢?4年的专业训练,使我深爱历史这门学科,但一个优秀的史家难道就非一辈子待在象牙之塔里吗?我不相信。所以,当一年后,市里机关来校调我的时候,我立即就走了,没有犹豫。 离校前,我应当时在上海市人事局工作的唐克敏兄之约,写了篇论文:《劳动者应当有权选择自己的职业——试论人才流动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首次提出择业权的概念。文章指出:“在打破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当代社会,任何人,任何单位或组织,都无权把劳动者终身禁锢在一个特定的岗位上,无权拒绝劳动者要求变换工作环境和兴趣、要求辞职的权利。有无择业权,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论文在国家人事部召开的全国人才交流理论讨论会上宣读,引起了一番争论,但受到广泛好评,并使我获得全国十家人才刊物联合评出的“人才研究新秀奖”。文章反映了我当时对人的生存权的思考。我相信,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人们可以同时扮演多种社会角色,比如,我即使到了机关,依然可以做历史学家,而不必做一个职业官僚。 我初进机关那几年,工作极为繁忙。但是,就在工作最为紧张的时候,我也始终没有忘记1981年底,一个历史系学生向老师做出的承诺。承蒙我的领导——张序敏、沈懋兴先生的关照,我依然能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1986年底,我出席了全国第一届中国近代军事史讨论会。会上,学术界的朋友们建议我,应当开始撰写中国近代海军史专著了。军事科学院的张一文先生,还聘我担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清末海军”条目撰写人。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厚爱和器重。正是在北京西山娘娘府军科招待所,我作出了决定:从明年1月1日起,开始写作中国近代海军史。每天写1000字,不管时间多紧,也要完成这部著作。 离开复旦后,我一直过着两栖生活。结束了白天工作后,我的风帆就在历史的海面上巡洋,查阅、考证、写作。两者间的距离是那么遥远,却又那么贴近。困难首先表现为时间和资料,更深层次的则是洞察力和识见。研究近代海军史的过程,其实也是我对整个中国近代史乃至中国社会的思辨过程。中国近代海军从创建到失败的历史教训,总使我的心灵震颤不已。随着深入地钻研,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见解。我觉得自己像是个掘宝人,手中的洛阳铲已经从地底掏出了宝物的碎片。 用了一年半的夜晚和星期天,我完成了《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的初稿。又经历了一年有半的磨砺,这部专著终获出版。在我困难的时候,许多朋友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使我终生难忘。获悉该书出版,赵启正部长亲自撰写了推荐书评。上海历史学会专门召开了书评会。一位素昧平生的留学生给我来信,告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东亚图书馆收藏了此书,以及他读该书的体会。更有我的同事姚晓亭君,认真对《龙旗》全书作了详尽的批注,使我得益匪浅。中学高班学长马逸群博士,在挪威从事用电子衍射作材料结构研究的同时,也多次给我来信,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探讨近代化失败的教训,使我深受启发。  《龙旗飘扬的舰队(甲午增订版)》 姜鸣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接着,在杨志本同志的推荐和张炜女士的直接操作下,海军学术研究所内部印行了我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未久,我离开工作了七个年头的机关,转入公司。 进入90年代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大学到社会底层,到处充满了躁动和不安。市场经济和发财成为社会关注的主题。听说我去经商,朋友们议论纷纷。其实,在我想来,原因很简单:一是想直接感受世纪交替之时社会的变化,以加深人生阅历;二是锻炼自己的从事经济工作的能力。但我依然书生本色。今年是甲申中法战争110周年和甲午中日战争100周年,我要用自己的方式祭奠在这两场民族战争中牺牲的海军将士,我献上的就是这本《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也是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完成的。它以《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为基础,增补了大量记事和图片,和《龙旗飘扬的舰队》恰好互补。书中记事,尽可能采用第一手原始史料,并进行了必要的考证。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采用编年体的方式展现历史场景,是历史学最传统也是最重要的表达手段。虽然作者自己并不直接阐述观点,但依靠历史自身的逻辑,却能产生强大的说服力,读者也就在阅读之中,感受到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种种细节和重重困难。如前所述,历史是难以完全复原的,但沿着时间走廊,把搜寻到的残片逐一定位,毕竟能够接近事件的本来面目。记得七年前,我与赵幼雄先生合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考证制作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模型。开始时,仅有几帧照片和一张简图。我们奉行宁缺毋滥原则,模型上每件设施都要有来历,找不到依据的不放上去。模型交付后,我们的探索并没有停止。本书所附的舰体图,“定远”改了七稿,“致远”改了四稿,“经远”“超勇”“平远”等都改了三稿。这一次次改动,凝聚着作者大量心血,也越来越接近历史真实。《史事日志》的条文,同样体现出这种精益求精的追求。我想,这些努力对于推动中国近代海军史的研究只要能有绵薄之力,我就感到满意了。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 姜鸣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在我编撰本书时,许多朋友给我提供了无私帮助和指教。他们包括:我的老师沈渭滨、陈绛教授,我的同学后志刚、许敏、蔡伟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许华兄,军事科学院的皮明勇少校、刘庆少校,海军的杨志本先生、张炜中校,山东甲午战争博物馆的戚俊杰馆长,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吸收了当代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被引用论著的学者,在此一并致谢。我特别要指出的是,台湾师范大学王家俭教授的论文,旁征博引了大量外交档案资料,对我帮助很大。 我感谢好友钱钢兄为本书撰序。七八年前,我鼓动他写历史纪实文学,写中国近代海军。我们为此神侃了几年,从现实的改革谈到历史,谈到历史上改革失败的教训以及历史上为改革捐躯的仁人志士……钱钢兄的《海葬——大清国北洋海军成军一百周年祭》,以其磅礴的气势和独到的见解,使我激动、给我启迪。 世界航海模型运动协会国际裁判赵幼雄先生在香港探亲期间,为本书绘制海军舰图,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陈伟庆女士为本书绘制历史地图,三联书店潘振平先生为安排本书的出版,军事科学院的张一文研究员担任本书的特约编审,都付出很大心血,谨向他们深表谢忱。 我的父母、我的妻子李家玻对我的事业所给予的最直接的支持,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我也向他们深致敬意。 1994年4月18日晨2时于上海望亭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