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足利学校。日本最古老的学校,大成殿内供奉着建成于1532 年日本最早的木造孔子坐像,
江户时代时,每月1日和15日举行孔子祭祀仪式(释奠)。
*文章节选自《孔子的学问:日本人如何读论语》([日]子安宣邦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6)“导读”。
近现代日本与《论语》解读
文 | 林少阳
在东京,对于许多人来说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它是永远营业的小食堂、小百货、小报摊、小邮局、小书店等等,可谓功能齐全。近日发现,在连锁便利店 Lawson狭小的书架上摆着一本《论语》解读书,作者佐久协,在一家有名的高中教授古汉语——文言文。近年他已经面向以高中生为主的一般读者写了三四本关于《论语》的通俗读物。是否畅销,从其在便利店可以购得,即可获得答案。便利店通常只卖少量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论语》解读也“晋身”其中,足见《论语》在今日日本社会巨大的影响力。其实,这一影响力也可以从普通日本人的人名中窥见。以“诚”“谦”“真”“仁”“文”“孝”“信”等儒学概念入名者,比比皆是,虽然大家未必留意这些是儒学的概念。
中国现代史曾激进地否定传统,但日本的情形有所不同。尽管日本有过以“脱亚入欧”为标志的现代化国策,但是,在近代日本的非学术世界中,与《论语》有关的出版物似乎从来都是长销书,它更没有被归入“四旧”,因而遭遇被“扫”、被“破”的命运。当然,无论被“扫”、被“破”,还是被奉为至宝,情况往往是复杂的。在日本,《论语》的出版热近年来尤其明显。当然,近年的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哲学研究者中岛隆博留意到一个事实:在现实日本社会的《论语》热中,孔子“礼”的实践其实是被忽视的,而且孟子、荀子、朱子也被完全排斥。中岛指出,日本近年的《论语》热,基本上是在“教养主义”这一近现代日本的传统中。 “教养”是西文Liberal Arts的日文汉字翻译,原本是指欧洲的传统教育理念,也指欧洲传统的自由七科(语法、逻辑、修辞、几何、算数、天文学、音乐)。在今天的日语中,“教养”与汉语学校的“通识”意思有所不同,主要指的是一个人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现代社会所(应该)具备的文化知识、基本知识体系。在此意义上,“修养”这一日文汉字的翻译本身显然也是日本现代教育理念的产物。但是,另一方面,“修养”一词也很易令人联想起“教化”与“修身养性”之类的儒家字眼。
确实,至少战后的“教养主义”的《论语》与个人的道德培养有关。也可能是因为日本的《论语》热与现代日本的教养主义有关,儒学本身所有的政治批判性就很容易被冲淡。这一点正如中岛隆博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儒学热受到了左右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欢迎。日本的自由派通常对保守化是比较抗拒的。但是,就连自由派都欢迎这一《论语》热,正是因为日本战后的《论语》热流通于日本特有的教养主义氛围中。
就保守的例子,中岛隆博举出的是斋藤孝的《论语》解读著作《想读出声来的〈论语〉》(『声に出して読みたい論語』)。斋藤孝本身是某私立大学教授,属于媒体明星学者一类,热衷于面向大众发言,并广受欢迎,该书提倡读《论语》,以提高“国民品格”。就努力恢复《论语》之批判性的例子,中岛也援引了加藤彻面向社会大众的《其实是很危险的〈论语〉》。加藤彻警告日本读者,《论语》既可是毒药,也可以是良药。“毒药”似可理解为保守性,“良药”则似乎可理解为批判性。加藤彻尤其提醒日本读者大众,《论语》也是一本关于革命、曾经带来反抗的读物。他列举出江户后期的阳明学徒大盐平八郎(1793—1837)如何知行如一、身体力行而揭竿而起 a;他也提及幕府末年武士吉田松阴(1830—1859)如何视孔子为革命家,以阳明学培养维新志士,改写日本历史。中岛援引加藤彻的讨论,认为今天《论语》这一教养主义式的阅读,是“兑过水的儒教”,也就是说,是将儒学本应该有的批判性抽离后的“教养主义”(同中岛前文)。中岛提醒读者,近年日本这一《论语》热,并不意味着有谁希望将日本人变成过着儒教生活的儒者,而仅仅是希望抽离出某种儒家“精神”,去支撑今天日本的道德提升。作为倡导“批判性的儒学”概念的中国哲学研究者,中岛对《论语》的保守化的批判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为什么中岛对提升“道德”如此介怀?为何日语的“道德”对日本知识界来说听起来如此不舒服?这一问题涉及日本近现代以来“道德”这一概念的特殊(亦即保守)的流通方式,这一特殊(保守)的流通方式与近代日本儒学在近现代日本意识形态中特殊的(保守的)位置不无关系。一方面, “《论语》与算盘”这一实用的应用方式,确实曾是《论语》在近代日本的一面。涩泽荣一(1840—1931)被称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之父”,他曾是幕府武士,后成为近代著名的金融官僚与成功的实业家,但在今天同样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写的《〈论语〉与算盘》(1916年)一书。在书中他主张“义理合一”的经济道德合一论,成为近代日本功利主义的典型。
另一方面,从明治中期开始至“二战”结束之前,日本的《论语》则更多与国家意识形态之构成部分的“道德”直接有关。西村茂树(1828—1902)是日本启蒙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成员(明六社成立于明治六年即 1873年,因而得名),如子安宣邦在其《汉字论:不可回避的他者》一书中指出的,西村折中“西国之哲学”与“儒道”,在 1886年左右建构起与新的明治国家意识形态配套的所谓“国民道德论”。在这一时点上,日本的儒教开始与天皇意识形态发生了紧密的关系,而西村茂树也是建议天皇颁布宣扬“忠君爱国”的《教育敕语》(1890年)的智囊团的一员。《教育敕语》是将儒家天皇意识形态化的直接结果,其主旨是将儒教重构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神道国体论的一部分。如子安宣邦在《汉字论》中指出的那样,日本的哲学家井上圆了(1858—1919)的《伦理通论》(1887年)与《道德摘要》(1891年)将西方的ethics、moral philosophy及 moral sciences都翻译为“伦理学”,这一“伦理学”包含道德,而这一伦理学与明治国家的确立是相辅相成的,“伦理学”的确立本身一开始就是近代明治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在学术中的反映,是大写的“日本国民道德论”。
作为日本学界的定论,《论语》被认为是在 4世纪由百济儒者王仁与《千字文》一起带入日本。日本汉学家竹内照夫(1910—1982)指出,在 6世纪(继体天皇),百济的五经博士来到日本,飞鸟时代(6—7世纪)谶纬说传到日本,并被名之曰“阴阳道”,日本此时对汉代、三国、六朝的学问、思想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从考古成果来看,7世纪日本便有《论语》遗物,德岛县观音寺遗迹曾经出土《习字木简》。但是,应该说,儒学在日本从一开始就有着与中国儒学不同的面相。首先,因为日本的儒学是与佛教一起传入,而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儒学与诸子学已经有很长的历史。由此,当然也可以同时说,日本的佛教与儒学也因此有着不同的面相,因为日本的佛教与儒学从进入日本开始就与权力者有着直接的关系。其次,中国儒学在中国特色的文官体系中有着特殊位置,因为中国、朝鲜有科举制度,而日本则是没有的。正如江户儒者荻生徂徕在《答屈景山》中所言“且此方之儒,不与国家之政,终身不迁官”。此外,如加地伸行指出,中日儒教的最本质的区别之一在于姓氏意识,因中国近代以前同姓不婚,而日本明治以前无姓者居多,所以相对易收养子,家庭在日本也因此容易被认作是组织,而非如在中国家庭被认作是“血缘集团”。这种不同也反映在中日的宗法制度上。中国学者官文娜曾系统地研究日本养子制度对中日不同的“家”意识所带来的影响,也探讨了因此带来的继承制度的不同,以及中日在“义礼”、功利主义理解、身份制、契约制等方面的区别。
记录朱熹(1130—1200)学说的书籍传入日本,多被认定是在镰仓时代(1185—1333)初期 。但是,传入后的朱子学长期只在日本佛教禅僧范围内被研究,在室町时代(1336—1573)这些研究已经显示出对朱子学的相当理解,但朱子学从日本佛教的辅助学说中完全脱离出来,则被认为始于江户时代朱子学嚆矢之藤原惺窝(1561—1619),其朱子学也被认为混杂了陆九渊(1139—1192,象山)的思想。之后,朱子学成为江户幕府的官方思想。日本汉学家阿部吉雄(1905—1978)如是概括了日本朱子学的作用:第一,日本的朱子学强化了基于理性之合理主义思想,一反中世日本(镰仓、室町时代)祈求佛教、神道教保佑来世之风,而强化了人们相信现世并建设人伦秩序的信心;第二,朱子学作为理想主义的道德哲学,增强了人们的道德心性;第三,朱子学有利于幕府政权强化国家统合,朱子发展了尊崇《春秋》大一统的思想,重视君臣上下的道德,因而强化了全国武士、领地属民通过各个大名归属于幕府将军的秩序,成为强化天下一家的官学;第四,与此同时,在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等著作大一统正统论的长期浸淫下,并且在幕府末年外敌当前、内忧不断的时期,在幕府抑或天皇的政治选择中,朱子学也为人们选择天皇、实现明治维新的王政复古而埋下了理论的伏笔。
就朱熹在《论语》解释史上的位置,子安在本书绪言中说:
南宋学者朱熹( 1130—1200)的出现一举改变了传统的阅读方法。朱熹创立了一套包含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哲学体系,即“朱子学”(性理学或理学)。他正是从这套哲学体系出发重新解读《论语》的。(中略)在中国、朝鲜,乃至在日本,朱子的注释都被视为《论语》解释的最基本的依据。日本江户时代盛行朱子学,人人皆读《论语》,其实当时读的就是朱子的注释。朱子是从本质上重读《论语》的第一人,甚至可以说,假如没有朱熹的《论语集注》,就不存在什么《论语》的注释。
江户日本的《论语》解读处在朱熹的强大影响之下,而反朱熹的思想,也脱胎于朱熹的思想之中。江户儒学史上反朱熹的代表伊藤仁斋(1627—1705)与荻生徂徕(1666—1728)无不出身于朱子之学。
虽然子安先生的这部讲义是面向市民授课的产物,但既然作者本人说明,《孔子的学问》是“思想史家读的《论语》”,自然不太可能是一本入门书,当然也不太可能是很学院派的著述。在此有必要就子安本人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子安宣邦出生于 1933年,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本科至博士),也曾留学德国,是日本近年最重要的思想史家,曾担任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作为学者,在五十岁前子安的业绩不多,影响也有限,甚至按时下汉字圈(香港、台湾、大陆)大学人文学科业绩评价机制,五十岁前的他可能在大学不会太愉快。但是,从五十岁起,随着他个人的思想史方法论形成,平均不到一年便有一本著作面世,而且,每一本都以其独特的视角,引起关注、讨论,甚至引起争论。这一势头随着六十岁左右他的方法论的成熟而持续,其著作质量及数量都保持着很高水平,直至八十一高龄,依然宝刀不老,可谓学界异数。就专业而言,子安的专业领域为江户时代的思想史,既然是江户思想,其主流自然是儒学,因为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上儒学风气最盛的时代。自四十岁左右起,子安先生的思想史研究开始延及近代日本,换言之,其研究对象便成为有着三百年视野的近现代日本思想史。子安的著作在汉字圈已有多种译本(出版单位以北京的三联书店为主)。
子安强调自己的“思想史家”身份,笔者也就有必要介绍其作为思想史家的方法论。假如说子安宣邦的思想史方法论与马克思(1818—1883)有间接的关联的话,那么,这种关联就体现在他的思想史中一贯的意识形态批判上,而这一“意识形态”,严格上说,指的是遍布的可视及不可视的话语背后的权力性。具体说,子安的思想史方法论,其实直接是受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批判史学,以及法国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批判社会学的影响。福柯的批判史学所植根的其中一个概念,是其内涵实为语言权力性的“话语”概念。福柯作为思想史方法概念的“话语”概念,糅合、重构了尼采(F. W. Nietzsche,1844—1900)的“权力”“意志”概念,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精神分析理论,福柯探讨话语背后的“权力性”“意志”或“意识形态”,并且视“世界”“历史”为语言的构筑物。这些语言被命名为“集存体系”(Archives,原意“档案”),福柯如此定义:“‘集存体系’首先是那些可能被说出来的东西的规律,是支配 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出现的体系。”而布尔迪厄的批判社会学其实与尼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着类似的问题关切。以布尔迪厄的名著《区隔:判断的社会批判》(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dgement)为例,他认为,每个人的趣味判断表面上看来是非常个人化的,但实际上都与我们所属的集团、阶级有着直接的关系。布尔迪厄试图揭示,这种 Distinction(区分化、差异化、分类化、等级化)是在将广义的文化等级化。布尔迪厄旨在研究社会中的“象征性权力”,这一象征权力包含看不见的权力,诸如“文化资本”“社会关系资本”“性向”“习惯行为”等。他研究这一类权力在构筑社会权力关系上的作用,认为社会权力无处不在。显然,布尔迪厄的社会性“权力”概念与注重语言性权力的福柯不无相通之处。子安之思想史把握,在笔者看来其实是置于这一意义上的新史学的影响之中的(假如将社会学视为广义的史学的一部分)。带着这样的新史学方法论,子安试图实践其于新史学领域中的阐释可能性。以此方法论,子安研究以江户儒学为主的江户思想,更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批判性地分析近代以来日本知识分子对江户思想的话语重构。通常来说,战后日本影响最大的思想史家、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1914—1996)部分毫无个性的追随者未必喜欢子安,因为子安的著作《作为事件的徂徕学》(1990年)曾致力于解构丸山真男政治理论中关于江户儒学(尤其关于荻生徂徕)的讨论,因为丸山真男被视为现代主义的象征性人物,而子安则致力于现代性批判。《作为事件的徂徕学》也可视为子安方法论确立的标志。但是,应该说,丸山应该仍是子安最为推崇的政治思想史家,在此意义上,他是丸山真男富批判性的追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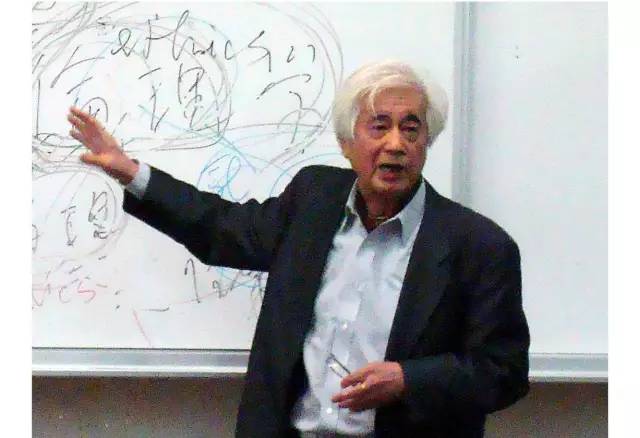
子安宣邦
说到这本《孔子的学问》,子安解读的方法论视角,似乎也多少可从如下《论语》的“有教无类”解读中窥见。子安先举出江户大阪商人、市民儒学团体怀德堂的儒者中井履轩(1732—1817)《论语逢原》为例:
在中井履轩这里,“教”的确被理解成“教育”的意思。人世间对善恶的区分,并非先天确定,而是由后天教育引发的。教育产生类别,而教育又能消除类别间的差异。不过,这里所说的教育,并非由人类平等的理念引申而出的“教育”。小人在集团内部施行不良的教育,自会产生不良的后继者;因此,所谓教育就有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教唆、教导的机能。正是这种机能后天性地决定了人及其团体的性格,也规定了其偏向性。按履轩的理解,孔子敦促我们注意的,正是教育的这一侧面:即它可能造就社会之中的优劣之分。
这里的孔子,不是认为人受教育便能独自成才,在此方面没有差别的平等主义教育家。毋宁说,他是一位卓越的人类社会观察者。因为他提醒人们注意,社会性存在的优劣差别的再生产,是社会集团内部的教育本身造成的。(后略)
《汉和大辞典》记载:“教”字的本义就是上行下效。“教育”一词原本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可以说,教育就是由权力阶层对下层民众进行驯化的支配行为。正如米歇尔 •福柯所言,教育始终含有调教(“规训”)的意思。其实,《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子路篇三十)宫崎市定将这句话译为:“把未曾接受训练的人民发派到战场上,犹如直接送他们去赴死一样。”所谓教育人民,就好比对人民施行军事训练。“教” 与 “教育” 原本含有这层意思。它是指自上而下施行的调教,是下层被迫为服务于上层而进行的一种他律性的学习过程。若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应该是一种与孔子学园水火不容的“教育”概念吧。因为孔子学园本身是一个自律的读书人的团体。自上而下施行的民众教育带上正面积极性意义,始于现代国家的国民教育,亦即使国民平等地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本书绪言)
通过追溯“有教无类”在江户、近现代日本的再解读,子安所体现的,是贯穿于其思想史中的现代性批判立场。在此,他借对《论语》解释史的梳理所要批判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特质之一的均质性是如何反映于近现代的教育制度的,而近现代的教育制度又是何如服务于这一均质性的。因为现代教育的一面,在于规训、训练国民,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相配套。但是,在子安看来,这一现代主义者角度的《论语》解读,在追求现代性理念之平等观的同时,却忽视了这一平等观其实遮蔽了教育本身的规训性。同时,这一平等观其实正是植根于扼杀个性的原子式的均质性之上的。子安上溯江户儒者的重读轨迹,认为“有教无类”恰恰表明了孔子锐利的批判性,也就是孔子洞察了教育本质在于“调教性训练”,此恰类于福柯的“规训”。按子安的解释,孔子的有教无类旨在指出教育这种机能“后天性地决定了人及其团体的性格,也规定了其偏向性”。这一解释背后无疑有着布尔迪厄批判社会学理论上的影响。按其解释,孔子正是一个伟大的先行者,他通过“教”与“学”的本质洞察,重新召唤被现代性压抑的“学”。就此,笔者想起的是,清末著名思想家、革命家章太炎(1869—1936)在其《齐物论释》(1910年)中,借其所解释的庄子而对这一现代均质性的平等观念进行批判:“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 ”章太炎质疑植根于所谓“公理”的平等观,质疑源自欧洲、实与扩张难脱干系的普遍性,而以不齐而齐为真正的普遍性。确实,这一平等观一方面扩大了受教育者的人数,也重视并且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发现,现代的教育制度旨在培养竞争能力与竞争精神。这一竞争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然后是由个人原子式构成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借用孔子的言辞略微夸张地说,我们的现代教育制度正是着眼于培养有着一定竞争力的“趋利者”,而非培养“仁义君子”。子安的《论语》解读偏于“学”,而质疑偏于“教”的现代以来的《论语》解释,试图借此重新呼唤“学”的本质,希冀重振“学”的主体性与尊严。
作为日本儒学史研究者,子安试图探寻多元的儒学形态,唯因此,他总是致力于对一元化(亦即被固定、被特权化)的儒学的解构,亦即批判体制化的儒学。此处所说的“体制化”可以是某种官方的、集团性意识形态的“儒学”,并借此批判而谋求儒学多元化的可能性。从上所述也不难发现,子安宣邦可谓是当今日本代表性的重振儒学批判性的思想史家。
本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子安也很注意与现代汉语圈学者《论语》解释的对话。子安并非中国研究者,在以西方(尤其法德大陆中心)为中心的现代日本人文学界,他这个年龄段的人文学者能阅读现代汉语的寥寥无几,他算是例外(文言文是日本中学的必修课)。钱穆(1895—1990)的《论语新读》(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也被频繁地提及。李泽厚可谓是影响了中国大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整整一个时代的最重要的思想史家及思想家,钱穆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中国学术史家及中国思想史家。三者的《论语》解读之间的对话关系以及其间的同异,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2014年7月

《孔子的学问:日本人如何读<论语>》
原作名: 思想史家が読む論語
作者: [日] 子安宣邦
译者: 吴燕 译 / 吴素兰 校 / 林少阳 导读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6-12-1
ISBN: 9787108054715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