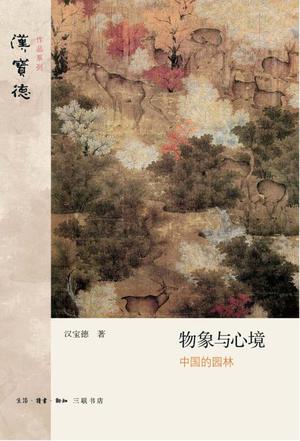 *摘自《物象与心境——中国的园林》 汉宝德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5月刊行 我国园林在近千年的历史中,发展得多彩多姿。有些不为后人注意的细微处,却有深刻的寓意。 明代以前的园林并不一定有水,古人就因环境的条件,对于水池之应用,采取相当弹性的态度。水池固然越大越好,有时他们也不得不欣赏很小的代用品,并琢磨出一些特殊的美学来。 池为心境 事实上,唐代的文人间确实发展出一种类似案上清洪的水池观,名曰“盆池”。我们可以想象对于一般文人,或中下级的官僚,在干燥的华北大地上,即使有园池建设的打算,也未必能达到目的,水在华北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有水池而保持池水常满是很不容易的,文人们要欣赏水景,有时候就不得不靠一点想象力了。 “盆池”是什么呢?在文献中可以看出,乃由于水源缺乏,只好在院子里埋下一个盆子,倾水其中,聊充水池。盆子是陶制的,比较不易渗水,明显的是为保存可贵的水源。唐人有一篇《盆池赋》,开始的几句,就说明了这一点: 达士无羁,居闲创奇,陶彼陷器,疏为曲池。……深浅随心,方圆任器。 虽然这里说盆池是“达士”独创的办法,其实在当时是相当流行的。诗人杜牧就曾有《盆池》一首,把盆池在庭园中的意境描写得十分动人: 凿破苍苔地,偷他一片天; 白云生镜里,明月落阶前。 这座盆子是埋在阶前的苔藓覆盖的土地上,水面平静如镜,常常反映出一片天光。白天可以看到白云,晚上可以看到明月。陶盆的形状,“方圆任器”,应该是几何形,因此盆池是相当有禅宗意味的。上引的《盆池赋》中有几句话,表达出一种深刻的禅境: 分玉甃之余润,写莲塘之远思。空庭欲曙,通宵之瑞露盈盘;幽径无风,一片之春冰在地。观夫影照高壁,光涵远虚,云鸟低临,误镜鸾之缥渺,庭槐俯映,连月桂之扶疏。是则涯涘非遥,漪澜酷似,沾濡才及于寸土,盈缩不过乎瓢水。 后文中,更发挥想象力,扇风可以起浪,浮芥叶可视同“解缆之舟,远同千里”,在意境上,在“影照高壁,光涵远虚”的格调上,与日本的枯山水与苔石庭,都很近似,尚觉高超些。“盈缩不过乎瓢水”,这水池泳涵着宇宙,却不过瓢水之盈亏而已,实是中国古人智者之心镜。 古文大家韩愈也很为盆池着迷,写了五首诗以歌颂之,第一首是说明其来源: 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作小池; 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如方口钓鱼时。 埋个盆子做成小池,晚上就有青蛙来鸣是不可能的。他老先生夸张得过分了。第三首描写池里的小动物,尚合情理: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虫无数不知名; 忽然分散无踪影,唯有鱼儿作队行。 最具有高超意境的还是第五首,与前引的文字有类似的玄思: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才添水数瓶; 且待夜深明月出,试来涵泳几多星。 这种自盆子里看“池光天影”的“池艺”,说明了唐人的情操,也说明了唐人对池的爱好。这盆子并不一定是陶瓦之盆,有时也可能是石盆。杜牧的作品中就有一首题为《石池》者: 通竹引泉脉,泓澄深石盆。 惊鱼翻藻叶,浴鸟上松根。 残月留山影,高风耗水痕。 谁家洗秋药,来往自开门。 石池的味道与陶盆不同。陶盆要远离树阴、花丛,以便完整地反映天光。石盆由于斫石不易,可能并不一定要埋在地下,而是有点园中道具一般的与树木花草形成一种雅致的组合。所以池上有竹引泉,池边有松,其根可供浴鸟振翼。这使我们想到日本式小园中的石臼样的小池。在园景中,残月的影子并不孤单。 这种玩具式的盆池到宋代渐不流行,与宋文化渐渐南移至多水地区有关。但在宋文中亦偶尔一见,大诗人陆游就有一首游戏之作: 小小盆池不畜鱼,题诗聊记破苔初; 未听两部鼓吹乐,且看一篇科斗书。 即使在南方,缺水的现象仍然发生,大诗人无池不能存活,学唐人弄只盆子充数。 既然可以接受以盆子为池的观念,我们推想唐宋的古人,靠文学的想象力,园池的规模小些,是可以接受的。唐代有园池狂的白居易,一天也不能看不到池子,而宦海浮沉,一生被流放多处,有时候免不了凑合些。他写过一首《官舍内新凿小池》诗,不但说明小池的做法,也表达了文人的感怀,与盆池是一贯的: 帘前开小池,盈盈水方积。 中底铺白沙,四隅甃青石。 勿言不深广,但是幽人适。 岂无大江外,波浪连天白。 未如床席间,方丈深盈尺。 清浅可狎弄,昏烦聊漱涤。 最爱晓暝时,一片秋天碧。 这是一座青石砌成的方池子,底铺白沙,在院子檐下不远处,白居易颇有童心,有时还玩玩水,顺便也洗洗脸、漱漱口,可以说是多用途的。大小方丈,深一尺,就很使他满意了。至于其景致呢?仍然无非是“泛滟微雨朝,泓澄明月夕”,无非是“最爱晓暝时,一片秋天碧”,爱其反映天光而已。 另有一首诗是一位名方干的诗人写的,题为《于秀才小池》,进一步证明了小池的普遍性。诗曰: 一泓潋滟复澄明,半日工夫劚小庭。 占地无过四五尺,浸天应入两三星。 鹢舟草际浮霜叶,渔火沙边驻水萤。 才见规模识方寸,知君立意在沧溟。 这位诗人在赞赏了小池的韵味之后,却自方寸的规模,度量小池主人的志向,是十分远大的。那就是以小池比心志了。 外来的影响 自以上唐代盆池、小池的诗文看,此种小型水池之使用,与六朝以来传统的园池观似有一种距离。它似乎不是用来表达自然,或模拟自然,而是当作一种心镜,不但是造型抽象,几近天然,用意也不在此,在精神上,颇富于宗教的情操,所以上文中曾认为它有禅园的意味。然而唐代以后,盆池为何逐渐消失了呢? 当然与南宋的重心移至多水地区有关。但是另有一个因素也不能忽略。那就是南宋以来,中国文化全面地回归于六朝崇尚自然的阴柔性格,逐渐放弃了唐人主观而阳刚的一面。 可是唐代何以会有这样的水池观呢?以我看来,乃受中东文化之影响。我们知道中东文化经由西域,与盛唐之长安有十分密切的接触。唐文化中融入波斯色彩的事实反映在精致文化的各方面。金银器、陶瓷器的造型,音乐歌舞,无不受中东直接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建筑并没有受到外来的影响,可是在庭园上可不可能受到影响呢? 很可能。唐代长安的外人很多,他们必然带来了一些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也许住中国的房子,但很可能带来中东的水池,那是自古罗马以来传播遍及地中海沿岸,并远及于波斯、伊斯兰教文化的庭院中的方形或圆形水池。在少雨的地中海地带,水是生命的泉源,是具有哲学意味的象征。水池在建筑中是一种装饰,也是一面镜子,它反射了四周的景物,是建筑的核心。在这种水池里,本是没有生物的,与树木花草无关。 我推想,这种使用水池的方法可能与波斯萨珊王朝的装饰纹样一样为中国人所借用,因为长安也是少雨的地区。它很快就中国化了,为中国文人的想象力所润饰。然而其基本的反映天光的虚幻精神却没有改变,为每一位文人所乐道。所以他们非常注意水面的平静、清洁,宁愿违背自然之理,只有到宋代,才开始容许生物之存在,如上文所引陆游的诗。 唐代有一位自号弘农子的,写了一篇《小池记》,记述他自建小池的故事。他的池在小园子的竹斋前,并不是盆池之类,周有三十步,四周还种了花木。在风起微澜,雨水充溢的时候,他感到“江湖之思满目”。最妙的是他不喜欢池面上有杂物,片叶寸梗都不能容忍,要僮仆们不停地清除。朋友们来访不免觉得这是过分的辛劳,并无价值。这样一个小水池,没有任何用处,费这些劳力做什么?这位弘农子则不以为然。池小就没有用吗?比起长河大川来,它固然无农渔舟楫之利,但也无这些活动带来的骚扰,最后他的结论是说: 故吾所以独洁此沼亦以镜其心也。将欲挠之而愈明,扬之而不波,决之而不流,俾吾终始对此而不渝…… 他竟把水池看作静态的镜子,比喻他的心性。 到了宋代,小池虽然偶然被使用,其意义则已大为改变。小池逐渐被视为小型的自然的水域,人并乐于看到因水池之存在,所招来的生物的活动。这才真正接近后期中国案头园林的观念。欧阳修有一首题为《小池》的诗是这样写的: 深院无人锁曲池,莓苔绕岸雨生衣; 绿萍合处蜻蜓立,红蓼开时蛱蝶飞。 院子是静悄悄的,但是池子却是一个充满了生命的戏剧的舞台。下过雨,苔藓就长满了水岸,蜻蜓与蝴蝶为绿萍与红蓼吸引而来。诗人静观的心态与唐代的“心镜”似乎并无不同,但是静观对象是自然的生态与生命的美感,不再是在虚幻的影子中找自己的存在了。 心园的经营 不论是唐人的盆池、小池,及宋代以后的小型自然园林,都属于静观艺术的范畴,在精神上是内省的,为供主人修身养性时观赏之用,与案上的清供,或琴棋书画等文人艺术并没有不同,这与通常对外开放的大型园林在意义上是完全不同的。 我发现唐人有这种盆池的观念时,不免有点惊讶,因为它与中国传统园林中的自然观大不相同。然而我亦自此感觉到中国传统的博大精深与兼容并蓄。它说明了中国的古人虽然在园景艺术上自始即有大众化的倾向,却同时也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抽象化,形成一种完全属于个人的,用来寄以玄思的艺术。 自唐人盆池的心镜的观念,使我想到,中国的园林原来就是一种心境的表现,与真正的自然有别,所以广义地看来,一切园景都是心镜。这种观念是抽象的、现代的,可以连结上现代生活环境的创造。然而在精神上又是传统的、内省的,重于心性修养的。这种精神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庭园艺术。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