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嫁给王蒙那一天起,认定和他同甘共苦 1979年春,王蒙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于是一通百通,我们的命运立即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我们返 回北京,王蒙被安排在北京市作协搞专业创作,从此,王蒙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他蒙受多年的不白之冤澄清了,他重新获得了写作权力。他在实践中找到了自己,他回来后分秒必争,因为他在前20年失去的太多太多,他想尽快寻回以往的损失。况且,一旦获得了自由,他那种强烈的写作欲望,那种蓄积多年极富生活根底的素材全都活了起来。面临时代大变革,他触景生情,八面开花,写作的热情汹涌澎湃。这个时期,他的小说像雨后春笋一样接二连三地问世,如《布礼》、《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太多太多了。 那么这个家呢?自然全靠我了,方方面面的事我都得管起来。其实未必我能管,很多事情都堆在那里“挂”在那里。我承认在家务事上我是低能,不是一个出色的家庭主妇,不会理财,不会精打细算,缺乏领导锅碗瓢勺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才能。我更不是一个修养到家的贤妻良母,我可以默默地做很多,只是听不进一点儿埋怨的话,我的忍耐度不算高,有时也会大发脾气。很多人称赞我是位贤内助,我受宠若惊,不敢当,因为明白自己并非如此。 我俩一起生活40年,从没认真谈论过“钱”字。在家里,我们的收入与支出属于放任自流。不管我俩谁的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谁用谁拿。钱多,手松些;钱少,手紧些;没钱,不用,就这么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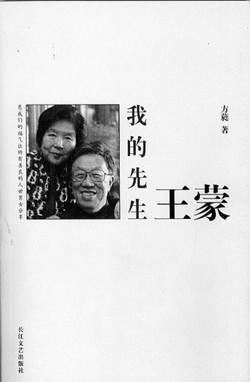 2000年底,《当代》杂志设了一个大奖,奖金10万元。这年王蒙在上面发表了长篇《狂欢的季节》,感觉可能会获奖。王蒙说,如果获奖,他希望捐献出来,扶持青年作者。他说:“得太多的奖,好事太多,占有太多,不好,不能心安理得,不如捐献出去……”我当即表示同意,10万块钱的用途,用了不到1分钟就确定下来。 2000年底,《当代》杂志设了一个大奖,奖金10万元。这年王蒙在上面发表了长篇《狂欢的季节》,感觉可能会获奖。王蒙说,如果获奖,他希望捐献出来,扶持青年作者。他说:“得太多的奖,好事太多,占有太多,不好,不能心安理得,不如捐献出去……”我当即表示同意,10万块钱的用途,用了不到1分钟就确定下来。
那次,王蒙得了奖,捐了出来,并正式设立了春天文学奖。他在会上说,现在衣食住行玩乐钱都够用,他愿意把奖金捐赠。参加会议的作家毕淑敏对王蒙说:“您的衣食住行我不知道,至于您所说的玩乐,我想最多是与崔老师下下跳棋而已……”王蒙说:“怎么毕淑敏如此了解咱们?确实,我们的玩乐不过是下跳棋,如果天天‘蹦迪’,再来10万也不够!” 为了这个家,为了王蒙能投入精力去写作,我做了许多“无意义”的事。我喜欢整洁,习惯随时随刻把东西放在一定的地方,希望有个整齐、卫生、美观的环境,使生活舒适,工作有条不紊。只是在我家,整洁保持不住两分钟,常常是边整理边被破坏。书籍本是我家的财富,也是惟一的财富,已经占满了十几个书柜,加上近几年来,各地的报刊出版物雪片似地飞来,在我家堆积成山、成灾。每天邮件一大摞,我一件一件地拆封之后,分门别类地放好,分清哪些是急需处理的,哪些是有保存价值的。我向王蒙交代之后,不多功夫再一看,总是大吃一惊:有用和没用的混在一起,报纸在地上、沙发上、茶几上支成一座座的小帐篷。只要是我交到他手里的东西,准丢,一来二去我也没脾气了。他写作起来,是有目不能视,有耳不能闻,一切都不管不顾,只要有一席立足之地,旁边再脏、再乱他都看不见。 王蒙不修边幅,时常衣帽不整。往往是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每次出门,我都要提醒他拔出别在鞋里的裤角。若是少说一句,他就这样参加活动去了。 约好了人来取稿件,或是有客人来时,我送水倒茶啊,迎来送往啊,这都没什么难的———当然也有照顾不周的时候,对于车水马龙的生活,对于不速之客,我有时候也实在是应接不暇。另外,我常为家中的混乱感到难为情,感到自己太无能。有时我想,家中有这么多“乱源”,就是有8个保姆也伺候不过来。 1979年我返回北京后,本可做更多的事情,或换一种我最喜欢做的工作,但是没有,我仍回中学,而且去了比较一般的七十二中教书。我拒绝接受教高中三年级的课程,那需要把关,我没那份精力。有时,正批改着作业,忽地想起家里还有一大堆事在等我做。第一次调工资时,不是全部人都可以调,我表现出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姿态,在小组会上,说了一堆废话,目的是谦让,不要给我调,让给别人。这样大大地减轻了校领导的困境,他们求之不得。这样做,当时在全校大概我是独一个,在北京市也是绝无仅有。这一次错过了,一错再错,在以后的调资过程里,我总比和我情况相同的人低三级。理应这样!谁让你谦让呢?你为什么不去争?凭良心而论,我并不是雷锋,但是我为王蒙多做一些,难道不是在为自己做吗? 1979年6月,我从新疆返回北京后,见到一些朋友,他们很自然地要问:怎么样?你们在新疆过得好吗?我会口若悬河地说一通在那儿生活如何如何丰富、有趣而且有意义。有一次,我的一位同学问我:“你到新疆,一去就是16年,怎么样,有什么收获?”我说:“收获可大了:第一,王蒙学会了维吾尔语;第二,深入了基层,和维吾尔农民打成一片,交了许多朋友,写作有了深厚的生活底子;第三,‘文革’期间我们处于少数民族地区,又是边陲,那里简直是一座避风港,在关键时刻,被善良的维吾尔农民保护起来了。如果在北京的话,王蒙恐怕要遭受更大的灾难……” 正说得起劲时,我的同学插话,唐突地问:“我问的是你,是你自己过得怎么样?” 蓦地,我哑言塞语,窘迫得无地自容。 像触电似的,我猛然想到:原来许多年来,我没有了我自己。岁月匆匆流逝,我呢?我被岁月吞食了,被岁月淹没了,被岁月消融了。 当然,流逝、消融的岁月,是有它的内容和价值的。常言道:一个成功男人的后面,会有一个后盾型的女人。尽管这句话我不太喜欢听,但事实上充当了这种角色。 王蒙总爱说:没有了我,就没有他。 可我呢?我在哪里呢?我在他的生活中,在他的梦中,在他的写作中,在他的一切活动领域中,在他多变的时空中…… 王蒙还说:如果没有了我,他简直是寸步难行。这话真是一点儿不假,没有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呢?稿纸满天飞,衣服不成套,袜子不成双,寄信找不着地址,打电话找不到号码,遇事瞎着急。 王蒙多次问我:“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白痴?”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我知道真是有许多人尊敬甚至于崇拜王蒙,可是对于我来说,王蒙永远是一个需要照顾和宽容得一塌糊涂的呆子。连他过马路的姿式我都觉得拙笨万分,几乎是瞪着眼向急驶而来的车辆走去。我不能想像,没有我的时候他能安全地穿过马路而不会滚到轮子下面。 而我自己倘若做些事情,却常常不会被承认。就拿1959年春季来说,那时我才参加工作不久,在一○九中工作,一次庆祝活动中,我代表教职工在大会上发言,获得一致好评。会下,好多人问我:“你的讲演稿真好。那当然了,你家有支笔杆子啊!”其实我的演讲与王蒙毫无关系。 公平地说,很久了,我已逐渐地失去了我自己———但这是我心甘情愿的选择。 (摘自《我的先生王蒙》,方蕤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我们是很平常的一对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