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查多·德·阿西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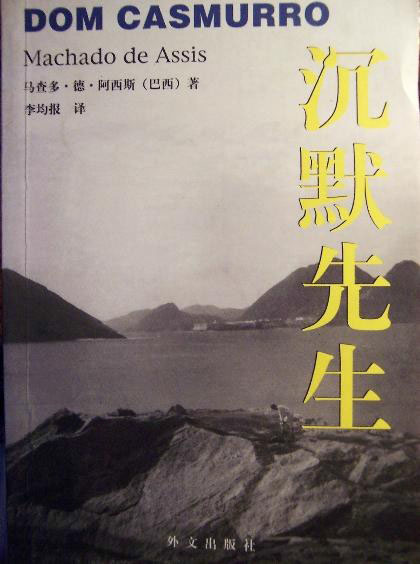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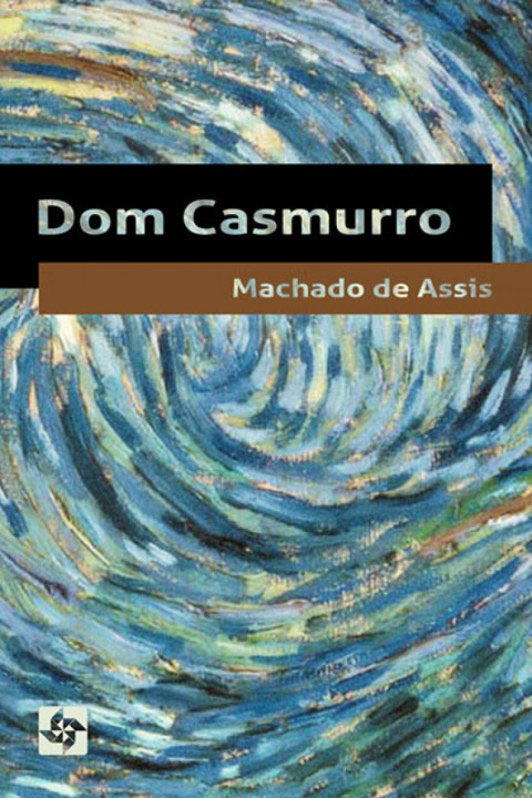
马查多·德·阿西斯是19世纪巴西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也是文坛公认的巴西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历程跨越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成为巴西文学过渡时期的重要见证。其70年代作品,如《复苏》《子夜故事集》《手和手套》《埃莱娜》等仍以讲述传奇性和感伤性的爱情故事为主要内容,遵循着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1881年,长篇小说《布拉斯·库巴斯德死后回忆》的出版标志着马查多思想观念的重大转折,他否定了浪漫主义对社会现象所秉持的盲目赞同态度,转而开始了对社会的揭露与批判。《沉默先生》出版于1899年,是马查多从浪漫主义文学向现实主义文学的转型之作,其中既延续了前期批判资产阶级伪善的现实主义传统,又通过对心理分析这一艺术手法的出色运用,开创了巴西小说中心理分析的先河。通过对人物精神的洞悉和对叙事手法的把握,马查多彻底摆脱了前期浪漫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创作出看似无比真实却又充满谎言与欺骗的故事。
《沉默先生》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通过“我”即主人公本托的视角,将一切信息传递给读者。本托别名唐·卡斯穆罗,意为“沉默先生”。他是一个沉迷于自身的非典型男人形象:性格矛盾、谨小慎微、平庸无能,没有真实的观念,也不能传达准确的观念。在本质上,本托是一个无法获得读者信任的叙述者,他无法真实地叙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人与事,他所记录的一切都是经过主观加工甚至是臆造的事情。《沉默先生》的核心情节正是围绕本托的疑心展开的,即他对妻子的怀疑,其理由是妻子卡皮杜生下一子,孩子长得很像好友艾斯科巴尔。本托于是怀疑好友与卡皮杜关系暧昧。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分裂,卡皮杜带着孩子出走欧洲,客死他乡;儿子也在一次旅行中身亡;本托孤身一人度过凄凉的晚年,写下了该书作为对自己一生经历,特别是感情经历的回忆。
叙述者的不可信,对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的卡皮杜构成了巨大障碍。但尽管第一人称男性视角的叙述声音有碍于女性以女性身份发出自己的声音,却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女性形成文本的叙述权威。阿西斯在采用本托视角叙事的同时,巧妙的将卡皮杜的行为和独特的女性思想意识渗透进小说,建立起属于女性的文本叙述权威。因此,虽然小说采用了男性叙述视角,拉开了读者与卡皮杜的距离,但是却运用内视角的方法,让读者深入到卡皮杜的内心,由此引发了读者对卡皮杜的理解与同情——最终我们不但不会谴责女主人公,反而确认了人物行为的合理性。
在这个意义上,故事真相并不在叙述者的话语之中,而是在卡皮杜的言行之中,通过这种处理方式,阿西斯将阐释真相的权利交还到了读者手中。卡皮杜以极强的行动力和智性上的优势超越了弱势的叙述者本身,取得了全书的话语权,为自己做出了隐形的“辩护”。从少女时期开始,卡皮杜就是一个僭越与反叛的女性形象,她从多个方面僭越了19世纪男权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并为自己争取到一定社会地位。然而她的僭越只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体现,并不在情节上指向一种出轨的必然。相反,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卡皮杜性僭越进行影射和指责,本托完成了男权社会对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报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9世纪巴西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理念依然是维护性别秩序的话语体系。
卡皮杜的一生极富传奇与反叛色彩。在少女时代她就已经体现出了智性上的过人之处和极强的自我意识。除了先天就拥有智性上的优势,后天接受的教育和知识也是卡皮杜日后的反叛与僭越的深层原因。主观上的理性和自我实现的意识促使卡皮杜积极追求内在的提升,同时,客观的原因更迫使卡皮杜不可避免地僭越传统的伦理规范,努力跳出自己的社会阶层。作为普通家庭的女性,卡皮杜的生活境况并不乐观,而本托则是处在中上层阶级,拥有可观的家产。这种阶级身份的巨大差异也构成了阻碍她和本托相结合的一个障碍。少女时期的卡皮杜就已认识到了自己的处境,萌发了要改变自身经济地位的渴望。但在19世纪的巴西,现实的物质世界把婚姻变成了女人的竞技场,输掉了婚姻就输掉了整个人生。除此之外,经济个人主义的盛行,改变了既有的婚姻模式,使得出来谋生的女性的婚姻问题日益面临危机。她们的未来越来越取决于能否有桩好姻缘,而她们能否找到好丈夫也愈发艰难了。卡皮杜的家庭条件预示着她无法获得可观的嫁妆,自我生存和自我欲望的实现使卡皮杜不可避免地僭越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宗教规范。
客观的外部环境只是促使卡皮杜僭越的一个原因,她本性中的理智、独立、利己也是重要原因。卡皮杜的僭越是女性自我意识和父权制体系碰撞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卡皮杜的僭越是心理上和行动上的双重僭越,她不仅在精神上成为本托不可或缺的情感依靠和人生导师,更在现实中不遗余力地为本托出谋划策,并在某种意义上推动着本托,这个缺乏谋略与行动力的男性成长。本托的弱势男性形象为卡皮杜超越父权体系提供了绝佳的出口。无论是出于爱情还是利益权衡,卡皮杜与本托之间的关系势必是不平衡的,卡皮杜将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在心理上处在一种永恒的僭越之中。
卡皮杜内在强大的女性特质更体现在她应对现实事务的能力上。卡皮杜善于察言观色,深谙人情世故,展现出惊人的行动力和内驱力。她在应对问题时的能力同本托的懦弱无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托在为卡皮杜梳头时被卡皮杜的母亲撞到,但卡皮杜“一边摇头,一边笑,没有丝毫惊慌,没有点滴的羞涩,笑得自然,笑得爽朗”,巧妙的化解了尴尬:“就这样我们被她母亲抓住。我们也变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人。她用语言遮掩,我则用沉默亮出。”卡皮杜过分的成熟催化了本托的成长,她开启了本托作为男人的自我认知。在同卡皮杜接吻之后,本托不断地重复:“我是个男人啦”。由此,卡皮杜彻底瓦解了本托的男性权威。波伏娃指出成长中的女人的两难处境:“她摇摆在渴望与厌恶、希望与恐惧之间,仍在童年的独立时刻和女性的顺从时刻悬而未决。”而卡皮杜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自己的处境做出反应,她“也能在她‘小母亲’的处境中汲取一种权威感,这种感觉引导她反抗男性的枷锁:她准备建立一种母权制,而不是变成肉欲的对象和女仆”。
正迈入现代社会的巴西普遍存在的婚姻危机促使卡皮杜千方百计找个好归属,对她而言,爱情并不是婚姻的必须,但婚姻却是女性谋得生存空间的必要条件。当本托在前往神学院试图对她立下婚姻誓言时,她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应,而是模糊地对本托说他们两人应当各自结婚。这种对婚恋的态度僭越了传统婚姻道德观,体现出卡皮杜的精明和一贯的利己主义态度。
尽管如此,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理念依然是维护性别秩序的话语体系,女性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实质性改变,长期的不平等关系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压抑终于使本托与卡皮杜的婚姻生活发生了质变。
卡皮杜聪明、敏锐,决定自己的信念和人生,追寻着自我设定的实现。她仅仅在心理上和行动上形成了对传统男权话语体系的僭越,而在行为上还是符合既有道德规范的。而在男性思维中,逻辑往往是暴力,是一种狡黠的压迫形式,这也是本托对抗卡皮杜的僭越性所带来的不安的一种方式。通过臆造和指责卡皮杜的性僭越,本托完成了对卡皮杜自我追求的否定,这也使他的人生如同奥赛罗一般真正地走向悲剧。
《沉默先生》中表现的女性僭越充分体现了巴西现代社会之初的社会文化发展情况,描写了卡皮杜作为一个新女性对自我实现和个人解放的渴求。卡皮杜试图通过僭越找到出路,打破传统束缚并且挑战19世纪女性生活模式。而本托却并不纵容妻子追求自我:父权制话语体系与女性个体的意识形态在当时的社会是不相容的,卡皮杜打破了既定的社会契约,她的思想和行为无声地僭越了夫权制社会的规范。这个家庭悲剧预示着19世纪的男性需要适应女性觉醒的新局面,并召唤读者深入思考悲剧发生的根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