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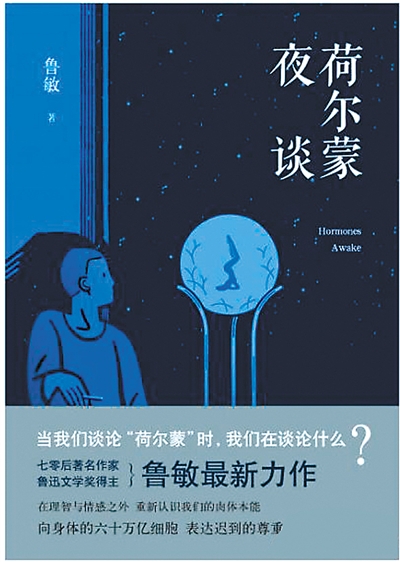
鲁敏的短篇小说有点像鲁迅所言的“揭疮疤”,似乎都是指向人之“暗疾”,正如之前的《九种忧伤》暴露当代人的种种精神隐患一样,这本《荷尔蒙夜谈》对准“身体的六十亿万细胞”,将欲望的强大、不可控以及现实的残酷结合于一体,我们看到欲望的满足与幻灭后的危机同步而来。尽管鲁敏貌似在写“荷尔蒙”,但某种程度上指向的是欲望的认知、精神的困境以及对存在的勘探。“荷尔蒙”是鲁敏的取景器,也是推动小说叙事的重要手段。在这个过程中,鲁敏道出了牧歌只存在于“追忆”之中的感慨,在人的欲望沉沦于“失乐园”之前。
鲁敏在开篇《大宴》中是写“宴”,所谓食色性也,正如孔子在《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大宴”即是“大欲”,只是鲁敏以极具讽刺的方式,将这种大欲建立于一种虚妄的想象之上,其荒诞令人想起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个或许可以改变命运的“荣哥”泯然众人之中,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荣哥,有的只是幻想中的权力欲望图景。当杨早最终逃离大宴现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荒诞背后无尽的悲凉,一种精神上的绝望之感。这种绝望是现实与精神的双重失重,作为小说家的鲁敏直面这种失重危机。《徐记鸭往事》貌似写通奸与复仇,写暴力,其实讨论的是一个处于精神困境、极度自卑的人,一旦获得了欲望无限满足的机会,他处理欲望的方式问题。在精巧的叙事中,鲁敏把人物的性格与存在的思考一并推向深入。
鲁敏其实重复表明了一种颠扑不破的东西,即欲望的客观存在,一种庸常却也是最为根本的事实,属于人类生活的常态,而鲁敏所要做的正在于揭示这种常态之下的非常状态,打破某种平庸化局限,并且告诉我们其必然性非但有着“欲”的根由,亦有“理”的根据。《荷尔蒙夜谈》中的人性皆是开放的,突破了日常状态下的扭捏与封闭,而这一切只源于现实的空虚与乏味。正如雕塑家何东城的所作所为正应了弗洛伊德所言,“艺术是被压抑的欲望的满足与升华”。在这个大背景下,虽然促成这场夜谈的叶羽将何东城作为欲望对象,以满足当年被拒绝的失望,但是一旦被其丈夫撞破二人之间的“秘密”,满足了自己的虚荣,何东城立刻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这是欲望的悖论,也是人性的真相。其实,一切高明的作家都在从寻常与非常之中,寻找人的生命存在与自我认知的奥秘。《三人两足》中的“章涵”与“邱先生”,犹似《万有引力》中的“小姐姐”与“杨局长”,畸恋与受虐的背后其实是利益的交易,也是人性的困境——那是“万有引力”的源头。
如果说,“荷尔蒙”是真实影响人类生活和生存境遇的客观依据,那么鲁敏在这本书中想要做的,还在于发现那一层虚妄之感,所谓“以小说之虚妄抵抗生活之虚妄”,以此来反思人的真实处境,达到“疾虚妄”的目的。柳云也可以说是《拥抱》中那个与老同学自闭症儿子约会的“她”之翻版,年龄所造成的伤痕,并未在青春的肉体上得到愈合,她非但没有占有年轻,而是更加印证了自己的衰老。因为拥抱过后,时间的鸿沟还在那里,处境只会更加孤独。
也即是说,鲁敏貌似在写“荷尔蒙”,“荷尔蒙”的凸显正是因为精神的失语。《西天寺》与《幼齿摇落》都写到清明节,这一纪念亡者的具有悲伤意味的节日,而符马一家行为似乎将之变为向亡者索取精神安慰的日子。符马讨厌家人的种种言行,而又觉得一切殊途同归,人生如此无聊,于是他选择在清明节约“那个女孩”,获取彼此的存在感。此时,荷尔蒙是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与唯一途径,而它指向的其实是其背后的深层焦虑。而在《幼齿摇落》中,与其说我们看到生之热烈,不如说看到爱之荒芜,那一包“幼齿”似乎是打破人生某种必然性的钥匙,当幼齿真正摇落之后,人生才有新的出路。
鲁敏在“荷尔蒙”的虚妄中,以反讽的方式揭示人在抓住欲望这类“贴身的东西”时候,精神性的缩减,爱情缩减为性,精神价值缩减为实用价值,这是人在从生到死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的同时,亦因时间的磨损变得面目全非的悲剧事实。然而正是因为欲望与虚妄的存在,才使得小说中人性的光芒更为耀眼,才使得肉体与灵魂有了碰撞的激情,就像那一包“幼齿”,它是一个平衡点,也是寻求生命意义的新的起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