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 平
主持人语
同样是“手艺人”,小说家对小说家的发现可能比作为旁观者的批评家更为敏感和及物。同行相轻,同行也可能知己般的惺惺相惜。小说家弋舟对小说家黄孝阳在当下文学中“稀缺性”的发现和尊重,其意义不只在于让我们去关注一个可能被批评家轻忽的优秀小说家。事实上,黄孝阳在当下文学中的“独异性”确实没有被我们充分辨识出来;同样重要的是,一种同行之间切磋的将心比心的文学批评也有待我们进一步开发。
几年前,《钟山》杂志有一个没有进行下去的作家写作家的栏目就叫“将心比心”。这种“将心比心”可以发生在同时代、同一个年龄代际、同一种文学趣味之间,也可以是跨越时间、空间、代际和文学趣味等等的基于作品的会心。我们期望有更多的小说家和诗人参与到讨论中来。另外,弋舟提出的文学形式的“整体性”把握也是一个有价值的观点。文学的外部和内部研究有一种浑然的微妙平衡,而所谓的“文学本体”也应该是浑然着的。

弋 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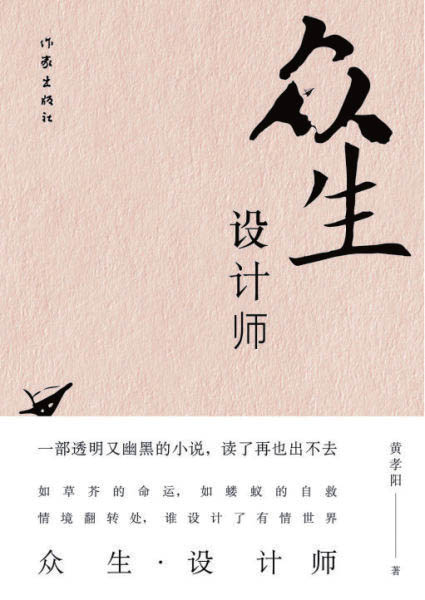
黄孝阳的《众生设计师》写出了某种物理性的、浩瀚的美。它迥异于当下小说的整体风格,在结构上有一种值得敬佩的、于今我们的小说家普遍缺乏的“设计”的耐心与能力。作品所焕发的,是“形式感”自有的美,有如一次精密的零件组装或繁复的拼图游戏,本身就弥散着“智性”那特殊的魅力。
这是一个考验或者一个游戏,承诺不再让小说披上那一贯“真实”的外衣来横行霸道。于是,传统小说那种不容分说的特权在此瓦解,一种全新的读写关系随之确立。
数年前,黄孝阳提出“量子文学观”,认为这是“当代小说的路径之一”。他热衷于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最新猜想,力图将之转化为新的小说叙事美学。“对小说的结构而言,我们要懂得整体与部分,核与衍散,黄金分割率。”这是他的自我阐释。如果说“黄金分割率”我大致还知道是个什么东西,那么,面对“核”“衍散”这些散发着金属光环一般的词语,我就只能望文生义了。
黄孝阳对于现实的敏感度,恐怕要超出绝大多数同行。只是,“现实”在他这里,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的意义,而是基于人类发展于今的更为深刻与本质的事实,他判定“只能说作家的经验与知识储备跟不上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一个开启新的千年文学备忘录的今天”。在这里,黄孝阳所说的“社会结构”,同样不是那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所指,它更接近于一个科技术语,几乎是一个数理公式,里面有艰深的换算与推演,并且足以导致出人类新的思维方式。
简言之,小说家黄孝阳要以“跟得上时代的经验与知识储备”,从形式上,拓宽我们的写作路径。对此,我一直心存怀疑。一则,文学究竟是以创作为前提,作品无力,观念悍然,总归是难以令人信服;二来,“量子”之说于我太过玄奥,没有一个深入的探讨和领教,我也不敢贸然鼓掌——文理之间壁垒森严,以方程式来写小说,那该有多难?我期待黄孝阳能够对自己的文学主张来一次有效的证明。现在,我看到了这部《众生设计师》。
一种全新的读写关系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尚不足十万字。相对于那个惊人的“量子文学观”,它似乎显得单薄了一些,但黄孝阳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篇幅里,竟然真的写出了某种物理性的、浩瀚的美。这得益于他的叙述试验:他将“数理性”融入了文学创作。小说中既有科学性的细节,也有科学性的议论,但整体上却并非一部科幻小说,而是以科学理念抑或“科技手段”来探寻别样的书写方式。它迥异于我们当下小说的整体风格,在结构上有一种值得敬佩的、于今我们的小说家普遍缺乏的“设计”的耐心与能力。作品所焕发的是“形式感”自有的美,有如一次精密的零件组装或繁复的拼图游戏,本身就弥散着“智性”那特殊的魅力。
黄孝阳以一场自杀开始写起,这个场景足足写了有30页左右,它没有我们习惯的那种节奏感,基本上罔顾我们根深蒂固的阅读习性。小说分为两部分,可以独自成篇,亦有草蛇灰线相互勾连。主人公各有不同却又彼此镜像般的投射与消解,你便是他,他便是你。视角转换得令人眼花缭乱,不断推翻着你刚刚稳定下来的阅读秩序。这种技法原来也非独出机杼,博尔赫斯不就这么干过吗?但这部小说更具“机械性”和“即时感”,博尔赫斯的杰作则富有“文学性”——“机械性”和“即时感”让它具有了某种“玩具”般的亲和力,同时少了些“文学性”那种对于人的排斥和拒绝。
小说写得天马行空,却难得地并不晦涩难读。它没有一个井然有序的脉络,但又并非一盘散沙。一个精致的架构在背后将其框定,小说家左右着局面,一切都在他“设计”的掌控之下。但这一次,他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你现在阅读着的只是一部虚构作品,它是假的,顶多是“仿真”的。它毫无诱骗你“信以为真”的野心,由此,反而成就了它绝对的真诚。这种“真诚”,给阅读构成了一种说明书般的可信度,它因为不再招摇小说长久以来高举着的那面“真实”的大旗,反而令人得以自主地徜徉在阅读的空间里。此时,读者参与了作品,小说家提供的答案不再是无可动摇的了,甚至,他还会时常跳出来与你共商小说的走向,他允许你质疑和辩驳,怂恿你另做他解。这当然是对读者智力的考验,但在这考验的背面,有一份“平等契约”悄然签订——它已经告知你:这是一个考验或者一个游戏,承诺不再让小说披上那一贯“真实”的外衣来横行霸道。于是,传统小说那种不容分说的特权在此瓦解,一种全新的读写关系随之确立。
稀缺的“烧脑”写作
这样的作品很难以那种耳熟能详的话语来进行“社会学意义”的分析,甚至,我都无从以一个“故事梗概”的套路来将其复述一遍。但是,它也并非没有一个那样的“社会学意义”和“故事梗概”。实际上,作为小说的基础材料,这部长篇比比皆是我们的曾经与我们的当下,某种程度上还有着过度的、面对那个“意义”发言的热情——小说中不断冒出长篇大论,对我们当下的经济、文化乃至人类科学的既有成就与未来命运喋喋不休地加以议论。这些与情节几无关系的文字,极大地挤占了本就不长的篇幅,使得小说阅读那种对于“故事性”的、约定俗成的依赖不断地受到干扰和冒犯。这或许是黄孝阳有太多的“社会性”见地想要表达,乃至忘记了必要的节制?但我宁可相信,如此地铺陈与拼贴,更是小说家从文本出发,以自己的写作诉求为旨归,刻意而为的结果。
一部小说由多种文本要素共同搭建而成,将语言、形式、结构、意蕴等统摄于一处,才是作品最终呈现的面目。单独将哪一个条件拎出来考量,都不足以成为最终的评判标准。而且,我也怀疑,是否真的能够这么拆解小说。小说艺术要求的是一个“综合分”,大多数成功的作品往往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和去掉一个最低分”后平均得分的结果,乃至它的每一处缺陷和每一个亮点,卯榫在一个整体之中后,都不再显得违和与夺目。这种对于“整体性”的要求,使得小说家理应具备一种“设计师”的自觉,他要为心中那份最终的蓝图负责。诚如书名所示,这一次,作为小说家的黄孝阳自觉扮演起了“设计师”的角色。文本中每一处“违规”的细部,综合起来考量,都成为了他精心打磨的零件,他非但自己设计着小说,也让小说中的人物设计着他们自己——他们写作、编程,用古老与先进的手段百般抵御着命运的碾压,对抗着物理世界牢笼般的铁律。夹叙夹议,不惮跳出来扮演深奥学说的阐释者,非常时期的国人命运与当下年轻人“小清新”恋爱故事的互文……凡此种种,都使得整部作品想象力澎湃,独具了一种杂糅的力量。
世界范围内与这部小说写作“原理”相近的作品恐怕不在少数,尤其是在影视作品中,像《盗梦空间》这种类型的电影已并不鲜见。但《众生设计师》这种令人“脑洞大开”的小说形式,在我们当下的文学语境中依然稀缺。我们的小说家懒于如此“烧脑”,或者干脆在智力与知识储备上难当此任;我们的批评家似乎也在强力抑制着作家们试验的企图——这种依仗“形式感”发起的写作尝试,也许同样挑战着那熟能生巧的批评之笔。
作家的“工匠精神”
当我们在文学中面向“意义”,“求真”或可被假定为神圣的终极目标,而这朝圣之路,却应当被允许途径“虚假”的“设计”。小说家之于设计师的例子不胜枚举,《红楼梦》不就是一部复杂精微的设计之书吗?贾雨村,甄士隐,连人名都敢于如此明喻!那么,当我们长久地、五体投地地服膺于小说“求真”的伦理之余,是否也可以、并且有理由心怀某种不那么忠实于“现实”、毋宁主观而骄傲地去“设计”的勇气?小说为什么不能够写得更“假”一些、更富有“设计感”一些呢?这即便算不得是康庄大道,在文学的地图上,也有权利被竖起路标,成为那些一意孤行者合法的羊肠小径。
美国作家唐娜·塔特认为雕琢句子是写作带给人的最深层次的满足。有人专注于词语的锤炼,有人专注于结构的玄想,本质上,小说家们的工作伦理是一致的,都颇具“设计师”的“工匠精神”。当作品完成,那“意义”之光将其整体笼罩之时,作为一名小说工匠,大约也渴望观赏者的目光多流连一些那“设计”而成的本体吧?这是对劳作者最体贴的尊重与理解;况且,漠视本体,那道投射其上的“意义”之光也将无从赋形。
黄孝阳以“量子文学观”为蹊径,至少说明作为小说家的他克服了写作的惰性,力图积极地处理一个小说家在今天所面对的经验,以新的艺术方式去回应生命全新的感受。而且,当他在这部小说中强力追求着“形式感”的时候,奇特的效果亦随之叠现——诸般“意义”不请自来,冰冷的“设计”宛如工业钢管,而流泻其上的却是怆然而又温暖的“意义”之光。
在小说的结尾,黄孝阳如此写道:“我叫元庆,十八岁,我生下来是一个中国人,便永远是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在遥远的将来,你们会听到许多关于我的故事,就像一群渴了很久的人,听见水的消息。”谁能够再将“意义”与“形式”从这样的句子中强硬拆分、断然切割为两个互不相干的价值?它是语言之美,是情感,是“设计”,是对“中国故事”的有力书写,也是对于小说艺术本身的致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