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我们都是一群时代的弃儿,但是我们却是一群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无论我们多么迷惘,多么痛苦,多么孤独,但是我们心中依然会让自己亮起一束光,我们就是那个寻找光亮的人。
在某个不入流的电影学院,滑稽可笑的学生吴正大对电影圈的一位“女神”痴痴迷恋。他舍友、整日沉浸在哲学世界的岳超峰,在某一天突然冷冷冒出了一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词语携带了一种奇异的力量击中了吴正大……
这是王斌的新小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要讲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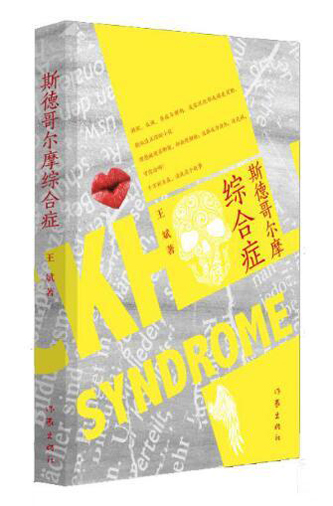
王斌曾是张艺谋御用编剧,两人并肩迈进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曾合作《活着》、《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英雄》、等十多部等国人耳熟能详的电影。十六年后的2006年,王斌选择退出,留在自己的小书斋。他上午写作,中午去附近吃写字楼里的职工食堂,下午继续阅读或写作。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十年。节衣缩食,精神丰盛。
他的朋友曾经评价十年前的他:“瘦削、尖刻——从内到外都见棱见角。他几乎是盗版的鲁迅……好斗、一触即跳、一个都不宽恕”。
十年之后的王斌仍是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但眼神温和,会拿自己的高鼻子说笑。虽然也常常有惊人之语。
他会在微信朋友圈发大段的文字,关于文学,或者电影。虽是发在友圈,更像是自己对自己发问。
“点赞很多,对话者很少,几乎没有。”他说。

“现在电影业真的是太堕落了”
腾讯文化:怎么想到写这么一部荒诞不经的小说?
王斌:在这个之前,我原计划将我的小说《遇》拍成电影,后来资金出现了问题,剧组就停下来了。这时我突然发现有两年没写小说了,我必须写一部小说,写什么呢?
我想到一个名字,叫“圈套”,但是这个《圈套》里面是个什么圈套?一时还不知道,只是围绕着“圈套”二字形成了一种隐约的感觉。我写小说从不事先构思,只是一种感觉在萦绕和诱惑着我,但有趣的是,我的一个在美国当大学教授的哥们儿,看了我的《遇》及《六六年》后,告我说你肯定写前会在墙上画了一个详细的人物关系表,及情节走向,所以才会让小说显得严丝合缝。我说我写前完全没有构思,所有人物都是自己跑出来的,以致常会让我感到惊异。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起头时,我先试着写我的一位好哥们儿,画家李向阳,我给此兄起名叫向阳斯基。为什么叫向阳斯基呢?因为他是画抽象画的,抽象画的鼻祖乃康定斯基,所以我就戏称他为向阳斯基了。这个人特别滑稽,完全不懂生活,说的话都是从书本里来的,永远是一堆抽象的概念,我想把他拿出来进行戏谑和嘲弄,然后把现代社会中的一些点点滴滴的感觉通过他展现进来。
那天,一口气写了几千多字了,然后我习惯性的停下不写了,因为到饭点了。我写小说一般是上午写,而且只写二个半小时左右。第二天我又来到电脑前,先例行性的扫了一遍昨天写下的文字,忽然觉得不对了。然后另起头。这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开头,写了几万字后,突然有一天觉得一个灵感蹭一下把我照亮了,这不就是在写人性固置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吗?今天的年轻人,今天的文化,不就是被这些东西绑架了吗,包括我们的政治运动、当下的体制。我的写作就这样突然就它彻底照亮了,从那一刻起,思路变得异常清晰。
腾讯文化:吴正大和艾咪咪“肉搏”的那一场,也是吴正大以艾咪咪为对象实施他的“斯德哥尔摩症”的一个段落。艾咪咪屈服之后,吴正大得意地称之为“伟大不朽的爱情”。您是想表达什么?
王斌: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那个真实的事件里,银行的劫匪一方面残忍地绑架了人质,但另一方面也同时给予了人质于温暖,这就令人质感激涕零了,并且爱上劫匪。
我把情境和事件做了一次现代性的转换,转化一种普遍存在的人性中的某种情结,小说里吴正大的这句台词,仅是为了让这个人物显得滑稽、怪诞,增加我对这种情结的讽刺效果。
腾讯文化:您从事电影十多年,这部小说是对电影圈现实的一种荒诞表述吗?
王斌:一开始我只是想拿李向阳开个小玩笑,没想到会扯上电影圈,当时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写些什么。如同我前面说过的,起完小说开头的第二天早上,我在电脑前一坐,直觉告诉我它有问题,于是仿佛顺理成章地写了一帮不着四六想要混电影圈的人。
现在电影业真的是太堕落了,他们几近在摧毁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的品质和价值,这太可怕了,我深恶痛绝。但今天的小说,如果仍用犀利的,批判的,板着面孔的方式来写,可能会有问题,因为今天的年轻读者,不喜欢听你在说教,当你用这种嘲讽的、荒诞的,夸张的,乃至幽默的方式书写,会让他们在享受阅读快感的同时,为自己被点醒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感到汗颜与羞耻,由此引发必要的警觉,这是我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
腾讯文化:如果开始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思,中间是否会有一些偶然的情节跳进来打断你?
王斌:始终存在,没有事先的构思就是为了让偶然的即时的事件自然而然的浮现,因为过去编电影剧本是必须有一个事先构思的,所以我有意识地回避了这类写作方式,其目的,就是为了为偶然与即时留下足够的空间,我的所有小说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完成的,而且很少在过程中突然卡壳。写这部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里那种荒诞和夸张、反讽,黑色幽默是对我是有启发的,但我发现作为小说,它有严重的问题,就是它的人物、情节、性格逻辑都不对。所以我告诉自己,必须让我小说的每一个人物那怕行为再夸张,也必须处在他的性格逻辑、心理逻辑和事件逻辑里,这样才能增加读者的认同感。
所以在写的过程中,我经常会为自己的神来之笔而感到惊讶,甚至写到酣暢淋漓的地方我会哑然失笑,比如吴正大应聘时把他的女老板在办公室里给办了,秘书在外面打电话给她男朋友,那就是神来之笔。写时我哈哈大笑,一边大笑,一边想,未来我的读者一定会认为王斌这个人太坏了,没有这么损人的。
“岳超峰就是我的化身,耿直、不妥协”
腾讯文化:岳超峰身上携带的那种信念,给人很强烈的感受。那也是在写您自己?
王斌:对,写的是我自己内心的一种东西。我们都是一群时代的弃儿,但是我们却是一群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无论我们多么迷惘,多么痛苦,多么孤独,但是我们心中依然会让自己亮起一束光,我们就是那个寻找光亮的人。
今天是个逆淘汰的时代,那些理想主义者、正直的人,诚实的人被这个时代淘汰出去了,文化圈尤其明显,而一些投机的混蛋,那些蠢货们,在这个时代价值沦落的时代却成了所谓的成功者。
最后的结尾部分,岳超峰和他的女上司张秋雯的告别,写时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了一种涌上心头的难过,写了半个小时后,我觉得写不下去了,不是思路断了,而是感到了无以言表的难言的悲怆,突然感到一种沉重的苍凉感,是这种感觉就让我没办法再往下写了。我离开电脑,一个人去了客厅,抽着烟,看着窗外在远方隐隐浮现的连绵起伏的西山,它笼在一层淡淡的薄雾中,我又下楼起了一圈,让自己平静下来。我知道今天我不能写了,因为接下来我还要转化到吴正大所代表的另一类型的荒诞感的情绪中去,但我现在还转换不过去。
腾讯文化:张秋雯这个人物,您对她也有很深的认同感?
王斌:是我。在我看来,她曾经是一个被这个时代裹胁下已经处在休眠状态的人,浑浑噩噩,理想的火种在她心里几乎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岳超峰的到来,把她又点燃了。她最后在酒吧里把岳超峰找去,她喝的有点醉醺醺的,有个小男孩想泡她。我突然觉得我对这个女人有一种特别的爱,不是男女之间的爱,就是爱这个人物,在她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善解人意、干练、豁达,以及理想的情怀,甚至为了岳超峰赌上自己的职业生命,这都让我非常感慨,哥德的诗中有这么一句吟咏: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向上。
腾讯文化:您怎么看理想和情怀在当下处于被嘲笑境地的现实?
王斌:一定会遭到嘲笑,因为金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唯一价值,理想在很多人的心中就沦落了,甚至泯灭。“坚守”这两个字说起来很轻松,但你会有很多损失,比如舒适生活跟你就没关系了。至今为止,什么饭局,吃吃喝喝基本上与我无缘,我也不会感到后悔,我最关心的是:我的文字是不是好,是不是辜负了我的心灵?我的表达方式是不是好,是不是直击了时代?其他生活方式对我来说,真的没那么重要了。
腾讯文化:为什么没让岳超峰和张秋雯之间产生一点爱情?
王斌:我想过这个问题。小说的批判主题严格说是由吴正大来承担的,岳超峰承载着副主题,他的出现,是为了反衬出吴正大所代表的时代的荒诞。如果岳张之间产生了爱情,会转移读者的注意力。另外,在我心里,张秋雯是喜欢岳超峰的,岳超峰把她看成一个知己或姐姐,我觉得这个关系比爱情关系更高级,而且朦胧,让人遐想,应该对小说的主题表达更好。
腾讯文化:您对岳超峰有些许的不认同感吗?
王斌:也没有,某种意义上,他就是我的化身,我在生活中就是这样的,耿直、热血、率真,轻易不会妥协,隐着一份高贵的自尊心,任何利益收买不了我,我宁愿吃亏。
腾讯文化:您对吴正大有些许的认同感吗?
王斌:没有,一点都没有,我就是特别瞧不起他,特别想用刻毒的方式把他那张伪装的皮全部扒光。
腾讯文化:小说结尾吴正大的电影被同学质疑是垃圾,他摆出了后现代主义大师杜尚的作品——小便池,作为回击。众人陷入一种惶惑。这是否意味着您对您的信念也存在一丝怀疑?
王斌: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个结尾是最后一稿,事前我设置的另二个结尾的方案,都自我否决了,改成了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由吴正大拿杜尚的小便器的那套说辞,我一方面想嘲弄一下当代艺术,另一方面,等于高调地把这套理念给它亮出来,评价和思考留给读者,我就不做评价了。
一个好的小说,呈现的是生活中存在的诸多悖论,亦此亦彼的悖论,所谓:呈现,但不要告诉,这点很重要,这是好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准。
腾讯文化:结尾岳超峰和张秋雯都各自出走,有点像时代边缘人的感觉?
王斌:对,我在我的另一部小说《遇》中,写的主角就类似于岳超峰这个人,按照李保田的说法:你写了一个中国式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边缘人,或说多余的人。我们这种人很可能终身就都在流浪,只是以精神的方式在流浪,所谓的行囊,就是我们的思想。
在退出电影圈之前一直是很孤独、分裂的状态
腾讯文化:2006年您选择退出电影圈,出于什么原因?
王斌:简单地说,那个时候电影的理念和我的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已经感到不适应了。
如果再坚持下去,很可能就会影响到我所珍惜的友谊,只能放弃,这是最好的选择,况且,我少年时就为自己立下了当作家的目标,后来一不留神成了文学批评家,但心有不甘,但因为没时间写小说,这理想就耽搁了下来,离开电影圈,等于给了我一个写小说的时间和机会,也给予了我一个重新思考的时间,就这点而言,我感谢我的人生,我没有辜负我的人生。
腾讯文化:选择离开的时候,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王斌:最初的那一段很孤独也很失落、迷茫,我希望还能合群,可是非常奇怪,在那样的众声喧哗的氛围里,我会感到更加的孤独和无望。那个时候一直是这样一种状态,很分裂的一种状态。
腾讯文化:离开之后的生活是怎样的?
王斌:过上一种特别清贫的日子,没有收益,要节衣缩食。每天中午、晚上都要出去觅食,和那些最底层的小职员、民工们一块吃饭。之前大概有七八年我是走到团结湖,沿途找餐厅,跟人在一块拼桌吃,有时候你中途插进来,他们还会讨厌你,但你可以倾听他们聊天;有时出去办事要去挤公共汽车,挤地铁,你要知道,此前,我有十多年有坐过地铁与公车了。这样一种生活常态,让我对日常生活恢复了一种切近的感知,感受生活的冷暖,甚至寒意。
但是心中的那个文学理想我从来没有泯灭。1999年,我偷偷地写下了第一部小说《遇》,写到五分之四,我突然写不下去了。因为那时候我在电影圈的价值观是混乱的,我突然看不到那些主人公的精神归宿了。结果2007年,当我重新提起笔时,竟一口气就补上了尾声,我突然明白他们是谁,要去到哪里了。所以我庆幸离开电影圈,重新回到了这种孤寂的生活状态,这是一个好作家需要的状态:孤独与痛苦。离开喧嚣之后,自然地跟时代拉开距离,你会把时代下的问题看得一清二楚。
这么多年我就是这么一路走下来的。我从来没觉得我们这代人的思想已经老去,虽然我们处在一个拒绝思想的时代,但我始终认为有一天思想仍然会归来,因为我们已经把很多弥足珍贵的价值毁得差不多了,毁到这种程度,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我们需要重建思想和价值了,否则我们人人都不安生。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在思想消亡的时代下,我们真的需要寻找曾经丢失的那些值得珍惜的高贵价值。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深植于人性之中
腾讯文化:写完了这部小说后,您当时对小说有没有一个自我评价?
王斌:写完《六六年》和《浮桥少年》(还没出版),我心里特别有底,就是写到最后,有一种巨大的情感之潮从我心里浮升了起来,把我整个人裹挟了进去,让我欲哭无泪,我心知,那就是我终于抵达了我预定的目标。记得我写《六六年》,写到中段时,我忽然想到我的结尾是什么的时候,那一刻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孤独的身影,在那个茫茫不见边际的大漠中,背着巨大的行囊独行,天地竟如此辽阔悠远……这个感觉一直带着我强烈地往下走,我就知道它一定是好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写完之后,我有点拿不太准,但是我唯一能够安慰自己的,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所有文字是从我内心深处滚出来的,我没背叛自己的心灵,我忠诚地完成了我内心想要表达的内容。但因为写的是当下,你还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一个高于当下的视点,这是第一。第二,我第一次写这么荒诞的,带有黑色幽默的后现代式的小说,这需要市场检验。
腾讯文化:这本小说您期待得到读者的什么样反馈和评价?
王斌:我最期待的就是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概念先普及了,它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都会有的、根植于人性深处的情结,对它,我们要给予足够的警觉,不要被各种莫名其妙的“偶像”给洗脑和绑架了。人活在世上,最有价值的,是你拥有一个不被别人所左右的,独立不羁的思想。
另外,我希望这个小说,能唤醒“综合症患者”沉睡着的内心,虽然我也不能指望它真正地能改变了谁,但起码让人对自己内心的那个怪兽有所警觉。我觉得文学的一个最大的作用或说功能,就是袪蔽,去除社会的遮蔽,启示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