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当时有很多这样的声音:“两德的分裂是德国因为奥斯维辛而承受的惩罚。”在这个问题上,奥斯维辛确实是被工具化了——东西德的分裂不是因为奥斯维辛,而是因为其他国家害怕德国。

马丁·瓦尔泽在朗诵自己的作品(供图/歌德学院)
继8月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来华后,9月中旬,德国重量级作家马丁•瓦尔泽也来到中国。
作为当代最著名的德语作家之一,瓦尔泽曾和诺奖得主君特•格拉斯轮番执掌德国文坛。格拉斯去世后,瓦尔泽成为德国文坛名副其实的“文学君主”。迄今已出版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的他,也拿了二十几项文学大奖,德国有名的文学奖更是一个不落。有人评价,他在德国公众中的影响,仅次于德籍教宗本笃十六世。
9月18日下午,在北京凯宾斯基酒店大堂,腾讯文化记者见到了瓦尔泽。对于中国媒体轮番轰炸似的采访,第三次来华的瓦尔泽大概已经见怪不怪。但长时间连轴接待我们这些“各异的头脑和古怪的意见”,89岁的他还是流露出了一些疲态。
而造就这种疲态的原因之一,或许还有那些针对他的形形色色的误解。于是顺势,腾讯文化记者将“误解”作为这次简短谈话的主题,以此厘清一些围绕在他身边的“不靠谱意见”。
扭头不看奥斯维辛画面,不是在回避
腾讯文化:对于像你这样完整经历过纳粹的最后一代人,“奥斯维辛”是不是一个被强加的文学主题?怎样去应对这样一种文学上的“时代遗产”?
马丁•瓦尔泽:奥斯维辛本身不是一个文学主题。对20世纪的每个德国人来说,它是最大的一个挑衅,或者说,是他们要克服的一个挑战。
1964年,德国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在法兰克福主持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审判。我去参加了这场审判。我说我必须到现场,对在奥斯维辛发生的真实情况,我必须有一些基本的亲身了解,而非仅仅通过报纸或电视。
亲身经历这次大审判后,奥斯维辛就成了我作品中时刻存在的一个主题。为此,我写了很多文章,也创作了一些话剧作品。歌德42岁时,在法兰克福为他的朋友们热情洋溢地朗诵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标题是《莎士比亚没有尽头》,我也写了一篇关于奥斯维辛的文章,借用了歌德的这个标题,叫做《奥斯维辛没有尽头》。

奥斯维辛审判现场
腾讯文化:关于奥斯维辛,你的两个观点流传较广,一是你对奥斯维辛的公式化和被工具化不满,一是你反对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犹太人屠杀纪念碑。此外,流传较广的,也包括你对集中营画面扭头不看的传闻。这是否会造成外界的误解,即你在回避?写作时,如何应对盘桓在这一主题上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
马丁•瓦尔泽:奥斯维辛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德国社会对于奥斯维辛的讨论,在过去50年间一直都在持续,大家也都能去直面这段历史,这没有任何问题。但你提到的这两个观点,我觉得有必要解释或纠正一下,因为后来由于德国和其他国家一些媒体的断章取义,产生了很多误解。
首先是关于奥斯维辛的“被工具化”。它一定要加入一个背景,即我强调的,应该以历史的维度来看待德国。当时有很多这样的声音:“两德的分裂是德国因为奥斯维辛而承受的惩罚。”在这个问题上,奥斯维辛确实是被工具化了——东西德的分裂不是因为奥斯维辛,而是因为其他国家害怕德国。我们不能什么时候都拿奥斯维辛当借口。
第二个误解,就是关于这个“扭头不见”。我们的电视上经常会播奥斯维辛集中营特别可怕的场景,我说我不能看这样的画面,扭头是因为我不忍心看,因为太悲惨了。这就好比电视上如果正播美国人在越战中枪杀当地人,我也会扭头不看一样。并不是只因为出现奥斯维辛我就扭头不看。
看到这样的画面,我觉得非常难受,所以我不看。我相信这是人性的本能,但没有人敢说出来,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应该坦率地说出来。我这么说了以后,很多人出于维护道德的需要,就开始说“你完全不把奥斯维辛当回事”,但我其实只是在讲个人感情接受的方面。
德国人往往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喜欢盯着别人,认为别人不能不把奥斯维辛当回事,却不在乎自己怎么看,也不做自己的道德评判。

马丁·瓦尔泽(供图/歌德学院)
小说针对的是“批评家”,而非“犹太人”
腾讯文化:在小说《批评家之死》中,主人公原型是德国著名的评论家拉尼茨基,小说里也表达了对批评家的不满和讽刺,而拉尼茨基的座右铭恰恰是:“能够毁掉作家的人,才能做批评家。”这本书在当时似乎也引发了很大的误解。在作家于批评家之间,你认为存在一种近乎古老的敌意吗?
马丁•瓦尔泽:作家和批评家并不是互有敌意的一对职业。每次我的书出版之后,如果能读到别人的批评性文章,我会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和满足。一个作家听到的全都是赞美之词,那其实是很悲惨的,因为你从中没办法获得任何滋养——只有在批评中,你才能知道哪里还可以改进。
当然,也有一些批评家,他们的评论性文章能够彻底毁掉一个作家的创作生涯。比如你提到的拉尼茨基。
在25年的创作生涯中,我面对的最强大的一个批评者就是拉尼茨基。我曾经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在爱的彼岸》,拉尼茨基就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在文学的彼岸》。在这篇文章里,他直言我的写作水平太烂,“为他好,同时也为了我们自己,希望这本书尽早被人遗忘”,并要求将我彻底地踢出文学界。但我始终没把他作为一个敌人,而是把他作为一个对手。对于我来说,这种经历就是作家身份的一部分。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你写书,他就有权利评你的书。
被拉尼茨基猛烈批评的作家不只是我,还包括君特•格拉斯、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等等。他们的作品也都被他狠狠地批过,但不同的是,其他人都没有正面和他对抗,而我却把他写进了小说《批评家之死》。但我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并没有怀着恶意。我塑造的这个形象要高于他的原型,我甚至把他塑造得有点伟大,几乎是拿他和肯尼迪、斯特劳斯这样一些了不起的政治家相比的。
这部小说引发的反响是疯狂的。拉尼茨基是一个犹太人,我因此被指责为一个反犹主义者,因为在小说中,我没有一个词是针对他的犹太人身份的。我只是针对他的批评家身份,将我们两人之间的往来做了一个友好的清算,但所有人的理解都是:你在针对一个犹太人。(无奈摊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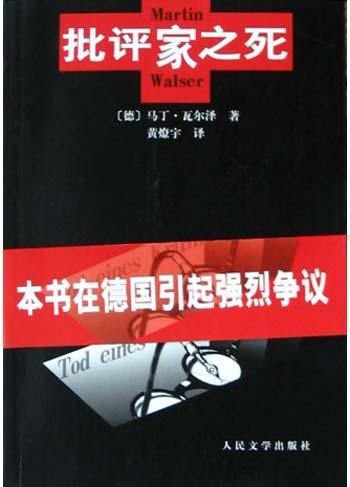
马丁·瓦尔泽的小说《批评家之死》
腾讯文化:类似这样的来自评论的误解还有哪些?除了将评论家作为原型直接写入小说,你还有哪些方式来化解这种误解?
马丁•瓦尔泽:也许我可以跟你聊聊我的另一本小说《恋爱中的男人》。在此之前,在我的几部长篇小说里,男性角色都比女性角色大二十几岁,我安排他们相恋。于是有很多女性评论家就纷纷撰文批评,认为我的这种人物设置是典型的男权主义思想,是对女性的一种物化,诸如此类。
于是我想,那我写歌德好了,歌德是一个很好写的人物,而写他恰恰也是我自己的一种深层需要。于是我写了《恋爱中的男人》。在小说里,歌德74岁,他爱上的女性乌尔莉克才19岁,两人不再是相差二十几岁,而是相差五十几岁。
尽管这么大的年龄差确实注定这不会是一段幸福的爱情,但小说出版以后,再也没有任何女批评家批评我“男权主义”,大家都说这个小说写得太好了。(笑)

马丁·瓦尔泽(供图/歌德学院)
把生活塑造得比它本身更美
腾讯文化:这次你来访华,也带来了新作《一个寻死的男人》。在标题上,它确实让人想到了《恋爱中的男人》。而小说的书信体形式,则继承了你的另一部爱情小说《第十三章》。都是讲述老男人的爱情故事,如果说《恋爱中的男人》处理的是老男人的精神恋爱,那么在《一个寻死的男人》中,会涉及恋爱中的肉体叙事吗?
马丁•瓦尔泽:书信体的长篇小说,其实在文学史上是常用的体裁,但18世纪以后,已经很久没有再出现过以书信为主的长篇小说。这是我的一个尝试。今天的阅读环境,对长篇小说来说已经很艰难了。在今天,更多的爱情小说充斥着色情、诱惑、性欲的描写。
在我的书信体小说《第十三章》中,我也曾经构思过是否让男女主人公见面,但我觉得如果见面,就没有办法写下去了,所以就继续让两个人不见面,只是通过书信往来,而不去宾馆。但《第十三章》出版后,接受度特别高,我感到很高兴,但也非常吃惊。我去统计了报纸上的公开书评,有75篇文章是赞扬的,只有5篇认为写得不好。所以我认为,我们德国的文学评论能力还是很好的,虽然这种书信小说构造出来的柏拉图式爱情模式,不见得很符合现代社会现实,但这种爱确实还是被大家所理解和接受的。
我想强调的是,我之所以从事写作,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还不够好,我希望在创作中写更好的生活,希望把生活塑造得比它本身更美。我是追求美的一个作家,你甚至可以说,我是一个美化型的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