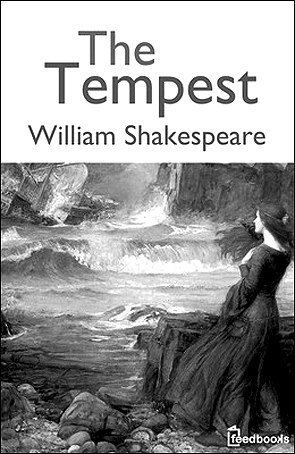
“我们的狂欢已经终止了。我们的这一些演员们,我曾经告诉过你,原是一群精灵;他们都已化成淡烟而消散了。如同这虚无缥缈的幻景一样,入云的楼阁、瑰伟的宫殿、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自身,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同样消散,就像这一场幻景,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都不曾留下。构成我们的料子也就是那梦幻的料子;我们的短暂的一生,前后都环绕在酣睡之中。”——《暴风雨》中的普洛斯彼罗如是说。
在《暴风雨》这部封笔之作里,在普洛斯彼罗放下他的魔杖告别奇幻岛屿之际——莎士比亚说出了这段通透也最能予以人慰藉的独白:任何一个熟悉莎士比亚的读者,或者说作为一个有阅读经验的读者,总是会在《暴风雨》里看到属于作者自己的东西。莎士比亚作为一个闻名的剧作家,《暴风雨》作为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作品里对以往主题的再现(如同《皆大欢喜》的放逐继而回宫的设置、《麦克白》弑君夺位的情节),“地球本身”(The Great Global Itself)这样的表达就是会让读者想起泰晤士河南畔那所属于莎士比亚自己的剧院。所有这些来自梦幻的东西又会回归到它最初的样子,莎士比亚并没有想到400年之后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他的作品被一次一次地复排演出,他当时想的东西只能更加实际,当他作为剧作家的生涯结束,他需要来自观众的首肯。
“因着我法力无边的命令,坟墓中的长眠者也被惊醒,打开了墓门出来。”这是写在《暴风雨》的故事里却没有被普洛斯彼罗展现出来的一幕。但是这个形容仍然让我们想到了作者本身。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他召唤了老国王哈姆雷特的鬼魂,召唤了苏格兰高地上的三个姊妹。而其实是,伊丽莎白时期奉行新教,鬼魂这个说法或者这个观念已经不存在了,那么这种背景下的鬼魂更加像一个“踪迹”,“踪迹”无法成为这个现行体系的一部分——但它仍然存在,它是我们写下的字上覆盖着的那把叉,它指向了更深的结构:经历过巨大动荡的人们的不适应和焦虑,曾经能够给予安慰的仪式现在已经失去了合法性,这给了莎士比亚这一代人心理上巨大的空洞,他早逝的儿子和哈姆雷特的名字仅有一字之差,无疑他将这份感情带进了他的作品,但是现行宗教并没有许诺他一条能和死者通话的路径,于是他在作品里召唤起了鬼魂。哈姆雷特在摇摆,在延宕,在自责,莎士比亚同样;而英格兰也早在1542年就已经明令禁止使用巫术,但无论如何莎士比亚仍然把三姊妹带上了苏格兰一场政变的中心。麦克白的弑君之心究竟是先于女巫的存在抑或是被女巫们激起,已经不得而知,《麦克白》后续许多情节并没有集中在女巫身上了,反而是通过三个模糊的女巫形象指向了某种暗涌,在哪些不可见的地方——我们的对于得失的恐惧会扎根会肆意生长,莎士比亚带给我们的仅仅是,动机的多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外在物,又多大程度来自于自己本身,这一片“程度”空间究竟如何丈量的问题,却不是答案。莎士比亚在一场腥风血雨之后仍然安慰了每个读者:不要用和你去爱的同等程度去悲哀,因为那样会无穷无尽。这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创作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普洛斯彼罗就像莎士比亚的另我,他所有作品的精粹都在这个小岛上一一展现:他是神,但是他的魔力仅限于这个小岛上,就像莎士比亚仅在他的作品中一样:他们企求观众原谅他在戏剧中所做的一切,就像这些魔法会让“一阵空气”的爱丽儿也能“感觉到它们的痛苦”一样,至于莎士比亚,在他的作品里他甚至召唤了上一个时代的幽灵,煽动了这一个时代的焦虑,他同样需要为这些“舞台上两点钟的悲欢离合”向所有他的观众祈求认可以及原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