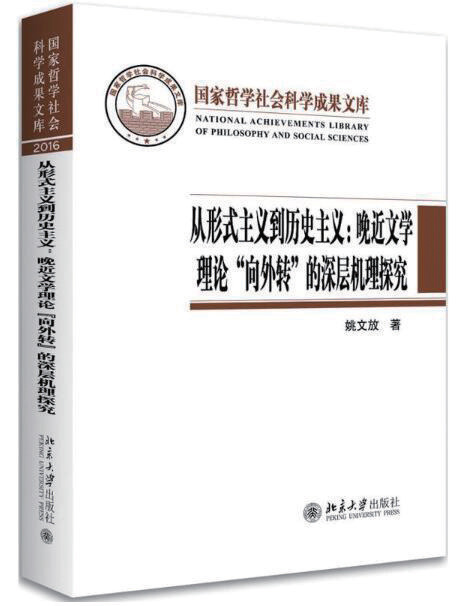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西方,文学研究的重心发生了重大转移:已由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了“外部研究”,已由重形式研究的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现象学、解构主义等转向了重作品内涵研究的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生态主义等等。与其影响有关,中国当代文论也在发生着同步性的变化。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一书正是敏锐地抓住这一世界性的文论态势,从“问题、观念、概念、论争、理论、方法、基础、动向、宗旨”等九个方面,结合“文学性”、“文学理论”、“文化政治”、“文学经典”、“话语转向”、“症候解读”、“美学重构”、“理论回归”、“中国当代文论”等九个相关的重要问题,对其“转向”的内在机理、特征、意义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由具体论述可见,作者基于对西方文论、尤其是诸多前沿问题翔实而深透的把握,特别注重运用“谱系学”的视野与方法,尽力将与“转向”相关的概念范畴纳入特定系统中进行比较分析。这样,不仅使原本纷纭复杂的“转向”问题明晰可察,同时亦深化了读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如在关于“文学性”的论述中,作者将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与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所讲的“转向”性的解构主义的“文学性”进行了比较,指出二者虽有本质区别,又有内在关联。其区别是:前者乃指文学中的“文学性”,后者则指非文学中的“文学性”;前者意在划定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后者则意在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前者要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后者看重的则恰是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正是因其本质差异,解构主义的“文学性”,自然也就体现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向。其内在关联是:在注重“内部研究”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中,实已埋下了自我解构的种子,如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雅各布森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玩笑之类在语言结构上与抒情诗及小说颇多相同之处的见解中,实已含有对“非文学”的“文学性”的认识;雅各布森所注重的对纵横交错的语义关系网的探讨,以及在纵横意义轴上建立的语义关联理论,实已“无不通向外部世界,通向历史、现实和文化”(引文均见该书,不再注明)。作者正是据此内在关联,清晰地揭示了在此问题上文学理论由形式主义转向历史主义的内在机理。也正是经此比较分析,更为精当地阐明了“转向”前后两种“文学性”的不同特征、内涵,以及均未能真正回答“什么是文学”的内在局限,进而得出了如下结论:“有必要打破以往的思维定势,对于文学的自身规定性与外部规定性这两者的复合关系给予更多的重视”;“文学是一种关系概念而非属性概念,是一种复合性概念而非单一性概念”。这类基于“谱系学”的比较分析得出的见解,无疑更为切近文学的实际,也更有助于我们合理地把握文学的实质。
在关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论述中,也都可以看出作者宏阔的“谱系学”视野,以及对相关问题的深邃洞察与缜密研判。
关于“文学理论”观念的转向,作者将“理论”、“后理论”与传统的“文学理论”三个具有谱系性的概念范畴进行了比较分析。明确指出:取代了“文学理论”的“理论”,谈论的多是哲学、社会学、符号学、阐释学、现象学、生态学之类问题,实际上已是文化研究。近些年来出现的所谓“后理论”,则不过是与文化研究相关的“理论”的进一步衍化,其区别只在于“理论”关注的是宏大社会现象,“后理论”关注的是琐屑叙事。对此“转向”,作者一方面高度肯定其“对于以往不同学科、专业之间,以邻为壑、老死不相往来的弊端是一次反拨”,有着“通往对话、交流、沟通、合作、综合、民主、开放、多元、宽松、和谐等当今时代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已与“文学”不相干的“理论”与“后理论”, 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
关于“文化政治”,作者抓住的具有“转向”性的“谱系性”范畴是“社会政治”与“文化政治”,以及衍生性的“阶级政治”与“后阶级政治”、“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实践政治”与“审美政治”等等,认为“转向”之后的“文化政治”,虽缘其不再像“社会政治”那样注重与国家、政党、阶级相关的社会权力关系,有着消解宏大历史叙事的不足,但对与性、性别、年龄、民族、种族、地域有关的文化权力关系的重视,自有其切近人类当今社会现实的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是今天文化研究取得的重要学术进展和理论成果”。其中,对人本身的更多体贴与担当,对人间化、草根化的日常生活的更多关注,亦与原本即具“人学”性的文学及文学理论之间的关联更为密切。
关于“症候解读”,作者将阿尔都塞、马舍雷、卡勒的见解进行了比较,认为在这几位学者的思想中,“症候解读”理论像一条红线一以贯之,但又先后有别,转向明显。阿尔都塞关注的尚是一般文本,注重探讨的尚是阅读与批评的一般规律;马舍雷则将其引向文学领域,用之于文学批评,以及关于文学批评的批评;卡勒在“症候解读”基础上提出的“表征性解释”,关注的则是文化研究,体现的是文学研究“向外转”的历史主义趋向。对此转向,作者的看法是:有时虽难免“过度阐释”之弊,但“从文本所暴露的‘症候’着眼,从其不可见、不可言、不可知之处看出漏洞、抓住破绽,进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解读”方式,大大拓展了文本解读的生产性空间,是在马克思所开创的“艺术生产论”基础上的重大进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