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征文选登
吉林省委宣传部 《文艺报》社 吉林省作家协会 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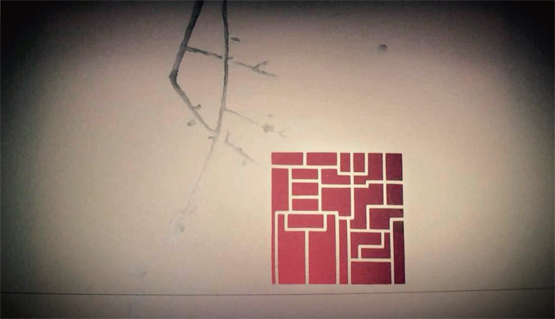
在社会转型时期,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历史标准与审美标准都会具有特殊的内涵,面对更加复杂的历史背景,当下中国叙事在历史与审美两个维度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从历史与审美两个向度的延展性而言,中国故事有巨大的可能性,中国叙事大有可为,在叙事主题的丰富性、叙事空间的诗性与弹性、叙事策略的多样性、叙事语言的驳杂性等方面所具有的可能性是20世纪以来任何历史时期都不能比拟的。然而,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中国叙事还要面对来自全球化的冲击,通过合理的姿态与手段确认其自身身份,显得尤为急迫。作为中华美学经验的一个发展阶段,以及作为中华文化本体的重要部分,当下的中国叙事亟待对接中华美学的传统经验,为自己开辟新的叙事空间与方向,确立新的叙事形态。这种对接有许多种可能的维度,以下三个维度也许是其中最为重要的。
一、当下立场与历史眼光的统一
文学创作与批评从来都是当下立场与历史眼光的辩证统一,偏向其中哪一方都会产生严重的诗学问题。《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优秀长篇小说处理的都是巨变时期的社会现实,这些作品都同时兼具对现实的深刻剖析与对历史规律的深入阐释,具有卓越的艺术成就。在这个方面,当下中国叙事主要存在三种倾向与偏差。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当下书写延伸为历史追溯,大多从现实社会的各种现象出发进行溯源,往上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20世纪80年代、1949年后甚至整个20世纪,从而出现了大规模现实与历史对照的小说模式。这种模式将现实社会中的某些弊端简单归结为历史演变,并未深入其中探寻其文化根源,存在将共识性问题偷换为历时性阐释的嫌疑。这种模式在当下立场的视野中简化了历史眼光,认为所谓历史性地理解问题就是将问题放置在历史背景中而已。其次,许多作家和作品都倾向于将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对立,在二者的优劣中来阐释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这种方式总体上是合理、可行的,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根源一定程度上也主要表现为这种差异,但是过分强调两种空间的差别,甚至将城市空间简单视为乡村空间的侵入者与毁灭者,将城市空间视为当下现实的代表、将乡村空间视为原始状态而将共存关系置换为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和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其结果必然是当下现实的复杂性被遮蔽和简化,存在坚持当下立场而忽视历史判断的嫌疑,也存在以当下立场改造、异化历史视野的嫌疑。再次,与上述两种现象相反,有些作家尝试用当下眼光重构20世纪历史,每个历史阶段凝固为一部长篇小说,每部长篇小说就像一块历史拼图,从属于作家重构历史的宏达目标。这种所谓史诗性的追求对于变动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而言有其先天的合理性,但也容易带来作家与作品对每个时代的肤浅书写,并不能深入到时代精神内部,从而也就很难建立起真正的历史眼光。在每部作品之间,作家的史观虽然多少有些变化,但变化不大,结果是作家的创作进程变成了同一种历史观念的不断铺展。
通过这些现象可以看到,当下的中国叙事还没有发展出辩证地统一当下立场与历史眼光的能力,对社会现实的把握能力还有所欠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仍然比较肤浅。在这些方面向中华美学传统学习,应该成为当下中国叙事的一个发展方向。
二、悲悯情怀与反思深度的统一
在当下的社会转型中,社会现象的复杂程度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书写空间。在面对这个时代时,所有中国故事都需要穿透更多的时代迷雾,以更大的情怀去理解和反思社会现实,才能寻找到时代精神深处的正向信息与正面能量,才能提供更多的未来可能。其中,对于建构恰切的叙事立场而言,当下中国叙事需要在悲悯与反思之间找到更加微妙、更加辩证的平衡点。
面对社会底层,许多当代作家往往表现出单面的道德同情,常见的情节模式包括农民进城以后变成城市生活的受害者,或者城市内部从志向高远到与世俗同流合污、从对欲望的决绝抵抗到妥协共谋。不可否认,这些现象都是大量存在的,但是在叙事中将其视作某种通用的叙事捷径,却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同时也很难超越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书写深度与艺术成就。这种现象描述并没有上升到精神高度,没有能够从精神层面揭示当下中国整体性的深刻特征,无法做出实质性的时代书写。
面对社会现实中的负面因素,许多作家更喜欢以现象堆积或纯粹个体的视角来建构总体反思。这些现象与人物无疑是当下现实的组成部分,但却无力承担总体上审视中国当下现实的任务。这种书写方式表面上看坚持了对现实的反思,但无论其中表现出的悲悯情怀还是反思深度都有明显的局限。将深刻的现实反思与高远的人性视野相联系,将阔大的悲悯情怀与深刻的精神现象相联系,才是中国叙事应有的品格。
三、深入现实与超拔想象的统一
中华美学传统中积累了许多优秀的经验来处理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结构关系,许多风格与手法已经沉淀为中国美学精神的核心质素。“托物言志”、“形神兼备”、“意境深远”都与此相关。如何在当下的叙事实践中有效地借鉴和利用这些文化资源,值得创作者和批评者深思。没有经过想象加工的现实书写只是一种粗加工而已,不是作家经验与社会现实的化合反应,不具有深厚的文学品质,无法成为优秀的中国故事;脱离现实的纯粹形式想象则只是无源之水,没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无论是《红楼梦》还是《聊斋志异》,作为两种不同方向的书写实践,之所以能够达到永恒的艺术高度,它们对现实与想象的辩证处理是最重要的原因。艺术想象不仅仅包括对情节乃至细节的精细加工,还应该包括对当下中国的心理性、精神性的把握,并结合合理的形式最终建构起对时代生活的诗性把握。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不难理解,但实现起来却极难。伟大的时代文学与伟大的文学时代都以能够创新性地解决二者关系作为标志,无论是中华美学历史还是西方文学发展进程都能体现出来。
除了以上三个维度,还有许多可能对接当下中国叙事与中华美学经验的维度,如苦难意识、性别叙事、伦理书写等。综合辩证的书写视野和多样丰富的叙事手段是这种对接的基本条件,而在历史与审美两个层面上更好地贴近现实、贴近剧烈变化中的当下中国,需要更多的作家、批评家投身其中。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对于当下中国的叙事进展而言,核心的任务仍然是更好地理解幽微的诗学想象与复杂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向中华美学经验中挖掘更多的精神资源则是必经之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