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作家的写作与他(她)的身世经历关系紧密,而一个杰出作家人与文的契合度似乎更甚。许多时候,它们甚至可以相互印证、互为解读。作家萧红和她的作品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萧红 资料图片 以“悄吟”为笔名,展现出孔武有力的文学世界 萧红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杰出作家,在于她实践着时代对作家的“立言”要求。她两次到北京求学,思想上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不同,她有着强烈的女性自觉和强劲的生命意识。 这种生命意识内涵宽广,来源于一种对生命平等的珍视之心。这里的平等,不仅有大时代文学所表达的男女平等,而且有身为知识女性与未曾受过教育的穷苦女性的平等。正是这样的平民立场,使其文学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她的第一部小说《弃儿》写出穷苦女性的悲苦处境,同时也写出一个抛却以往种种纠葛、已经觉醒女性的刚毅和勇猛。萧红发表作品时用的是笔名“悄吟”,但《弃儿》的力度有着一种义无反顾的决绝,其中包含着一个作家对大时代的呼应。 如果萧红只是一个专注于自身经验的作家,那么她会是另一个萧红。萧红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她的视野从来是由己及人,看到的不只是自己从旧家庭中走出来的阵痛与叛逆,以及为之付出的痛苦与艰辛。她看到的还有更广阔世界中的女性,她们没有反抗,逆来顺受,但她们的种种忍耐与屈辱也并不能换来安稳与幸福。 《王阿嫂的死》写的是王阿嫂丈夫被张地主逼疯烧死,而自己也被张地主踢打,以致在产后死去,新生儿也未能活成,养女又成为孤儿的故事。小说中,王阿嫂最大的抗争也只能是“哭”与“死”,她哭已死的丈夫,哭自己已死的心。萧红的平民视角显而易见,小说中对人性恶的揭示是有力的,并且通过文学性的书写呈现出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革命文学中的反封建主题,对于萧红而言,是从实践和体验中来的,而不只是从书本和理论中来。这使得萧红文学作品的平民视角与女性觉醒交错在一起。她写的穷苦人也是她自己,因有深刻的体验,所以她的文字虽以“悄吟”这个名字“代言”,却孔武有力。她是真如鲁迅所言“将自己也烧进去”的作家。萧红在平民与女性的身份和命运的双重关注中,将自己的文学打上不独属于自我天地的时代烙印。  20世纪30年代,萧红(右)、萧军(中)、黄源在上海万氏照相馆合影。资料图片 以勇猛、怒吼式的文学,发出一位作家的呐喊 一个作家不可能也不可以游离于他(她)的时代。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东北沦陷,萧红的出走与流离失所,除却她个人反封建、争自由的因素外,她的命运还裹挟着一个更大的家国背景,这就是1934年与萧军一起从哈尔滨到青岛之后,萧红创作完成的《生死场》的心理起因。 《生死场》何以在家国破碎的年代里,如鲁迅所言,给人“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原因在于作品本身的品质与气度。 《生死场》从一只山羊、一个小孩、一个跌步的农夫、一片菜田写起,以十七节文字,绘出20世纪30年代初期东北农民生活的图景。作品的镜头剪辑得很碎,没有特别主要的人物或贯穿始终的故事,却保持着生活原有的真实。这种散漫的写法,使得小说呈现出无主角但场景明晰、无情节但细节动人的特点。如果只是狭义地将它视为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铺陈书写,就低估了作品的文学史价值。《生死场》所提供的意义更为丰富。比如,从十一节开始,作品写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百姓的蹂躏,更写出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着“有血气的人”。老赵三这个曾经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醒来了,他和大家一起流着泪,“在红蜡烛前用力鼓了桌子两下”,表达着自己的信念:“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 萧红之所以是萧红,在于在那个家国破碎的时代,作为从东北逃亡出来的作家,没有停留于对个人遭遇的控诉和对女性弱者形象的描摹,而是以一种勇猛、怒吼式的文学,向世界发出一位作家的呐喊。 离开家乡越远,萧红的故园之思越重,并且与故园之失纠缠在一起。她在以“生”“死”命名的小说中,借笔下人物呐喊出的“不当亡国奴”,激荡起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声,让我们至今热血沸腾,原因在哪里?在于一位饱经沧桑、居无定所的作家对民族尊严的守护和对生命力量的礼敬。 21世纪之初我到青岛,专门找到萧红、萧军1934年住过的旧址——观象一路1号。走上石阶,门上落锁,无缘进入。他们在这里只住了不足半年时间,却分别写出了《生死场》《八月的乡村》。我长久地站立在那个门口,我要让自己记住,就是在这里,就是在青岛,在那个飘摇不定、风雨如磐的岁月,白纸黑字,萧红替家乡农民老赵三发出“不当亡国  《生死场》一九三五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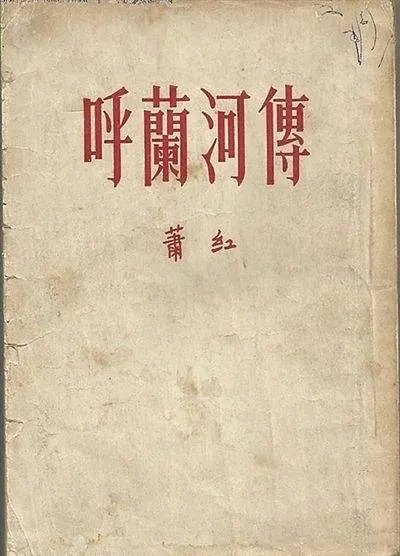 《呼兰河传》一九四一年版 以鲁迅为精神偶像,力图写出《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的篇章 从文学创作的本质上来说,萧红是贴近鲁迅的。这种“衣钵”传承,可以从她的文学实践中看出。1940年1月,她在香港完成了两年前就开始写作的《呼兰河传》。她在对儿时故乡的回望之中,回归了与《生死场》中救亡主题同等重要的启蒙主题。 《呼兰河传》也是散点化透视,没有结构主线,没有中心故事,也没有主角人物,而是日常生活场景的铺陈与百姓命运的延展跌宕,有的是北方小城里关起门来过日子的居民,还有围绕这小城的一些外来讨生计的人们,卖豆芽菜的、卖麻花的、卖凉粉的、卖瓦盆的、卖豆腐的,还有看火烧云的。总之日子像河水一般平稳。 在这些“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之外,还有诸如跳大神、放河灯、唱野台子戏、逛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盛举”,特别是祖父与“我”共同拥有的后园,是一个孩子的自由世界。这里有蜻蜓、蚂蚱、蝴蝶,有樱桃树、玫瑰,有“蒿草当中开了的蓼花”。 但与这些景象在同一时空中的,还生活着小团圆媳妇,还有冯歪嘴子一家。这两个章节体现着萧红的文学启蒙思想。小团圆媳妇嫁到老胡家才12岁,亲人的残酷与看客的冷漠,联合“谋杀”了一个活泼的生命。和鲁迅一样,萧红批判了这样的精神麻木。 冯歪嘴子一家让人看到希望。女人死后,留下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小的刚刚出生,冯歪嘴子在别人绝望或是看热闹的环境中,反而镇定下来,“他觉得在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他不管他自己有这份能力没有,他看着别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他觉得他也应该这样做”。 萧红的笔端留下一抹亮色:“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上去饮水了。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给他东西吃,他会伸手来拿。而且小牙也长出来了。”这样的句子,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中华儿女的坚韧与强悍。在对故乡的一份记忆中,萧红对养育她的祖父表达爱意的同时,也给了她自己曾经在离乱中失去的两个孩子以文学的活泼生命。 在1941年的香港,萧红写下《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这些启蒙主题作品的同时,仍写下不少关于救亡主题的篇章。在《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中,她传达出“在最后的斗争里,谁打得最沉着,谁就会得胜”的必胜决心。在《“九一八”致弟弟书》中,她对青年表达出自己的信心,“你们都是年青的,都是北方的粗直的青年。内心充满了力量,……你们都怀着万分的勇敢,只有向前,没有回头。……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这与她写于1938年的《黄河》《汾河的圆月》《寄东北流亡者》等作品相呼应,显现出一位作家与时代和民族的密切关系。尤其是《黄河》的结尾,对于“我问你,是不是中国这回打胜仗,老百姓就得日子过啦”的百姓之问,八路军兵士回答是:“是的,我们这回必胜……老百姓一定有好日子过的。” 从呼兰县出发,从哈尔滨到北京、青岛、上海再到东京,从北京到上海再到临汾、西安、武汉、重庆,直至香港,萧红一生是在漂泊中度过的。我们从《商市街》中即可了解她所经历的一无所有和饥寒交迫,但无论在哪里,无论是迁徙、离乱、饥饿、病痛,她都始终抱定这一信念。这是胜利的信念,也是对人的信念。 与这信念一起让我颇感折服的,还有萧红文学风格的自由。当时多位评论家对她小说的散文化风格有着不同看法,萧红并不辩论,只是在与聂绀弩的一次谈话中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聂绀弩追问:“写《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之类吗?”萧红的回答相当率真:“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这显现出萧红的超越之心。她也的确试图在写作中加以践行。 茅盾曾在1946年《呼兰河传》的再版序中写道:“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种评判是公允的,但我不大同意文中隐约存在对萧红与大时代隔绝的判断。的确,萧红是寂寞的。这寂寞的由来,并非感情上的一再受伤,或是对居无定所的厌倦,而是她在精神上一直是一个人的,一直与她所在的知识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于她进行观察和审视。在最后的岁月,她一边体味这寂寞,一边仍在拼命写作,她真正体味到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滋味,这可能也是她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的身先死的“不甘”,这可能就是她死后想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的原因吧。 萧红去世时不足31岁。自1932年写诗开始,到1942年1月,不足十年时间,她写下了百多万字的作品,而且还是在颠沛流离、贫病交加之中!这些作品,是她个人艰辛生活的见证,也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对于国家、民族、人的精神的一份思想的贡献。这思想,是她于生死场上跋涉而来的。 萧红不朽! (作者:何向阳,系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