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目前生态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由于地理位置、文化传统、经济模式等因素的影响, 中西方传统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建构方面存在根本差异。大体而言, 西方倡导“天人两分”, 中国崇尚“天人合一”。但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 随着“中体西用”等对外交流战略的实施, 中国不断学习、吸收西方的机械论自然观, 这种自我西化特别鲜明地表现为:主动译介“Nature”“Science”这两个最能代表当时西方自然观特征的概念。文章基于中西传统自然观的对比, 深入探究这两个西方概念是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 并革命性地颠覆曾主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对该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了解翻译对中国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重构的影响。 关键词:科学;自然;翻译;生态研究 作者简介:陈月红,湖北宜昌人,博士,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批评与翻译研究。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危机背景下生态研究的核心问题。从古至今, 人类文明的发展既依赖自然, 同时又受制于自然。如何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了我们拥有什么样的自然观。东西方各个历史时期均有多种建构模式存在, 但大体说来, 中国传统自然观的主要特点是“天人合一”, 西方则是“天人两分”。[1,2]20世纪60年代西方现代生态危机爆发后, 以林恩·怀特 (Lynn White) 为代表的西方生态研究者意识到: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引发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源, 为此, 必须重新反思现有的宗教, 或者找到一种新的宗教, 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3] (P3~14) 在此背景下, 西方不少生态研究者希望能从建立在儒、释、道基础上的东方传统有机自然观中找到医治现代生态危机的良药, 由此, “出现明显的向‘东方生态智慧’回归的倾向。其中,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种具有独到的深刻思想内涵的哲学命题, 它所具有的现代生态伦理价值, 即对于维护现代人类所处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具有的现实道德意义, 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4] (P7) 但另一方面, 以菲利普·诺瓦克等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5~7]在目睹了中国当今社会各种环境灾难后, 对东方传统思想的生态价值提出质疑:既然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 中国目前的环境之恶劣又如何解释?这些西方学者完全没有意识到: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已经被彻底边缘化, 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机械论自然观, 以及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科学文化理念, 这一过程特别鲜明地体现为对“Nature”“Science”这两个典型的体现西方自然观的概念的译介。本文将探讨这两个词的译介是如何革命性地颠覆曾主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有机自然观的。 一、中西传统自然观的根本差异 如何理解自然?如何界定“自然”一词的意义?这是环境哲学的重要议题。[8] (P32) 由于地理位置、文化传统、经济模式等各方面的不同, 中西方传统文化对自然的认识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 由此表现为不同的自然观。 “自然”作为一个哲学概念, 其内涵在西方也是随着时代而变迁的。对此, 柯林武德[9]有专著探讨。大体说来, 20世纪之前, 西方自然观念的演变可分为三个时期:古希腊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有机自然观、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自然观、文艺复兴时期逐渐建立起来的机械论自然观。从历时视角来看, 这三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古希腊时期, 自然概念的发展受两种观念支配:第一, 自然是一个自我生长着的活的有机体;第二, 自然有理智的秩序是可以被理解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就受到这两种观念的支配。[10] (P73) 柏拉图的理论认为:可感的东西是不真实的, 或者至少远远不如可理解的东西, 或曰“形式”, 或曰“理念”, 来得真实。[9] (P57) 因为柏拉图推行超验世界, 并认为超验世界高于现实世界, 其“形式”理论中所包含的二元对立思想初见端倪, 也为后来基督教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基督教思想中金字塔式的“伟大存在之链”将世界的存在分为三等, 即:创造并主宰人类及世界的上帝;人;低于人的自然或万事万物。上帝是超自然的存在, 而自然由上帝创造出来为人类服务, 自然不具备独立于人的任何价值, 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已表现得十分明显。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 机械论自然观逐渐形成。一方面, 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与发展, 特别是机械的大量发明及使用, 大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和水平, 最终影响了西方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与看法。在培根、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笛卡儿等一批科学家或思想家的共同推动下, 自然科学逐步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实验或观察的基础上, 通过严密的数学逻辑来揭示自然规律, 自然被看成一台机器, 可任人拆解、分析、控制和改造。另一方面,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人认识世界的主体意识。通过与自然科学联姻, “人”成为认识“自然的理智秩序”的主体, 而“自然”成为被认识的对象即客体。 总之, 机械论自然观的建立一方面得益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为之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 在古希腊时期就已萌芽的二元对立思想, 到了笛卡尔时期, 成为人与自然关系建构的主导观念。机械论自然观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共同促进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确立, 并为工业文明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对20世纪初中国自然观重构产生颠覆性影响的, 正是这种二元对立的机械论自然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建构相对而言比较稳定, 20世纪之前主要体现为“天人合一”。庄子旗帜鲜明地主张“天人合一”, 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 。“天人合一”思想后来也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实践中, 由此而得出的根本态度就是“无以人灭天” (《庄子·秋水》) 和“赞天地之化育”;前者是道家的态度, 后者是儒家的态度。两者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本态度是一致的, 只是前者偏于消极地顺应自然, 后者较为积极。[11] (P11) 但总体而言, 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所最为关注的问题。从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到宋代朱熹对“格物致知”的阐释, 再到明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等等, 儒家学说倡导通过修身养性来提高自身的精神境界、德行及品格, 以此作为人生的理想与追求, 而不是从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中获得幸福感和成就感。与西方传统相比,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蔑视自然、征服自然的传统, 这与中国几千年来的农业经济模式息息相关, 农业经济凸显了人对自然的依赖, 强化了“靠天吃饭”、尊天为神的思想, 属于典型的非二元对立的有机自然观。中西之间的差异特别鲜明地体现为英语中的“Nature”与古汉语中的“自然”, 以及英语中的“Science”与古汉语中的“格致”的区别。 二、“Nature”“Science”两词的译介 虽说中西传统自然观存在显著差异, 但与此同时, 中国和西方在自然观方面的相互影响, 几乎是与双方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同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急剧变革的时期,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 中国开始实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外战略, 大规模译介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化, 开启了中国翻译史上的又一轮高潮, 翻译由此成为颠覆当时中国社会的革命性力量, “Nature”“Science”的译介即是明证。“Nature”一词的译介让中国人开始独立地看待物质世界, 并由此开始接受人为主体、物质世界为客体的二元对立思想, 而“Science”一词的译介开启了中国人全盘接受西方科学的、机械的自然观的历程, 世界由此成为一台冷冰冰的、巨大无比的机器。“Science”概念的引进标志着中国全盘接受西方科学的自然观, 而主宰了中国几千年的有机自然观被边缘化。这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如今的自然环境, 均产生了一系列颠覆性影响。 1.“Nature”与“自然” 英语单词“Nature”的词源一半来自于拉丁词“natura”, 一半来自于法语“nature”。在该词的历史演进过程中, 意义变得越来越复杂。正如雷曼·威廉 (Raymonds William) 指出的那样, “自然可能是语言中最复杂的词。相对而言, 比较容易区分出三方面的意义: (1) 某一事物的基本品质和特征; (2) 主导世界、人类或者两者的内在力量; (3) 物质世界本身, 包括或者不包括人类”。[12] (P219) 其中, (1) 、 (2) 和古汉语中“自然”的意义比较类似, 但 (3) 却是古汉语“自然”没有的意义。依据牛津在线辞典 (Oxford Dictionary Online) , “Nature”在19世纪的定义曾包括人类, 但后来就仅指物质世界本身。如今, “Nature”是指:整个物质世界的现象;尤其是植物、动物以及地球自身的特征和产品, 与人类和人类的创造相对立。[13]依据柯利斯 (Collins) 词典, “Nature”的意思是:“all the animals, plants, and other things in the world that are not made by people, and all the events and processes that are not caused by people。”[14] (P1099) 很显然, 这里的“Nature”纯粹指物质世界。由此可见, 目前“Nature”的主导意义基本上是不包括人类的。 古汉语中的“自然”在《道德经》中出现了五处, 如第十七章, “功成, 事遂, 百姓皆谓:我自然”, 第二十五章,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第五十一章, “道之尊, 徳之贵,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第六十四章, “以辅万物之自然, 而不敢为”。这些章节里的“自然”指事物的本来面貌、非人为的本然状态。老子主张清静无为, 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 反对对万事进行过分的干预。这跟英文中的意义 (2) 有相似之处。 事实上, 古汉语中并不存在单独指代物质世界的词, 因为“相信天人合一思想的中国文化从未把天地万物视作独立于人的客观对象, 也从未将这个客观的存在者领域统一命名为‘自然’”。[15] (P105) “天”可谓最接近英语中“Nature” (物质世界) 的对等语, 但“天”与“Nature”存在本质区别。“天”即可指现实存在的物质世界, 也可指代这个世界的最高主宰, 古汉语并没有像西方传统那样区别物质世界与超验世界。汤一介认为, “天”在中国历史上有多种含义, 归纳起来至少有三种: (1) 主宰之天 (有人格神义) ; (2) 自然之天 (有自然界义) ; (3) 义理之天 (有超越性义、道德义) 。[16] (P6) 安乐哲 (Roger Ames) 曾如此比较西方的“上帝”和中国的“天”:“圣经中的上帝, 经常用来指代‘天堂’, 创造了世界, 但是古典汉语中的天就是世界, ……天既是世界是什么, 也是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天既是创造者也是存在的万物。在秩序本身和秩序的制定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2] (P46~47) 蒙培元也指出:“天不是上帝, 也不是绝对超越的精神实体, 天是自然界的总称, 但是有超越的层面。其‘形而上者’即天道、天德, 便是超越层面;其‘形而下者’即有形天空和大地, 便是物质层面。但在中国哲学中, ‘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不是分离的两个世界, 而是统一的一个世界。不能说, ‘形而上者’是天, ‘形而下者’不是天。事实上, ‘运而无形’之道是天, 那‘苍苍者’也是天。”[17] (P3) 由此可见, 在西方概念中的“自然”引入中国之前, 中国人还不习惯将物质世界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进行观察;由于“天”本身具有的神性意义, 中国人对天甚至怀有膜拜和敬畏之心。 2.“Science”与“格致” 中文“科学”一词译自英语“Science”, 用法也与“Science”基本相同。但19世纪之前, 英语中更通用的表达是“Natural Philosophy”。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代表了西方机械论自然观的确立。近代科学的创始人之一牛顿认为, “物质的世界是被精巧设计出来的巨大机械装置, 服从于无比美妙的运动规律”。[10] (P77) 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卡普拉曾如此评价近代科学的另一创始人笛卡儿:“笛卡儿认为, 物质世界是一部机器, 自然界根据力学原则而运动, 物质世界中的一切现象均可以根据其组成部分的排列和运动加以解释。这一机械论的自然观, 成了后来科学的主导范式。直到20世纪物理学急遽变化之前, 各门科学均在其指导下观察现象和总结理论。笛卡儿奉献给了科学界一个基本框架, 就是把自然看作是一台完美的、被精确的数学规则控制着的机器。”[18] (P46) 显而易见, 这种机械论自然观与中国传统的有机自然观有着天壤之别。 西方“科学”概念引进到中国属于旧瓶装新酒。有学者认为:在中国, “科学”一词似早在北宋时期编纂的文献中就已出现, 但西学东渐之前该词出现的频率并不高, 即使出现, “科学”一词多指“科举之学”, 偶尔也可解作“分科之学”, [19] (P187) 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Science”的区别很大。大量史料表明, 英语“Science”最初引进中国时被译为“格致”。“格致”是儒家“格物致知”概念的缩写。格物致知的目的, 是为了能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水平。宋代儒学家们对其内涵进一步挖掘, 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即物穷理”的思想, 成为文人们探究世界的最主要方式。明末清初时期, 徐光启和利玛窦一起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这表明中国自明末清初就已经开始学习西方古代自然科学。但在使用“科学”以前, 中国一直是用“格致”或“格物”来表示西方自然科学。胡适认为“格致”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类似于培根提出的归纳法在中国的启蒙, 但他同时也指出:由于宋代哲学家们并未就此提出具体的试验方法, 而且他们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在人间世界而非自然界, 所以未能促进科学的诞生。换句话说, “他们具有科学精神, 而找不到科学方法, 甚至采集标本并分类这样的方法也没有。唯一的方法是观察和内省”。[20] (P196) 由此可见, 中国传统的格致学和西方科学是大相径庭的。 3.“Nature”“Science”两个概念的正式引进 19世纪已经有一些学者认识到格致和科学的区别, 并有广泛的讨论。到了20世纪初, 中国逐渐吸收了西方“天人两分”的科学自然观, 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帮助引进西方的“自然”概念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天演论》是严复依据托马斯·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翻译成汉语的, 这本书是宣传达尔文自然进化论思想的重要著作。作为学贯中西的严复, 洞察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与西方观念的本质差异。在1903年出版的《群学肄言》中, 他以“谨案”和“译者注”的方式对中国的“天”字做了如下说明: 中国所谓天字, 乃名学所谓歧义之名, 最病思理而起争端。以神理言之上帝, 以形下言之苍昊。至于无所为作而有因果之形气, 虽有因果而不可得言之适偶, 西文各有异字, 而中国常语皆谓之天。如此书天意天字, 则第一义也;天演天字, 则第三义也, 皆绝不相谋, 必不可混者也。[21](P124) 通过与西方观念的比较, 严复认识到表示神理、形下、因果之形气这三个方面的意义, 在西方各有不同的词汇, 而中国的“天”字则同时包含了这三个方面不同的意义, 即“天意” (神) 、“天演” (自然性及其因果关系) , 还有“苍昊” (自然界、自然) 。尽管严复对“天”的含义进行了区分, 但由于当时汉语中还没有用“自然”指代物质世界, 严复不得已而用“天”这个最切近的对等语来指代达尔文笔下的“自然”。有学者指出:作为西学东渐的代表性人物, 严复在科学和进化的视域下对古代中国“天人”观念进行了重构。在很大程度上, 严复过滤掉了古代中国“天”观念的“神性”, [21] (P124) 由此成为引进西方“自然”观念的先锋人物。通过翻译《天演论》, 严复实际上是将由达尔文代表的西方社会看待物质世界的视角引入中国, 即帮助中国人以博物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界。[22] (P156) 现在汉语中的“自然”, 即科学意义上的自然, 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 最早于1926年出现在中国关于西方哲学的一本词典里, 对“自然”的解释是: (1) “文明”“文化”和“技巧”的对立面; (2) 实际存在的总和, 与“精神”和“历史”相对立。可见, 这里的“自然”概念已完全遵循西方二元对立的观念。而这种对“自然”的新定义是随着当时席卷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和民主狂热流传开来的, 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更是如此。“自然”现在变得具体、客观, 完全成为科学分析的对象。[23] (P323) 西方“自然”概念的引入让中国人觉得物质世界不再那么神秘, 而是与人相对立的客体, “世界的祛魅”由此开启。 随着“科学”的机械论观念被正式引入中国, 自然完全变成了需要被征服的对象。中国将“Science”译为“科学”是受日本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 大力译介西方的科学技术, 汉字“科学”一词开始被不少日本学者使用。吴国盛认为, 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列出了《科学入门》和《科学之原理》两书, 大概是“科学”这个词作为英文“Science”一词的汉译首次出现在中文文献中。严复在1900年之后也开始使用“科学”来译“Science”。此外, 梁启超、王国维、杜亚泉等人开始频繁使用“科学”一词, 示范作用很大。特别是杜亚泉于1900年创办并主编了在当时影响非常大的科学杂志《亚泉杂志》, “科学”一词从杂志创刊开始就成为“Science”的定译。1912年, 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下令全国取消“格致科”。1915年, 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等人创办了影响深远的杂志《科学》。从这一年开始, “格致”退出历史舞台, “科学”成为“Science”的定译。[24] (P127~128) 艾尔曼 (Elman) 通过统计数据证明, 1902至1905年, “科学”与“格致”使用频度大体相当, 但1905年后, “科学”的使用频度开始高于“格致”。[25] (P103) 三、“Nature”“Science”两词译入中国后的影响 “Nature”“Science”两个西方概念译入中国,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看待和对待物质世界的方式, 不仅让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彻底边缘化, 而且对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1. 科学文化取代儒教文化, 自然被视为征服的对象 随着中国人开始吸收西方“自然”的观念, 二元对立的自然观也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自然被彻底地客体化, 为科学文化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基础。当时积极引进“科学”概念的一批学者相信:科学可以帮助中国人穷尽自然的奥秘, 而只有征服了自然, 中华民族才能实现复兴。这在1923年著名的“科玄之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科学派的典型代表胡适认为, 西方精神文明的发达是因为物质文明的发达, 中国的复兴必须要大力发展科学。科学也是追求真理的唯一正确途径, 而真理可以将人们从压迫的环境中解脱出来。胡适这样写道: 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人生世间, 受环境的逼迫, 受习惯的支配, 受迷信与成见的拘束。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 使你强有力, 使你聪明圣智;只有真理可以使你打破你的环境里的一切束缚, 使你戡天, 使你缩地, 使你天不怕, 地不怕, 堂堂地做一个人。[26] (P254) 他又说:“自然 (Nature) 是一个最狡猾的妖魔, 只有敲打逼拶才可以逼她吐露真情。”[26] (P255) 胡适很自豪地宣称自己信奉“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27] (P15) 他认为生活是要与自然环境斗争, 而不是寻求与自然和谐相处。很明显, 胡适主张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不再信奉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 “科玄之争”的结果完全有利于“科学派”, 西方的科学文化得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据调查, 1923年的辩论实际上给科学做了很好的宣传, 将科学提到一个很高的程度, 从此以后科学这个术语被普遍用于一些积极的思想潮流中。”[28] (P17) 韦勒 (Weller) 也指出:“20世纪20年代, 自然被看作供人类使用的一个客观物体。在五四时期被理想化的‘赛先生’, 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超过了其他任何思想, 超过了中国的有机自然观。”[29] (P61) 从此科学文化取代了儒教文明, 科学被尊崇为改变世界的有力武器。孙中山也曾说过:“今天, 随着科学的蓬勃发展, 我们终于知道人可以征服自然。”[22] (P351) 2. 追求物质文明成为中国人新的幸福观 毫不夸张地说, “自然”“科学”两个西方概念的引进不仅从根本上撼动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 而且也彻头彻尾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 倡导修身养性的“对内发力”, 要“存天理, 灭人欲”, 并不主张“对外发力”, 即从对物质世界的征服中获得成就感。中国传统的幸福观认为:只要人类有基本的生存手段就是幸福的, 物质财富与幸福没有太大的关系。20世纪美国著名汉学家卜德 (Bodde) 认为, 现代科学没有起源于中国的根本原因是中西方定义幸福的差异: 在西方, 幸福就是利用自然的力量增加人类物质享受。相反, 在中国, 圣人就是遵循宇宙中的规则, 从而获得他所认为的真正的幸福。这个概念在中国广为接受, 进一步解释了即使在贫困和简陋的条件下, 为什么无论是受过教育的人还是文盲都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状态, 而这些于西方人而言, 是不能忍受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人的字典、历史、百科全书及其他学术著作中都记载着一些显著的、发达的科学技术, 却没有形成物理科学的原因, 因为中国人没有将这些技术运用到自然界中。[30] (P295) 但随着科学文化在中国地位的牢固树立, 中国人征服物质世界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 传统的追求修身养性的人生观和幸福观逐渐被边缘化。 “天人合一”这个具有独特生态价值的人与自然关系之建构曾经主宰了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 但在20世纪初, “Nature”和“Science”两词的译介标志着西方当时盛行的机械论自然观从此植根于中国, 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有机自然观, 由此也动摇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和幸福观, 西方自然及科学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科学和技术的联姻大大提高了中国人干预和改造自然系统的能力, 工业文明逐渐发展, 物质财富与日俱增。但与此同时, 自然环境也一天天恶化。如今, 中国同西方一样, 也不得不面对由于毫无节制地开发自然、改造自然而带来的环境危机的巨大挑战。中国目前的生态危机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20世纪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全盘西化可以说是罪魁祸首。在生态危机日益恶化的今天, 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而如何在谋求绿色发展的同时, 从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中吸取生态智慧, 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3, (1) . [2]Ames, Roger T., and Henry Rosemont, Jr..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M].New York:Ballantine Books, 1998. [3]White, Lynn.Jr.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A].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C].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4]王正平.“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生态伦理价值[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5, (3) . [5]Novak, Phillip.How?Asian Religions and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J].Revision 1993, (2) . [6]Bruun, Ole.Fengshui and the Chinese Perceptions of Nature[A].Richard C.Foltz.Worldviews, Religion, and the Environment:A Global Anthology[C].CA:Wadsworth Publishing, 2002. [7]Snyder, Samuel.Chinese Traditions and Ecology:Survey Article[J].Worldviews:Environment, Culture, Religion, 2006, (1) . [8] 卢风.人、环境与自然——环境哲学导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9]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0]王正平.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4. [11]钱逊.也谈对“天人合一”的认识[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4, (3) . [12]William, Raymond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M].Revised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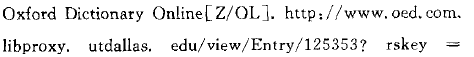  [14]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15]吴国盛.什么是科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16]汤一介.论“天人合一”[J].中国哲学史, 2005, (2) . [17]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18] 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19]周程.“科学”一词并非从日本引进[J].中国文化研究, 2009年夏之卷. [20]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 (英汉对照)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21]王中江.严复的科学、进化视域与自然化的“天人观”[J].文史哲, 2011, (1) . [22]Pusey, James Reeve.China and Charles Darwin[M].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23]   [24]吴国盛.现代中国人的“科学”概念及其由来[J].文史哲, 2012, (1) . [25]Elman, Benjamin.为什么Mr.Science中文叫“科学”[J].浙江社会科学, 2012, (5) . [26]胡适.胡适文集·第2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 2013. [27]Wang, Jessica Ching-Sze.John Dewey in China:To Teach and to Learn[M].Albany, 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28]Kwok, D.W.Y.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M].New York:Biblo and Tannen, 1971. [29]Weller, Robert P.Discovering Nature: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0]Bodde, Derk.Dominant Ideas i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42, (4) .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