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靳雷:用别人的故事感动自己
我曾经参观过一个村里的陈列室,竟然还有讲解员!当然是村民。水平不能苛责,背诵痕迹不是一般地重,而且还没背熟,口音就更别提了。所以,参观者也不被吸引,散漫得很。
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讲解员哭了。
我们还以为她是为自己不尽人意的讲解懊恼呢,仔细一问,还真不是。随着讲解的深入,她被曾经在这里战斗的先烈们的事迹感动得流下热泪!一个连词也背不熟的讲解员,完全沉浸在她所讲的故事里,自己先感染了自己。
说了这么多,是想说,这次,让我来当那个讲解员吧,讲几个感动我的央广故事。
我来央广的时候,大家还自然地把央广称作中央台,办公地点还在前面的那幢老楼里,编辑们兢兢业业地手写稿件,为了让播音员看清楚,一笔一画。
错字多了,会重抄一张。阿拉伯数字要改成中文,方便播音员读,不用现场反应。有些句子,编辑们还不嫌麻烦地加上“了呢吗”之类的语气词,为了读起来更像口语。
有主持人好心地说,这些都别改了,到时我们自己加吧。老编辑淡然地说,我们加了,你们就省点心,可以专心备稿。
后来我去国外培训,那里上的第一课,就是广播工作是teamwork。
我的教育背景里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但却一点不陌生,带我的老师早就告诉过我,你的稿子写得不好,再好的播音员也读不好;你的播音不好,编辑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所以,节目好,我们每个人都要好。

我的组长,四十多岁,获奖无数,但是,为了带上我们两个“小尾巴”,她还是积极组织策划节目,选题是她找的,专家是她请的,提纲是她写的,节目是她主持的,全过程除了沏茶倒水,我们只有学习的份儿,但是获奖证书上,却黑纸白字地印着我们三个人的名字。
我自己获得的第一个中国广播奖一等奖叫《死者对生者的奉献》,署名是四个年轻人。但我们都知道,其实那是我们主任的作品。我们做出了好的采访,却没有写出好的作品,她把整个作品都重写了,最后却没有加上自己的名字,成全了我们四个。
还有一位上司,我交上去的好几万字的报告,被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改过,包括标点符号。
后来,我们一起出一本书,她审过的书稿送到出版社,编辑说,这本书之所以令她印象深刻,是因为校对老师一个错都没发现。
她带着我们做活动,反反复复叮嘱我们一件事:品质。因为所有的活动都代表中央台。你心目中,中央台是什么样的,你的所作所为要称得上它。

来台以后的第一次外出采访,去的是社科院西欧所,所里的老师特别重视中央台的采访,连上他自己,一共组织了四个人,滔滔不绝一上午。
我抱着比砖头还大的采访机心满意足地回来了。那时候,做个带响儿的节目都要订机房,每个机房都配备一位录音员,由TA帮编辑合成出成品。
我的那个她一定不记得了,当时她面无表情地说出“这个录音不行,得重录”的时候,我脑子里好像有一万个雷同时炸响,人一下子就懵了。
我指着调音台上百十来个旋钮怯生生地问,难道不能调一下,把声音提高吗?她依旧神色不变:“调了,噪音就大了,不够中央台播出标准”。
没办法,我只好回办公室,打了半个小时腹稿之后,拿起电话给社科院的老师解释我没录好,所幸他啥也没问,就让我过去了。于是,我又背上采访机,骑上自行车跑回社科院。
不过,这次,就只有他老人家一位接受采访了。因为采访对象不再丰富,节目也做得兴味索然。但是从那以后,每次录音前我都会认真试音,检查表头;重要录音做备份,带耳机监听,生怕声音品质不符合中央台播出标准。

几年之后,我的职业生涯里第二次听到“你这录音不行啊”,仍旧是在机房,仍旧是一位录音员跟我说的。
我采录了一堆音响,自认为很典型、很丰富,能够成就我的作品野心。谁知,她听了几个就皱眉,说:“你这声音不干净啊,你听听人家的声音”,于是,她给我放别人录的黄河源头冰川融化的声音,一滴一滴的,每一次滴落都打在我心上。
这是一个女记者背着砖头大小的两部采访机(其中一部还是那时少见的数字采访机,她专门从器材科借出来的),带了几只话筒,在青藏高原上爬冰卧雪录出来的。除了播出的那一段,剩下的都是她沉重的喘息声……
于是我知道,有声音还不行,录出来的声音得漂亮!

入台后我听到的第一篇广播特写是讲少林寺的,当作品的结尾处,山门打开的时候,外边街道上车水马龙的声音扑面而来,和此前构造的寺庙里的清静形成巨大的反差,把我自己的灵魂都震慑到了!
声音,以不可思议的能量携生动的画面呈现在我的脑海里!原来,这才是广播的力量。
那时候,特别羡慕他们可以做到用两支话筒记录山门开合的声音,听声音从一只音箱转入另一只音箱带来的动感。
带着好奇,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也会讨论怎样录出果园里青苹果长个儿的声音;也会琢磨是否可以在野生动物园泡一整天,用声音还原一个动物世界……
必须得说,那时候中央台对声音质量的要求真是严。
记得好几位播音员都讲过,正直播呢,要加一篇稿子,编辑是跑上来的,呼哧呼哧直喘,被播音员一把摁到地上,只好蹲在地上蒙着头喘气,怕声音传到话筒里。
这样的故事也被我们讲给每一位来台直播的嘉宾,听过之后无不肃然起敬。
老楼有电梯,但是直播不让坐,怕电梯出故障,人被憋在电梯里到时间出不来。多大的专家也都被领着,走过长长的通道,爬上四层楼梯。路上,就是讲解安播纪律的时间。
结果就是,等走到直播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在电台里说上话,很神圣。进了直播间,更是大气都不敢出。
一次,一位专家想咳嗽,憋得满脸通红,绝望地看着我,马上就忍不住的样子。我用一秒钟的时间判断了一下后果后,果断地推起片花,然后把他从座位上拉起来,推出直播间,任他在走廊里尽兴地咳。

现在,我也经常带着嘉宾在台里参观,无数次在台史展上指着一张张熟悉的照片讲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袁阔成的故事、少儿广播合唱团的故事、国庆转播的故事、汶川的广播故事,等等。
有时候,我也会讲我看见的故事,因为细琐,更见专业力量,比如长达十几小时的直播,开盘带摞成小山,需要用平板车推来。
随着主持人跨越时空的讲述,要依次把这些带子上到有限的三台机器上,适时推起,再换另外三盘,如此往复,直至直播完毕。
这样的导播得算“肉电脑”了吧?脑子得清楚得令人发指,注意力还得高度集中。谁能干?每次听到这儿,来宾都会咋舌,我心里也会涌起一点小傲娇。
是的,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我的同事,卓越且敬业,做出了全中国最好的广播,一代又一代。能和他们共事,是我的荣幸。也是他们,照亮了我的职场,给工作注入意义,对未来充满期待,骄傲于自己是央广人。

作者:靳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主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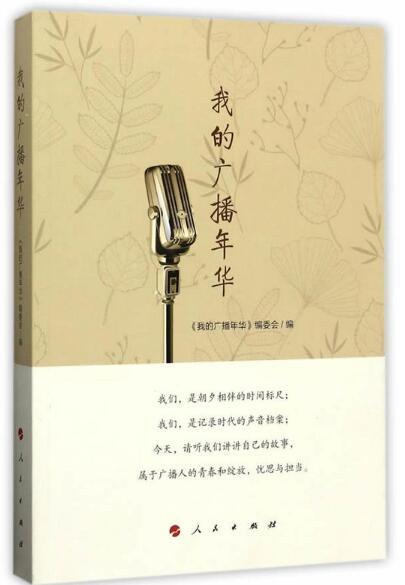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隋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