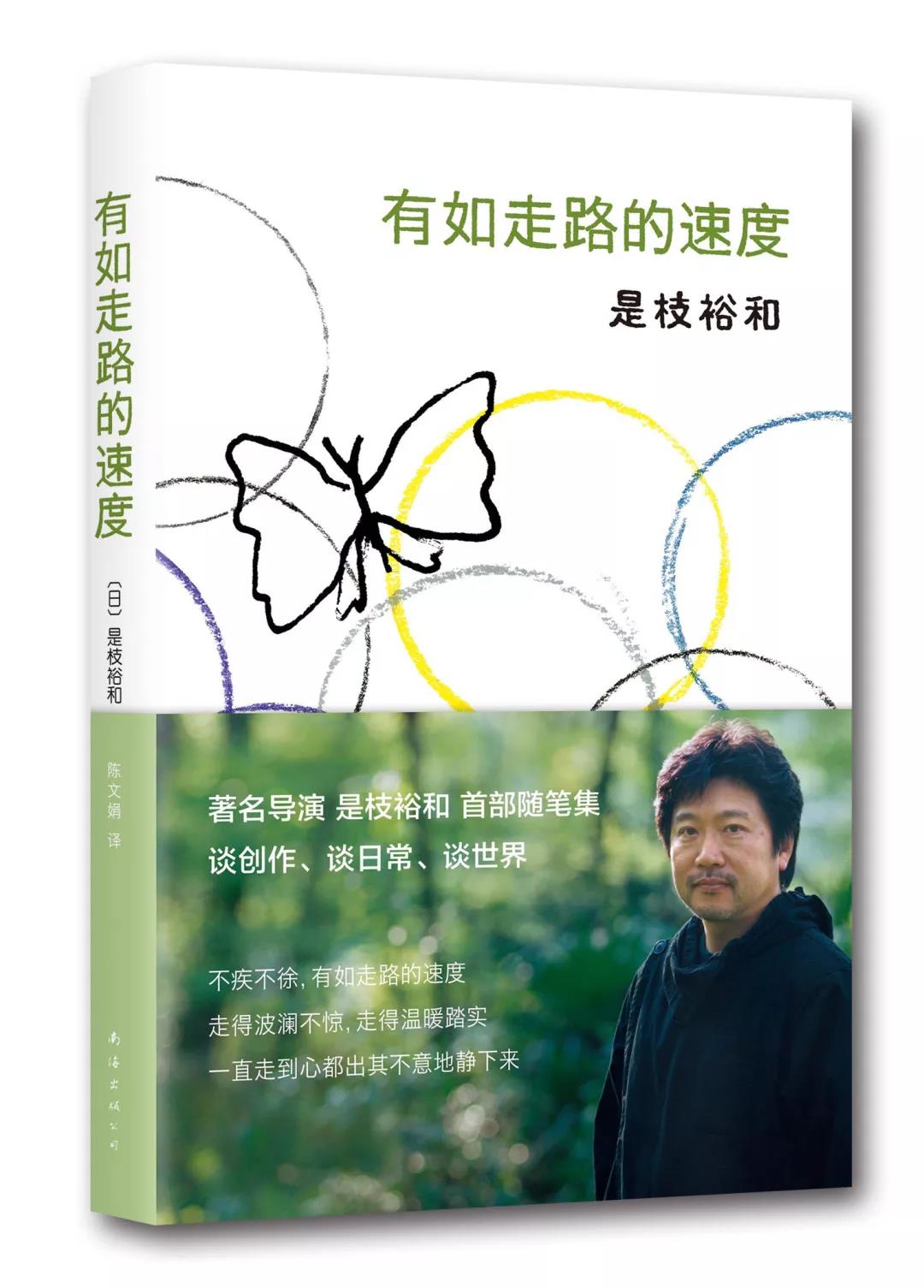 《有如走路的速度》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首部随笔集 字里行间 被书名吸引,买了一本书,《夏至将至》。 这是白水社出版的散文集,作者永田和宏先生是细胞生物学方面的权威,同时还是一位和歌诗人。文章围绕他与同为和歌诗人的妻子河野裕子的生活,记录日常点滴。书名取自永田先生知道妻子乳腺癌转移、大限将至时,所作的一首和歌。 过一日 少一日 与你的时间 夏至将至 影像和文字虽有区别,但这首和歌传达的感情和审视时间的方式,让我发现了某种自己想表达的理想形式。 散文中还有一段关于短歌的观点,虽然有点长,还请容我引用: 和歌中基本不会言及悲伤、寂寞的感受。不言明,但让读者感受到,这就是短诗的基础。所以,让读者从简短的语句中感受言外之意,是短诗成立的前提。(摘自《时间之钟》) 我想电影也应该尽量不直接言及悲伤和寂寞,而把那份悲伤和寂寞表现出来。在创作电影时,我也希望利用类似文章里的“字里行间”,依靠观众的想象力将其补充完整,让他们参与到电影中来。但如今作为前提的艺术影院陷入危机,看电影已经演变成去影城这样的大型娱乐场所“消费”的娱乐项目。面对这种现状,电影创作者不能一味唉声叹气,必须去探索怎样在这个新的场地与观众缔结关系。 讯息 讯息真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词。“请您简单谈一谈电影想向观众传达什么讯息。”宣传新电影的时候,总是反反复复被问到这个问题。真头疼,真头疼……我究竟有没有往电影中灌注什么讯息呢? 在法国的一个小型电影节上,曾有人问我:“你经常被介绍为讲述死亡与回忆的导演,我觉得并不是这样。你一直在拍‘落在后面的人’。你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了吗?” 在这位评论家告诉我之前,我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本质”。还有人对我说过:“你并不打算审判任何一个角色,这种不以善恶来区分的特点,与成濑巳喜男的电影有共通之处。” 这话让我颇为自豪。不过也是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自己为何喜欢成濑导演的电影。比起我能简单传达出来的讯息,这些评价更为深刻,深入我无意识的部分来理解作品的意图。 “诗并非讯息。讯息不过是刻意而为的东西,而诗是无意识的产物。”这是在某次座谈会上,我听诗人谷川俊太郎说的。如果作品中蕴含着称得上讯息的东西,那必定不是创作者所为,而是读者和观众发现的。 上周末,我为宣传新片《奇迹》,到仙台和福岛举办了放映会。这部电影的评价也许是我目前的作品中最正面的一部。但是(这与我上一篇所写的内容也一脉相承),我并没有说“看了以后请振作起来吧”之类的话。假如真的有讯息(勉为其难用这个词)在传递交接,那我也不是传递者,而是接收者。我是去灾区倾听还沉睡在无意识中、尚未转化为语言的声音,探究我的作品和我这个创作者置身于“现实”中时,是否还经得起考验。 世界 对你来说,电影和电视是什么? 有时会遇到这种直抵本质、难以作答的问题。 “就是交流。” 近来,我都是这么回答的。 “不是为了表达自我吗?” 对方继续追问。我不清楚其他导演的情况,但自从踏入这个行业,我就与“表达自我”这个词格格不入。 “你是那种外人琢磨不透你在想什么的人,反而从你制作的节目中看到了更多的感情。” 曾有一位初中同学这么对我说。这样看来,或许我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类似自我的东西,却借助具体的影像传达出来了。然而节目中表达的感情,只是针对某种特定的事物。 要在电影中以某种形式将感情表达出来,就需要一个电影之外、自己以外的对象。感情是借由与外在事物相遇或冲突产生的。看到眼前的风景,觉得很美,但这份美是属于我的,还是属于风景的呢?是以我为中心来看待世界,还是以世界为中心,将自己视作其中一部分?视角不一样,得出的答案会截然不同。如果说前者是西方视角,后者是东方视角,我无疑属于后者。 有句话叫“天地有情”,这是我最尊敬的台湾导演侯孝贤先生经常写在色纸上的话,我也非常认同这个理念。这样的缘分让我感动。 并非我在孕育作品,作品也好,感情也好,早已蕴含在世界之中。我不过是将它们捡拾并收集起来,然后捧在手心,展示给观众看。作品是与世界的对话(交流),是认为这种世界观谦虚又丰富,还是将其视为创作者的无能呢?这种对立自来就有。 对话 我昨天写道,作品不是自我表现,而是交流,那么今天再接着谈谈。 刚开始从事电视行业时,最常听到的要求是“要好懂”“让任何人都能看明白”。有位电视台员工甚至曾满不在乎地说:“因为观众都是傻瓜。”这是向人传达讯息的工作,自然会思考如何才能让对方认真倾听。既要选择讲述的措辞,也要考虑说话的顺序。但是,不可能有任何人都懂的作品。我觉得这些想法是对语言和影像,或者说是对交流的过度自信。也许很多人认为,电视就是把晦涩难懂的东西花五分钟解释清楚的媒介,但也有观点认为,电视要描述看似简单的事物背后的复杂性,因为世界如此复杂。正是由于无视世界的复杂,一味追求“易懂”来巴结观众(虽然并非全部),才导致了电视和电影的幼稚化,进而脱离现实。“快点明白这个味道吧”,这种大人引导小孩进步式的态度,不知何时已被视作创作方的傲慢。 那么,到底哪种态度才是认真与观众交流呢? “你要在心里想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去做。”这是我入行之初,一位前辈送给我的话。以抽象的观众为对象去做节目,难以打动任何人。不管是母亲也好,恋人也好,“像面对着一个人倾诉般去做”。那位前辈想告诉我,不要试图表现作品,而是去对话。的确,只要意识到这一点,作品就会自己打开门窗,清风自来。这股清风也会拂去我从“表达自我”中感受到的“自我终结感”。 我女儿现在三岁,拍《奇迹》时,我就想着这是等她十岁时让她观看的电影。我想对她说,世界如此精彩,日常生活就很美丽,生命本身就是奇迹。 责任 我至今仍在TV MAN UNION这家电视制作公司任职,从一九八七年大学毕业到现在,整整二十六年。我人生一半的时间都在这家公司度过。郑重其事地写成数字,实在令人吃惊。刚到公司面试时,面试官问我想制作什么样的节目,我回答想做关于自然能源的纪实栏目。对方略带嘲讽地说:“那这栋大楼最好也换成太阳能发电吧。”我答道:“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虽然是这样回答的(这正是问题所在),可我心里却明白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在幸运地(?)加入公司的第一年,我写了两份策划方案。一份关于不使用汽车与电力,在美国过着自给自足生活的阿米什人,另一份关于诞生于十二世纪的意大利,默默传教并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亚西西的方济各。有一次,一个同期入职的朋友听到我谈论不使用农药、实施自然培育法的可能性,说: “你懂什么农业?明明连地都没有好好翻过。” 他出身于山形县的农家。 虽然只会纸上谈兵,但对于核电站的危险性,我并非一无所知,因此也没有资格怒气冲冲地吼一句:被骗了!权力与企业相勾结,用钱堵上当地居民的嘴巴,请些御用学者讲讲安全性,这些手段与水俣病暴发时如出一辙。尽管如此,我终究没再写这种主题的策划方案了。不是受谁阻挠,而是主动放弃,在安全的东京尽情享受着舒适的生活。 片名我已经忘了,在一部描写虐杀犹太人的故事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男人说:“我什么都做不了,但至少我知道,这种行为是错误的。”犹太人戳穿了对方的诡辩:“比起因为无知而无所作为的人,明明知道却什么都不做的人罪孽更重。”最近,我总是反反复复想起这一幕。 关于丧 我想再聊聊死亡的话题。准确地说,不是关于“死”,而是关于“丧”。 精神科医生野田正彰的著作《服丧》,是一部讲述对日航123班机空难等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进行心理干预的纪实作品。这本书出版于二十年前,详细追述了遇难者家属接受亲人的死亡,并重新振作起来的过程,是一本非常感人、发人深省的书。其中有一句话:人在服丧时,也可以具有创造力。我的理解是,人在服丧期间(grief work)体会到的不单单是悲痛,还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成长。 这本书格外打动我其实是有原因的。在该书出版大约半年前,我在长野县一所不使用教科书,推行“综合学习”的小学进行了为期三年的采访。当时伊那小学春班从牧场借了一头母牛饲养,并定下育种和挤奶的目标。学生们从三年级开始一直照料它,但在临近五年级的第三学期,母牛比预产期早产了近一个月,老师们发现时,小牛已经浑身冰凉。学生们哭着为小牛举行葬礼后,他们盼望已久的挤牛奶的时刻来临了。小牛虽然死了,但学生们每天还是得给母牛挤奶,然后一起把牛奶加热,在午餐时喝掉。本该很欢乐的挤奶和午餐变了味道。这如实地体现在他们“服丧”期间所写的诗歌和作文当中: 哗啦啦 发出悦耳的声音 今天也来挤牛奶 虽然悲伤,还是要挤牛奶 虽然开心,却夹杂着悲伤,虽然悲伤,但牛奶依然美味,体验到这种复杂的感情,不叫成长又该叫什么? 我在日后的创作中如此钟情和迷恋“丧”而非“死”,出发点无疑就在这里。 缺陷 筹备电影《空气人偶》时,我收到了在仙台放映会上认识的一位学校老师寄来的信,信中夹着吉野弘先生的诗《所谓生命……》: 所谓生命 仅靠自身无法被完整创造出来 诗从这一节开始,描绘了世界上每一个生命之间的牵连,然后在下面这一节鲜明地点出主题: 生命自有缺陷 需要他人来填满《空气人偶》的主角一如片名,是一个塑料制成的充气人偶。一天,这个人偶有了心智,动了起来,就是这样一个奇幻的故事。电影中有一幕,人偶的塑料不小心被扎破了,泄了气,她心爱的男子用自己的气息把她吹满,于是她空虚的心灵和身体都被填满了。诗的主题和电影的主题完美契合。 人总是希望通过努力来弥补自身的缺陷。不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电影中,这种努力一直都被视为美德。但是,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能克服自身的缺陷吗?如果可以,那是否真的美好呢?这首诗似乎提醒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 我不喜欢主人公克服弱点、守护家人并拯救世界这样的情节,更想描述没有英雄、只有平凡人生活的、有点肮脏的世界忽然变得美好的瞬间。想做到这一点,需要的大概不是咬紧牙关的勇气,而是不自觉地向他人求助的弱点。缺陷并非只是缺点,还包含着可能性。如此一想,就会看到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正是因为不完美,才变得如此丰富多彩。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