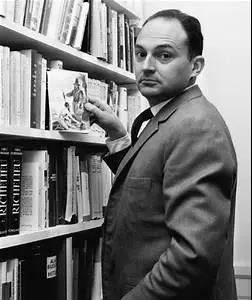 米歇尔·图尼埃是一个很容易被贴上标签的法国作家:德国、哲学、神话、寓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教育、阅读和朋友圈决定了他日后的创作路子。1924年12月19日,图尼埃出生在巴黎一个谙熟德语和德国文化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酷爱哲学和文学。在巴斯德中学,他和罗杰·尼米埃在一个班上学哲学,当时给他们上课的是莫里斯·德·冈迪拉克。之后报考巴黎高师失利,他在索邦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学位,于1945—1949年到德国蒂宾根大学继续攻读哲学,结识了吉尔·德勒兹。 图尼埃视让-保尔·萨特为“精神之父”,回国后两次考哲学教师资格未果,从此断了当哲学教师的念头,转而进入电台和电视台工作,再后来到布隆出版社当德语审稿人和译者(主要翻译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作品,或许正是《西线无战事》让图尼埃有了写作《桤木王》的灵感,用一种迥异的方式反思战争和人性)。1960年代初,痴迷摄影的他主持了一档名为“暗室”的电视节目,1970年操办了阿尔勒摄影艺术节,也是全球首个摄影艺术节。 与此同时,他进入文学圈,从读者慢慢滋养转变成作者,在写实和魔幻中找到了一条重写神话的金线。德国文学对他影响深远,歌德的诗歌,尤其是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狗年月》《比目鱼》给了他启发,用历史理性的棱镜折射出人类生存状况传奇、荒诞、恐怖的一面。这种手法和拉伯雷、塞万提斯、塞利纳也属于同一序列。 如果说图尼埃出道晚,作品数量也不算多(九部小说、几本短篇故事集),但他一出手就非同凡响。1967年伽利玛出版社推出他的处女作《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这本逆写笛福的《鲁宾孙漂流记》的作品一举夺得当年的法兰西学院小说奖,鲁滨孙和礼拜五作为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身份被掉了个个,和笛福的主人公相反,鲁滨孙放弃了把荒岛改造成英伦文明的袖珍模型的野心,开始欣赏荒岛的原始之美,故事最后,礼拜五选择离开荒岛,而鲁滨孙则决定留下。在1971年青少年版的《礼拜五或原始生活》中,这种回归自然的倾向变得愈发直白。在1978年短篇小说集《松鸡》中图尼埃还构思了另一种尾声“鲁滨孙·克鲁索的结局”:在海上失踪了二十二年后,鲁滨孙“蓬首垢面、胡子拉碴、野里野气”地回到了家乡,还带回了一个黑人。他做生意赚了钱,娶了年轻漂亮的太太,回到了生活正常的轨道,但一年年过去,“确实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内部暗暗腐蚀着鲁滨孙的家庭生活”。首先是礼拜五开始酗酒闹事,之后搞大了两个姑娘的肚子,最后被大家以为他偷了邻居家的钱财跑路了。鲁滨孙认定礼拜五回荒岛了,而他也越来越怀念那段青枝绿叶、鸟鸣啁啾、虽然不见人烟却阳光灿烂的日子。他租了一条帆船出海去找他的乐土,但乐土仿佛被海水吞噬了,再也找寻不到。荒岛一直都在,一个老舵手说,只是它变了,变得鲁滨孙不认识它了,而鲁滨孙也老了,老得连他的荒岛也不认识他了。这个故事的寓意或许在于:离开大陆,你可能会被文明抛弃,离开荒岛,你可能会被自然抛弃。在两难中,是双重的弃绝,是现代人精神无处栖居的虚无缥缈境。 顺便要提一句的是,改编后的青少年版《鲁滨孙或原始生活》成了法国中学语文的必修篇目,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用作家自己的话说是一笔足以让他养老的“年金”。他心目中的文学典范是福楼拜的《三故事》,纯粹的现实主义手法,却弥散出令人难以抗拒的魔力。自称“哲学走私贩子”的图尼埃最擅长的,也就是在小说和故事中“变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康德的哲学思想,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做蓝本,通过新的演绎(常常是颠覆性的),让它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熟悉的故事于是有了陌生的距离,这个距离让我们重新看到镜子中或扭曲变形或真实还原的历史,还有自己。 1970年图尼埃出版的第二本小说《桤木王》借用的是歌德于1782年发表的那首神秘的同名叙事诗: 是谁在风中迟迟骑行? 是父亲与他的孩子。 他把孩子抱在怀中, 紧紧地搂着他,温暖着他。 “我的儿子,为什么害怕,为什么你要把脸藏起来?” “父亲,你难道没有看见桤木王,头戴王冠、长发飘飘的桤木王?” …… 这部以二战为背景的警世小说讲述了汽车修理库老板阿贝尔·迪弗热一段带着宿命诡异色彩的经历:他在二战中应征入伍,嗜血的魔鬼本性得以淋漓发挥,这种魔力使他最后成为纳粹政训学校卡尔腾堡的“吃人魔鬼”。主人公阿尔贝曾经见到一具古尸,由于埋在泥潭里没有腐烂,那具古尸被命名为桤木王。当二战接近尾声,苏军攻入德国本土,希特勒穷途末路,卡尔滕堡的陷落指日可待。阿尔贝在尸横遍野的普鲁士土地上救下一名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出来的犹太男孩,他将这名弃儿背在肩头逃进长满黑桤木的沼泽。和传说中的桤木王一样,阿尔贝也沉入了泥炭沼,沉入了永恒的黑暗。当他最后一次仰起头,“只看见一颗六角的金星在黑暗的夜空中悠悠地转动”。小说以史无前例的全票通过摘得龚古尔奖,两年后,图尼埃自己也进了龚古尔学院,成了该奖的评委,一直到2009年退出(理由是年事已高、疲惫、没有胃口,为了不辜负好书和美食),这期间也有过被批评甚至被扔西红柿的尴尬经历。2006年,当乔纳森·利特尔的大部头《复仇女神》横空出世时,米歇尔·图尼埃和达尼埃尔·布朗热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龚古尔奖颁给一部写纳粹主义的小说(《桤木王》)就够了,后来有人在拍卖的名人手稿中发现了图尼埃的一封信:“我劝您不要选《复仇女神》,这本书很沉重,令人悲痛。我投票给了史岱凡·奥德纪的《独生子》,这是一部杰作。”或许《桤木王》的作者担心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而他的假想敌利特尔则摆出一副“书记员巴特尔比”的高冷腔调,说自己不喜欢文学奖,“这个奖,我千方百计想逃避,不幸的是,他们还是把它给了我……我不想要这个奖……我不认为文学奖可以和文学相提并论。文学奖可以和广告、营销相比,但和文学不可同日而语。” 图尼埃此后的作品《流星》(1975)《皮埃尔或夜的秘密》(1979)《加斯帕、梅尔基奥尔与巴尔塔扎尔》(1980,青少年版《三王》)《吉尔和贞德》(1983)《金滴》(1985)《七故事》(1998)等多数也都或多或少带着重(改)写的痕迹:圣经故事(摩西、三王)、贞德、蓝胡子、小拇指……没做成哲学教授的小说家一辈子都在用“新寓言”的方式去思索存在和虚无:“我们越往时间迈进,过去将离我们越近。”他最不能忍受的是那“像潮水一般突然在世界上汹涌澎湃、似乎要淹没世界的庸俗以及平淡”。或许还有年老,2010年5月19日他回答《快报》记者玛利亚娜·巴约时说:“我不会自杀,但我觉得我已经活得太久了。我深受年迈之苦:什么事都不做,不再旅行。我感到无聊。”不疯魔,不成书,不疯魔,不成活。 当作家去世的消息传开,贝尔纳·毕沃在Twitter上发消息:从明天开始,当别人问我“谁是法国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我再也不能回答“米歇尔·图尼埃”。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