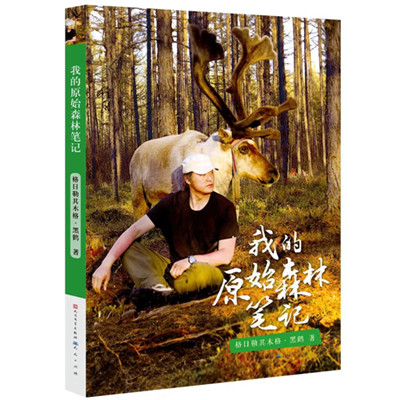 那天我丢失了一块相机的电池。 还好,我的相机有三块备用电池。即使如此,我仍然需要它,外出的时候,在森林里永远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电池备足。 随后,营地里又莫名其妙地丢失了一些东西,芭拉杰依刚刚用过之后放在床铺上的顶针,还有盐罐的盖子、小镜子、小刀、打火机,都不见了。而在我这里,除了那块电池,还丢失了一根登山鞋的鞋带,我实在无法在营地里找到一根细到可以穿进鞋扣眼里的绳子,没有办法,我只好找了一根细铁丝暂时充当鞋带。 我无法从这些丢失的东西里寻找到任何线索,这些丢失的东西显然无法分类,无法从中了解到盗窃者的兴趣取向,我不得不认为这是恶作剧。 但在营地里,只有三位老人。他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每日只是以融入山林般的恬静面对这个世界,这种恶作剧式的幽默显然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 一开始我怀疑是营地里的驯鹿,但我很快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这世界上能够吸引它们做出偷窃举动的无外乎就是食物和盐,其他东西在它们的眼里就与树和石头无异,不能进嘴的东西它们绝对不会感兴趣。 随后我又将目光投向那些总是像风一样从营地前的空地上一掠而过的花鼠。它们的嫌疑确实很大,但据我多年在林地里的经验和对它们的了解,也将它们的嫌疑排除了。它们对于更富于禁锢性质的人类的居所总是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它们会在帐篷附近寻找食物,但绝不会进入帐篷行窃,它们缺少那样的勇气。 然后,我又开始怀疑是营地里的狗,但结论同样是不可能的。两只老狗已经老眼昏花,它们懂得营地里的禁忌,除了恪尽职责,不会做出这种监守自盗的事来。而那只年轻的牧羊犬是我带上山的,它只对肉感兴趣,其他东西在它的眼里就是天上的浮云。至于我带上山的依玛,我太了解它了,对于电池这种东西,它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的。 我努力进行各种推测。 我也开始怀疑那些每天上午准时在营地里出现的蓝大胆,这些学名叫作普通的灰蓝色的小精灵。它们总是在上午九点左右跟随着越过山脊的温暖阳光一起出现。它们的速度太快,更像是灰蓝色的光,而当我看到它们的时候,不过是因为它们为食物所吸引,停留下来的片刻,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看清它们的身影。在营地里,它们永远受到欢迎,它们从挂在帐篷高处的肉干上啄取油脂,毫不顾忌地飞落在芭拉杰依的头上和身上,从她的手中叼取葵花子。它们如此高频率的动作确实需要大量的能量,它们也因此验证了自己蓝大胆的美名。它们已经习惯了使鹿鄂温克人的营地,总是伴随着阳光一起出现,即使营地搬迁,它们也总是可以尾随而至。我也试着在手里拿着葵花子喂它们,但显然,它们对我心存疑虑,还不能完全地信任我。它们总是叼起食物,快速飞离,从不停留。也许,它们可以感觉到我内心的想法。我确实有把它们抓在手里好好研究一下的计划,想仔细查看它们身上的羽毛。也许这个稍纵即逝的念头还是流露出什么迹象,让它们无法完全地信任我。说到底,它们显然没有运载备用电池的能力,我想以它们的能力,能够运载的最大的东西也就是一块直径不超过三厘米的肉块了。 总之,一切看起来都非常蹊跷。 每次上山都让我身心放松,放倒枯树再独自扛回来,用斧子劈成柈子,这种枯燥的工作也会让我欣喜不已。但这次,我感觉总是生活在猜疑之中。我开始怀疑一切,一头恰巧从帐篷门口走过的驯鹿随便向里面看了一眼,发现我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它,我想自己专注的表情让它备感诧异。显然,在营地里它还从来没有见到人类用这种目光看一头驯鹿。它惊跳着跑开了。 而我也注意到,没有了备用电池之后,我发现周围的世界满是稍纵即逝的美景——清晨挂满露珠的蛛网,刚从林间归来头顶着鸟巢的驯鹿,甚至还冒着热气的驯鹿粪,用后蹄为角搔痒的小鹿。总之,此时我认为一切都是永远不会出现的场景。而没有了备用电池,这些美景也就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真相早晚会露出水面的,否则就只能成为谜案,而安静的驯鹿营地,并不具备造就谜案的条件。 这天我起得很早,上山去寻找走失的驯鹿,回来的时候已经下午,感觉很累,吃了东西直接就躺下睡了。 我是被什么惊醒的,睁开眼,正好透过敞开的帐篷门看到那个无声潜入的小小的影子。 它轻快地跳动着,每跳动几下,就会停下来,转动着灵巧的头四处张望,当确定无人注意它的行踪时,才再次跳动着接近帐篷。 我仍然躺在床上,半眯着眼睛,装作仍在熟睡的样子。 它跳到了帐篷的门口,显然在第一刻就发现了我,它呆住了。 它的存在已经不再无形,所以对于它来讲偷窃显然也就显得没有必要了。它被发现了。 它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恐惧,没有尖叫着落荒而逃。 如果鸟可以思考,那么我想它正在思考,究竟如何面对这一切。 它僵立在当地足足有一分钟。 有四十秒钟的时间,它在死死地盯着我,它在观察我的眼睛,显然试图发现这是否是一个骗局。我一动未动,并且努力使自己的呼吸更为平稳。 最终,它确信我已经熟睡。 它跳进帐篷,开始在里面巡视。放在案板上切肉的小猎刀引起了它的注意,它试着叼了一下,但无论是扁平的刀刃还是圆滑的桦木柄都无法让它下口,它放弃了。随后,它又发现了桌上的一根蜡烛,这种莹润的白色让它颇为青睐,但它刚刚试着叼起就放弃了,显然蜡烛绵软油腻的质地不合它意。它甩动着头,在地上擦去喙上的残留物。 然后,它的眼睛突然间闪亮了,它看到了什么。 它加快速度,几个蹦跳蹿到另一张床边,随后轻轻一个弹跳,几乎没有扇动翅膀,就落在另一张床上。 它目不转睛地注意着什么,我努力在不发出声音的前提下微微地侧了侧头。 噢,它的乌托邦,它的雅典娜,它的新大陆,它找到了自己的珍宝。 它满怀爱意地盯着那个物件,床上放着我的尼康相机的镜头盖。 因为今天钻过几次灌木丛,相机上有草屑和灰尘。睡觉前,我仔细地擦拭着自己的相机,清理了镜头,擦完之后,显然,我忘记了盖上镜头盖,它就留在那里了。 一旦决定,它的行动是毫不犹豫的,转瞬之间就叼起镜头盖,展翅飞出了帐篷。 我这才警醒,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装睡,呼号一声,跳起来跟着冲了出去。 我想,它也确实受了惊吓,没有想到突然在背后有这震天动地的响动。 我如此诡异的叫声惊动了营地里的狗,它们也应和着发出狂乱的吠叫,而那些受惊的驯鹿,则撒开四蹄在营地里往复奔跑。 混乱中,我拎起一把小斧头,冲着已经飞向半空中的那斑斓的影子扔了过去。 斧子在空中旋转着,对于一只鸟儿这样的目标,斧子显得太沉重了,斧子柄从它的翅膀边轻轻地掠过。 它发出一声如裂帛般嘶哑的尖叫。 是一只松鸦。 当天下午,我就用一块风干肉在帐篷前布下一个陷阱。用木棍支起一个纸箱,——也许用筐之类的东西效果更好,但营地里没有这东西——木棍上用绳子拴了肉,放在纸箱下面。只要贪嘴的松鸦啄食这块肉,就会被纸箱扣在里面。这几乎是简单得有些弱智的陷阱,但有时候就是这种陷阱往往会最起作用。 下午它并没有来,而那块肉,也被营地里的狗叼走了。 第二天,我稍稍改进了一下,将纸箱放在货架子上,这样,狗就没有办法偷食作为诱饵的肉了。 这次,我选了一块更大的风干肉,肥瘦相间,被萦绕于帐篷上的烟熏得恰到好处,棕红色的肉闪烁着诱人的油汪汪的光泽。我想,它是无法禁受这种诱惑的。我在纸箱下摆放这块诱饵时,营地里的三只狗站在我的身边,傻子一样死死地盯着这块肉。我大声呵斥,终于将它们赶走了。 也许这应该算是称不上惊喜的惊喜。 我刚刚进了帐篷不到半个小时,就听到外面的货架子上一阵扑通扑通的响声。 …………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