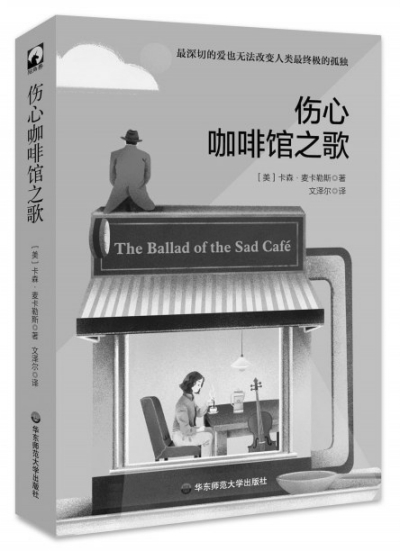 《伤心咖啡馆之歌》,[美]卡森·麦卡勒斯著,文泽尔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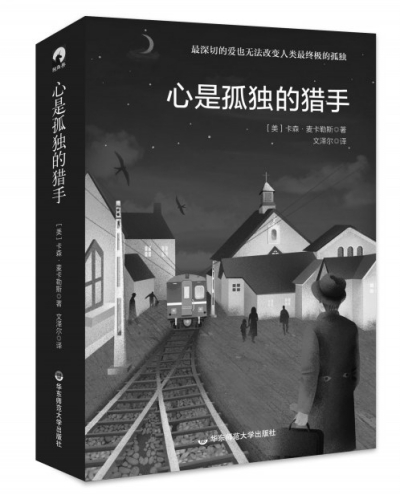 《心是孤独的猎手》,[美]卡森·麦卡勒斯著,文泽尔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福克纳到麦卡勒斯,从《真探》到《三块广告牌》,南方从未消逝。 最近,由马丁·麦克唐纳一手编导的剧情片《三块广告牌》在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评选中惜败于吉尔莫·德尔·托罗的《水形物语》,七项提名在手,却只有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和山姆·洛克威尔斩获最佳女主与男配,不可谓不让人惋惜。 麦克唐纳出生于伦敦南部的坎伯威尔,十年前便以长片处女作《杀手没有假期》挑战过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那是一部非常不南方的片子,有着盖里奇式的英国风格,兼具少许西部情怀,拍摄于布鲁日。话虽如此,里面却有个相当麦卡勒斯的畸人形象:由乔丹·普林蒂斯饰演的侏儒吉米。在《杀手没有假期》的这部分元电影性质情节当中,侏儒吉米的身份是来自美国的特型演员,最终以荒诞剧般的夸张形式为影片收了尾。《三块广告牌》中,凭借HBO剧《冰与火之歌》闻名全球的“在世最知名侏儒演员”彼特·丁拉基饰演钟情麦克多蒙德女士的侏儒詹姆斯,他的欺瞒行为同样决定了整部片子的结局定调。 麦克唐纳剧本的“南方”源自麦卡勒斯小说(而不是福克纳、奥康纳甚至韦尔蒂)。对于熟悉《心是孤独的猎手》和《伤心咖啡馆之歌》的读者们而言,这个论断几乎无可辩驳。 在美国南方文学的流变中,麦卡勒斯固然具有代表性,但却并非拥有绝对历史地位的人物——换言之,在众多美国文学史研究者们的长名单中,麦卡勒斯一定位列“南方前二十”,但未见得会在“南方前五”中出现。对于美国南方文学而言,她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其所营造的文学氛围的独特性上:小镇畸人、孤独、成长、爱的破灭与消费主义,兼带对资本社会和黑奴旧制的朴素抵制。这其中最常被世人所提及的,毫无疑问就是孤独,仿佛一提及麦卡勒斯的文字,就注定与孤独相伴似的。然而,世人对麦卡勒斯的最大误解,却也正在于此。且不提屡屡见诸报端的对《心是孤独的猎手》一书的捏造引用,将各种提到“孤独”二字的造作句子打上“卡森·麦卡勒斯”的名头,甚至谈卡佛作品的孤独、聊伊恩·麦克尤恩的孤独也一定要扯上麦卡勒斯作伴,这就显得很荒谬了。 《心是孤独的猎手》整本书译成中文接近三十万字,连同书名,“孤独”这个词总共只出现过十七次,大部分都是作为心理描写,或者形容某项具体事物比如“黑人音乐”时才出现。《伤心咖啡馆之歌》里的“孤独”则更少,只有四个,作家以旁白身份泛泛讨论爱情便用去了两个。 麦卡勒斯式孤独,与卡佛或者布考斯基的做派截然不同,既不简洁也不肮脏,仿佛某种无形压制所带来的难以挽回的后果。麦式孤独的标志作品《心是孤独的猎手》的雏形《哑巴》是自1937年起开始创作的,1940年由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伤心咖啡馆之歌》则完成于1941年。等到《婚礼的成员》时,这种孤独感开始发生转变,在田纳西·威廉斯大名鼎鼎的联合改编作用下,1946年舞台剧版《婚礼的成员》甚至呈现出难以想象的热闹氛围。 为什么?文学评论家们早就列出了各不相同的答案。作为麦卡勒斯三部著作的译者,我更倾向于将她的三部战时作品(除上述两部代表作外,尚有《金色眼睛的映像》)置于整个美国南方文学体系中去审视:战争,素来就是南方文学的发展节点。美国内战前的南方文学悠闲而幽默,南北战争后,因为南方的失败,逐渐转变为带有强烈批判现实意味的严肃风格。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南方文学的复兴,故事主体回归小镇故事,但即便如舍伍德·安德森的那部《小城畸人》(即《俄亥俄,温斯堡》),其精神内核也仍旧“危险地悬置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爆发,南方文学才狂飙猛进般地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从1938年到1945年,这一时期陆续出现了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和纳撒尼尔·韦斯特的《蝗虫之日》等具有指标意义的南方文学巨作。麦式作品也对弗兰纳里·奥康纳《智血》和杜鲁门·卡波特《别的声音,别的房间》起到了启示作用。至于“战时”对小说所起到的作用,恰如日军偷袭珍珠港对爱德华·霍珀创作《夜游者》所起的作用:这幅完成于1942年的画作描绘的是深夜空无一人的街道(原型来自纽约西村),夜间经营的餐厅内围坐着三位客人,以及一个似乎是穿着水手服装的吧台侍应生。餐厅有着如航母舰桥般的硕大窗户,但却找不到进入的门。四个聚在一起的角色,彼此之间既没有对话,也没有眼神交流,简直像被某个如前所述的“无形压制”给笼罩住了。霍珀的《夜游者》拥有如同穿着宇航服独自飘浮在太空中一般的孤独感,它或许正在倾诉那个决定性的时刻:美国对日本宣战的时刻。在《心是孤独的猎手》中,那恰恰也是小说收尾时的定调——万籁俱寂,比夫·布兰侬“用食指弹了弹自己的鼻子。广播里现在突然说起了某种外语。他无法确定那声音究竟是德语、法语还是西班牙语。但那语气听起来像是在宣布噩耗。光是听那声音,都令他感到瑟瑟发抖”。这段引用并不是个文学哑谜,因为此前,广播里正在议论希特勒在但泽制造的危机。如此这般,小说结尾的时间点是在1939年9月1日,德军闪击波兰,世界大战拉开序幕。 无论麦卡勒斯还是霍珀,揭示明确时间点这一行为本身,都不是意图凝聚特定的历史时刻——不仅是这般肤浅的作用。宏观层面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两个时间节点也是属于整个南方文学、属于美国写实画派的情感宣泄点,涉及到长达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精神内核蜕变。选定之后,时代的孤独共性便在美国得以承继下来。麦卡勒斯本人对此是有所自觉的,她写过《瞧着归家路啊,美国人》和《我们打了条幅——我们也是和平主义者》这样鼓舞士气的战时文章,还以《为了自由的夜巡》为饱受轰炸折磨的伦敦打气。相比之下,霍珀的《夜游者》更像是对麦卡勒斯这两部小说代表作的绘画式总结。《心是孤独的猎手》在主角设定上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如霍珀《夜游者》画中的那四个具象角色,拱卫着哑巴辛格这一如耶稣般的核心人物。但是,如果将画作中处于视觉中央的那位男士(也即先前我们认作是科普兰医生的男士。据说,霍珀是以自己的形象来绘制这一角色的)认作辛格,《夜游者》在对《心是孤独的猎手》的解读上,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女士可以是米克或者杰克·布朗特,那个背影是希腊佬安东尼帕罗斯——麦卡勒斯的这两部小说都有着隐晦的同性恋视角,酒保的身份则无甚紧要了。《心是孤独的猎手》里辛格爱安东尼帕罗斯,“好朋友”这个描述在全书中出现了近百次,是关乎生命的挚爱;《伤心咖啡馆之歌》里莱蒙表哥爱马文·梅西,是近乎崇拜的痴爱。 如果说《三块广告牌》是麦卡勒斯小说的电影式总结,那么米尔德丽德这位失去女儿的彪悍母亲便是米克或艾米丽娅小姐,是《夜游者》中的红衣女人——这种男性化塑造如出一辙。杰克·布朗特、安东尼帕罗斯、莱蒙表哥是有着“畸人”共性的,他们占据霍珀画作中背对人群的那个位置。“背对众人”自然也是畸人概念的隐喻,在电影中,这个位置是属于社交障碍狄克森和侏儒詹姆斯的。狄克森对警长威洛比有着同性间的爱意,警长死后,狄克森伴着一首BuckskinStallion所展开的血腥报复,与辛格的自我废弃情节简直神似。小镇警局轻视黑人的桥段,也是在复现《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科普兰医生的亲身经历。《伤心咖啡馆之歌》虽缺少虐待黑人的描述,但艾米丽娅小姐对黑仆杰夫的役使,寥寥数笔便说明了问题。 场景上,两部小说都有咖啡馆。《夜游者》几乎是在对布兰侬的纽约咖啡馆进行视觉还原。《三块广告牌》中,酒馆也是最重要的场景。地点上的原型或许是欧内斯特·海明威《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这部短篇小说,海明威式的决绝对于麦卡勒斯及其后来者们的影响,照此看来,大概也是毋庸置疑的。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