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现在需要回到公社制理想所固有的更微妙的暴力形式。阿多诺明确地提醒我们,一种普遍的、明晰的、彻底理性化的人性理想,理性意志的社会,本身就带有针对另类者的一种暴力态度,另类者总是被打上非理性的标签。此外,充分理性化的人类观念——我是审慎地使用这一词语的——本身就在强迫他者进入理性化共同体的特定理想,包括我们作为肉眼凡胎的生命的方方面面在内。用德里达的话来说: 人称自己为人,唯有通过划出界线,把他的他者排除在增补游戏之外:纯粹的自然、动物界、原始状态、童年、疯癫、神圣。对这些界限的接近,既是死亡威胁的恐惧,也是进入没有延异的生活欲望。人称自己为人的历史,就是把我们之间所有这些界限结合成为总体系统的表达。 我们现在转向德里达与卢梭的关联性。卢梭因其试图把共同体的罗曼蒂克概念与民主调和起来的努力而为人所记忆。但是对德里达来说,甚至卢梭强调自治的共同体的民主之梦——显然比黑格尔提供的更民主——仍然陷在阿多诺批判黑格尔的那种困境里面。因此,德里达对卢梭的批判变得与我们对共同体理想的讨论密切相关。 在卢梭构成共同体的平等幻梦中,节庆生活催生了共同体,德里达在这种幻梦中揭示了一种快乐而放纵的节庆,一种没有延异的生活之梦,一种实际上没有中介的生活之梦。在这种幻梦中,参与者充分在场(full present),互相直接平等会面。这种幻梦也是一种英雄不问出处的富于创意的聚会时刻。这种节庆是一种原创性的仪式,它让非暴力的伦理学敞开。它也是一种节庆,不是一种理性的人之间的争论。在此幻梦中,人们喝酒、跳舞、歌唱,庆祝他们会聚在一起,形成共同体。因此,在这种共同体的形成中,狄俄尼索斯的元素并未被否定。卢梭式的共同体,源于节庆,基于直接的、非中介的面对面关系,表达了卢梭关于人类与自然、个体与共同体、充满欲望和意愿的肉身主体与市民的公共生活角色之间非对立的梦想。卢梭赋予鲜活的声音以特权,说话成为互相同等的人之间的传媒,在共同决定他们的政府乃至他们的命运时,他们是互相真实表现自己的。充分在场的目的确实有助于我们通过共同重新界定我们的命运而逃避宿命。 但是,根据德里达的看法,人们在卢梭那里发现的并不是非对立关系之梦的实现,而是对内在于同一性原则的暴力等级制的复制。 什么是卢梭希冀同时获得的两种互相矛盾的可能性?他如何获取它?一方面,他希望通过赋予它积极的价值去肯定它作为统摄一切的原则,或者全部用以建构体系(情感、语言、社会、人,等等)。但是,在他想去肯定的同时,所有这一切又是通过统摄过程而被删除的(旨趣、生命、力量,也同样有情感,等等)。增补是这两种可能性的统摄结构,卢梭只能分解它们,把它们分离成两种简单的单元,逻辑上的矛盾因此容纳了一种对否定与肯定而言都是完好无损的纯粹性。而卢梭,好像限于增补性图式内的同一性逻辑一样,说他不想说的话,描绘他不想做出的结论:肯定(即是)否定,生(即是)死,在场(即是)缺席,而这种重复的增补并未包含着任何辩证法,如果概念历来是由在场的视界所统治的,那么,至少情况就不是这样。 从政治维度而言,卢梭的人人平等的共同体生活幻象使得卢梭所希冀克服的暴力对立的等级制所固有的社会不平等性长久存留。用阿多诺的术语来说,德里达通过揭示卢梭理想化的共同体同一性中的差异性,暗中破坏了同一性逻辑。因此,举例来说,他给我们展示了卢梭的充分言说(full speech)的原创性神话如何假设了一种已经占据有利地位的语言学系统,共同体成员凭借它掌握语言。言说暗指了“书写”。针对卢梭和后来的卢梭信徒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德里达认为最初纯真的共同体是无法脱离书写的,书写后来为人类学家并非蓄意的帝国主义所讹用。确实,德里达把自然纯真的神话与脱离书写的共同体信仰联系起来,德里达揭示的这种神话本身就是种族中心主义的翻版。德里达认为,书写是使交流成为可能的表达系统,而不只是通常我们认为的那样,书写意指一种图像符号系统,带有可辨识的字母之类的东西。正如德里达所解释的,“系谱学关系与社会分类学是原始书写(arche-writing)的缝口”。原始书写现身于此,恭候着延异这种增补性结构,即黑格尔扬弃的“干扰的机遇”。 回顾他没有书写就没有共同体的断言,德里达认为专用名词的安置是任何社会都不能规避的,它赋予书写以这样的意义,即它意味着一种分类系统,人们通过这一系统互相认识。专用名词本身带有制度历史的踪迹。换言之,言说的同一性被它的他者,也就是书写所玷污了。而德里达拒斥卢梭的原始纯真的神话,并不导致他否定他所理解的列维-施特劳斯和卢梭的中心观点——书写与暴力的联系。书写与“再现”诸系统的其他形式,无论它们是亲属关系系统还是政治制度,都是一种试图抗衡人类暴力的努力。而在某种程度上,为伦理与政治“再现”所建立的系统是认同于准则的,并僵硬地规定正确的行为,这样的系统建立本身就带有自己的暴力。对德里达而言,命名的权力是“语言的原初暴力,它存在于差异内部的铭刻,存在于分类中……为了思考系统内部的特异性,把它铭刻在那儿,这就是原始书写的姿态:原始暴力”。德里达认为,卢梭的言说伦理学是一种“掌控现在的错觉”,一种危险的错觉,因为它掩盖或抹杀了语言分类权力的暴力。 没有他者的显现就没有伦理学,同时也因此没有缺席、掩饰、迂回、延异、书写。原始书写是非道德的道德之源。它是伦理学的非伦理学开端,一种暴力的开端。正如在书写的通俗概念的例证中,为了重复道德系谱学,暴力的伦理学情况必须严格地加以悬置。 言说与言说主体不能获得充分的出场,因为言说被嵌入了一种既有的语言学系统中,独立于任何经验主体。因此,语言学意义不能简化为言说主体的意图。符号系统的可重复性,那种使得符号系统运作语言的可重复性,悖论式地偷偷带走发送者的信息。语言不能为作为其自身表达的主体所拥有。获取充分的自我澄明或共同体澄明的不可能性,可以理解为人类限度的“法律”以及共同体以语言为基础的结果。 个体或者共同体由差异所导致的分裂,包括使个体与共同体得以形成的相应的语言学系统,在排斥差异的“新的”同一性中并未被克服,正如德里达认为这种情况就存在于黑格尔的体系中那样。德里达的反驳不仅是哲学的,显然还是伦理学的。对德里达而言,恰如对阿多诺那样,黑格尔的扬弃是同化的另一种伪装。他者被精神所损毁,以便抹杀他者的差异。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是以其最精微复杂的形式出现的充分在场的神话。由于在充分在场的神话上共享着隐秘的联盟,德里达把卢梭的梦想(尽管其明显不同于黑格尔)与黑格尔联系起来。恰如德里达所释: 况且,卢梭并不是独自一人为增补图式所困。所有的意义,特别是所有的话语都被困在那儿,通过一种单向度的转换,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话语,卢梭的概念在这种形而上学话语内发生嬗变。当黑格尔宣称缺席与在场、非存在与存在的统一时,辩证法或历史仍将延续,至少在我们曾经谈论的卢梭希望言说的话语层面上如此;这是两种充分在场之间的中介运动。末世论的基督再次圣临也是一种充分言说的在场,它在逻各斯自我意识的框架内,把其所有的差异与表达都会聚在一起。这样一来,在追问关于卢梭文本的历史情境的必然性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把其所有附属于在场形而上学的符号,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加以定位,通过基于自我显现的在场表达赋予其韵律。 在此我们又要回到黑格尔的精神,即自在且自为的主体,因而也是完全自明的主体。德里达充分在场的神话的问题框架,尤其是黑格尔对基于自我显现神话的理解所凭依的问题框架,可以解释为对黑格尔自我反驳的一种解读。按照这种解读,黑格尔关于原始公有制主体的观点并未遭到否定,相反,它是与黑格尔自己对构成性本质的形而上学的“解构”相一致的。 增补,就是空无,既不是在场也不是缺席,它既不是实体也不是人的本质。它是……用形而上学或者本体论概念都无法理解的。因此,人的……这种属性并不是一种人的属性:总体而言,它是本性(the proper)的错位。 什么是这种本性错位的伦理与法律意义?个体的个人身份不再能够像黑格尔在《权利的哲学》的一种解读中所提出的那样,想象成最初属性的形式。解中心的主体至关重要。主体不再能够被设想为一种自我认同、自我显现的实体,一种自我限定的本质,但是也不能简单地想象成与集体性相关的一种东西。(译 | 麦永雄) 本文选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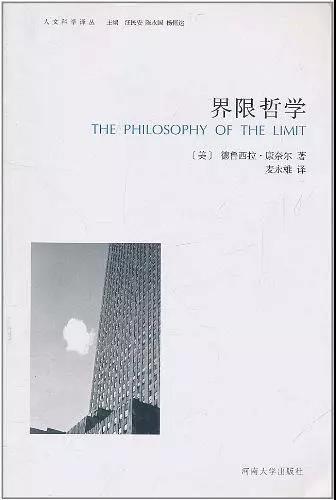 《界限哲学》 【美】德鲁西拉·康奈尔 著 麦永雄 译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