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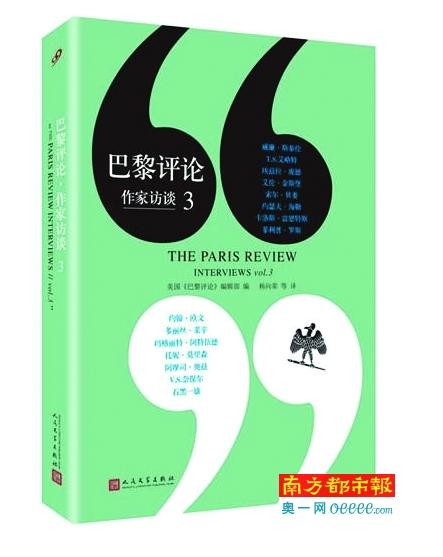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巴黎评论》编辑部编,杨向荣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版,49 .00元。
时下流行名目繁多的写作教程,平庸之辈打着教授文学的幌子,四处兜售所谓的成功秘诀。而《巴黎评论》称得上写作界的良心,作为一个老牌文学刊物,《巴黎评论》从不把谈论作家的立身处世、个人幸福当作重心,也无意一味神化受访者。吸引他们的永远是那些经历时间考验、自带熠熠光彩的作品。好比一生只做 一 件 事 的 工 匠 ,自1953年创刊以来,60余年不懈耕耘,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始终不曾偏离最初的方向:从“小说的艺术”到“诗歌的艺术”,再到“批评的艺术”,洋洋洒洒数十卷,早已超越了一本期刊的容量。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延续着前两卷的强势,遴选15位欧美知名作家、诗人,从26岁早早荣获普利策奖的威廉·斯泰伦,到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名人大作汇聚一堂,怎么看都是一场极致的文学盛宴。仿佛事先设定的程序,只要吱吱嘎嘎的录音机一响起,所有人就都进入了角色。金斯堡手舞足蹈,开口闭口尽是布莱克与禅宗、瑜伽和顿悟,言谈间似要将话筒牢牢握在手中;奈保尔全程一副冷漠脸,时时抛出连串反问,将单纯的问答环节变成步步紧逼的质疑;艾略特很轻松,抱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姿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哈哈大笑不绝于耳,数次打断采访的进程……
很难说,这样的对话究竟是“傲娇”大爆发,还是入戏太深无法轻易解脱。或者,不妨说是彻头彻尾的表演吧。可就算表演又有什么关系?只要说出来的不是庸见,而是真知,就已经足够。别忘了菲利普·罗斯的话,作家就是一个表演者,人物就是他的面具。不论是本色出演,还是“戏精”上身,仰赖的永远是作家的想象力。毕竟,文学不是选美大赛。我们看重的不是颜值,而是内涵。这种内涵来自作家在角色扮演之余,为故事附加上的“说服力和冒险精神”。
谈论文学不外乎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巴黎评论》也不例外。流行观点告诉我们,作家写作往往是为了抵抗什么,具体原因不一而足,都可以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或是抵抗平庸的侵袭,或是拒绝主流的归类,因而穷尽所能在不同领域里挖掘。其实不然。至少在艾略特这里,写作不是高深的玩意儿,它不过是旧时天桥上的杂耍,被贴上了自以为是的花头。我们知道的他是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诗歌、戏剧、文论门门懂、样样精。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位声震诗坛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有不靠谱的时候,曾经有模有样地为“妖猫”做赋。那么《四个四重奏》呢,不要感谢艾略特,应该感谢希特勒。如果不是1939年的战争打乱了他的创作节奏,天知道这世上还会多出多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再来看看怎么写。世人皆知文学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当然,没有人愿意在创作中自曝其短,以虚构的小说复制活生生的自我:既脆弱又孤独、很天真很愚钝。然而,这种一刀切开的粗暴做法,未尝不是文学的伪善之处。金斯堡的一句话仿佛惊醒了所有装睡的人:“去 写 ,正 如 你 我 的 存在。”意思是说,文学与现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作品;你出生在哪里,就有哪里的故事如影随行,“他知道他活着,他的存在与任何其他题材一样好”。
仿佛是感应到诗人的召唤,作家们齐齐发出了自己的回应。比如托妮·莫里森。与那些不愿被贴标签的同行相比,她更乐于接受“黑人女作家”的称谓。若是非要逼着她穿越时空、去质问纪德为何不屈尊写写黑人,或许她更愿意像福克纳一样,呆在孕育她的南方,书写属于她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因为写作不是别的,首先要无限契合她非裔美国人的脾性,其次才谈得上那些被称之为“文学传统”的东西。
同样,守着精神原乡的还有富恩特斯。他的每一个新动作都是接续旧作未尽之处,去完成同一本书。你永远不要指望从他手里看到类似“侯爵夫人下午五点出门去”的句子。因为在富恩特斯这儿,小说就是一面魔镜,在一比一还原镜中景物的同时,更要一砖一瓦地制造、放大现实。他很清楚他是谁、来自哪里,并不曾因为自己的故乡心生不安。剪不断的血脉将他与马尔克斯、科塔萨尔、卡彭铁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用怀疑,他们都写着同一本小说,名叫拉美。
纵观全书,不论肤色性别、国籍际遇有着怎样的区分,不管习惯手写还是打字,是一笔一画描摹现实,还是天马行空、脑洞大开,作家们对写作的看法终究还是一致的。约翰·欧文并不介意他的作品被称为“灾难小说”。因为作家终究不是闹喳喳的鹊儿,只知报喜不知报忧。他的创作就是“寻找受害者”,写得越多越深入,灾难就越集中。狄更斯、格拉斯、冯内古特教会他怎么做个好作家,“吸引我的,是令他们愤怒、热情洋溢、愤慨、赞赏的事物,是令他们对人寄予同情的事物,还有令他们对人感到憎恶的事物”。
愤怒、热情、同情、憎恶,大约也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关键词。这位加拿大女作家从不避讳暴力。小说于她,不仅是自我表达的秀场,也是窥望世界的窗口。人总是社会的动物吧,既然现实引领她拿起笔,她就该让笔尖停留于现实。她自称成长环境并无暴力,但不代表她的世界全无波澜。况且,要成为真正的作家,又有什么理由画地为牢,将自己活生生地困在奥斯丁的一亩三分地?很快,随着阅历的增加,现实主义扑面而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暴虐,战争、谋杀、阴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人身伤害”。谁又能置身事外,装作视而不见,去谈论什么你若安好、我便天晴?
说到这里,我们还能指望文学课吗?《苏菲的选择》的作者斯泰伦对写作班没有好感。他称其为“毁人的营生”。不是吗?几个原本应该被“赶尽杀绝”的教员自以为能带领学生迈步走入著名作家的阵营,殊不知反倒是误人子弟,“用最令人恶心的方式糊弄着那些可怜之至、见不到丁点儿才华的习作者”。相反,如果从《巴黎评论》中读出一点“写作秘辛”,当然不是什么难事。不过,要想成为真正的作家,仅仅靠阅读成功法门远远不够。你必须抛开一切,静下心来,实实在在地写,哪怕写下的只是抽屉文学,哪怕你的读者只有你一个人。但终究还是写了吧,毕竟写下才是永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