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可借助Croft(1990)提出的“关联的标记性”概念进行解释。若某一结构与相对应的一对或一组语境建立关联,而其中又有一个语境最频繁地与此结构相联系,那么该语境下这一结构所具有的意义就是其原型意义,而且这一关联是无标记关联,其他语境下赋予的意义与这一结构的关联则是有标记关联。“都是+NP”与消极语境之间建立了最频繁的关联,并且占有了绝对的优势,所以在消极语境下“都是+NP”结构所具有的责怪义便成了它的原型意义,而且其关联是无标记的,而在其他语境下的意义与这一结构的关联则是有标记的。试比较:  无标记项可以看作心理计算上的一个“缺省值”(default),在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就以这个值为准,所以当“都是+NP”结构在话语中出现时,被激活的应该是它的原型意义,即责怪义。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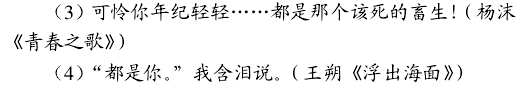 例(3)由于语境制约,责怪义是很清晰的;例(4)没有上下文的提示,即在没有语义色彩标记的前提下,听话人理解的是“都是你招惹的我”这一原型意义——责怪义。这就是构式义的固化以及泛化。 当“都是+NP”结构表示感激意义时,则是有标记的,即需要具有能够明确说话人态度的词语如“功劳、帮助”等进行标记,或者对“感激、赞美”的原由加以补充说明。这也说明“都是+NP”的构式义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可撤消性(cancellability)。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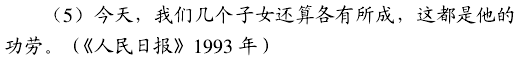 “都是+NP”与责怪义之间“超符号”关系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完成的,它需要两者之间的认知通道不断被激活,不断发生生化反应,需要其前结构形式与消极语境高频共现以及“都是+NP”内部成分贬义性高频出现的双重作用。语境赋予了“都是+NP”结构“超符号”的意义,从而形成了责怪义的“固化”;反过来,这一固化了的语义又制约了该结构对语境的选择。这种双向促进和制约是历时的,是在汉语长期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