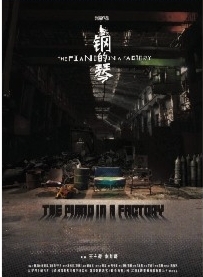■主持:吴子桐 ■嘉宾: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 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 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子桐:20世纪西方也出现了一些讲述中国历史的电影,如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等等,在二位看来,西方的“想象”与中国的“记忆”呈现出怎样不同的历史图景? 王炎:这部电影是1987年拍摄的,它既是一部独立风格的影片,又是一个好莱坞影片,当然还是部意大利人导演的戏。这部影片非常成功,获了奥斯卡奖,票房奇高无比,是一部特别成功的影片。同时,在1987年的中国,它也对中国大众文化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跟这部影片同时拍摄的,还有一部中国电视连续剧,也叫《末代皇帝》,陈道明演溥仪。从这两部作品被观众接受的角度来看,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当时中国大众觉得电视剧既真实又好看,而电影《末代皇帝》则看不懂,不太受欢迎。中国政府却对这部美国片高度重视,据说伊丽莎白二世当年访华,为了拍这部电影,居然没让英国女王去参观故宫。政府允许电影《末代皇帝》摄制组进驻故宫拍摄,开了历史的先河。拍摄过程中一只照明灯过热,引燃了一件文物,现在这已完全不可想象了。在那之后,中国政府才立法禁止在故宫拍戏。所以,这部电影是一个特别大的事件。 我不想用大家耳熟能详的“东方主义”的角度来谈这部影片。我倒想说,这部影片怎么会与中国观众的欣赏口味有这么大的不一样?或者说,连续剧和电影到底区别在哪?讲述历史的方式有何不同?这里,我不扩展到一个更大的政治文化层面,只想讲故事本身。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呈现了一个最经典的中国历史的讲述方式,像后来的《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连续剧一样,它们讲述王朝历史的方式,与评书传统或历史传记的方式是同构的——有大的历史事件、强烈的戏剧冲突、人物之间的种种矛盾——最经典的厚黑权力博弈,这才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历史话语。但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是一个经典的好莱坞影片,虽然是号称“独立风格”。电影的故事结构和讲述方式都属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线性逻辑的故事,突出明确的一个中心人物,所有戏剧冲突都围绕着主人公这一线索展开,最重要的是心理冲突,整个情节都围绕着一个人的心理变化或成长过程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心理剧,或者叫历史/心理剧,就是将整个大的历史都浓缩到个体的精神成长或者心路历程之中去。这是好莱坞讲述史诗的一个最经典的方式:心灵史的方式——你会透过个体的成长观察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走向。显然这部电影在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都非常讨巧。我们看20世纪50到60年代的美国史诗影片,差不多都是这个模式,而且非常有效,也包括犯罪片、战争片等,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叙事机制,但这个机制未必适合中国人讲故事的路数。 为佐证这个看法,我可以举最近票房很高的一部影片为例,就是《失恋33天》。它与中国人理解故事的方式非常贴切。影片中有两个主人公,从心路历程和心灵史的角度来说,他们的角色不是特殊的。整个故事其实是把网络上传播的段子拼接在一起,只要用这两个角色串起来即可。这两个主人公完全是类型化的角色——时尚且无奈的城市白领,既不特殊,也不特立独行,相反很有代表性,容易引起共鸣。搞笑、巧合、冲突、浪漫、反转等故事机制,在《失恋33天》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看完电影之后,我的感觉空落落的,虽然很酷、极爽,但缺点什么。缺的就是中国传统故事中的历史和伦理指涉。 吴子桐:像李安拍的《卧虎藏龙》,在中国观众和世界观众当中得到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观众可能觉得是瞎编的,一般的观众可能觉得有一种貌似中国的东西,可是有东西看不懂,会觉得不好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逻辑? 王炎:我跟戴老师对好莱坞电影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我总觉得好莱坞的机制有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商业化的,生产电影就像汽车、洗衣粉一样,是从生产线上下来的东西。电影有固定的配方、固定的制作模式,甚至可以写成教材在课上教授基本流程,这是它商业的方面。但它还有另一面,就是作者的理念。这个机制可以给导演和编剧以空间,允许个人风格、个人视角和叙事的独特性,使个人经验在讲述中成为可能,所以我觉得电影《末代皇帝》就是这个机制下的产物。但它最差的地方是对中国历史、中国人物以及中国思维的陌生感。首先你会觉得演溥仪的人(尊龙)根本不是中国人。其次,影片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讲述,洋师傅庄士敦作为故事的叙述者,推动故事的角色也以在中国的西方人物为主。而中国人的角色往往是被动的、被大的故事裹挟着,他们只在故事里承担着历史角色。你看到的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视角,对历史的解读和思辨完全是西方人认识历史的角度。也许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避免,毕竟这是在讲一个异国情调的故事。 戴锦华:1987年我已经是电影学院的青年教师了,1989年我在课上讲贝托鲁奇,我给他的命名是:“资产者的儿子”。我是在两个层次上说,一是说他作为欧洲资产者的儿子,怀抱着对欧洲资产阶级文化深刻的情结,永远仰慕着一个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前的世界,也就是贵族的世界。他永远仰视着、想象着那样一种革命之前的、贵族独有的优雅。作为电影作者,他的影片中复沓出现的主题,始终是大时代里倍受拨弄的、无助的个人;历史太残暴,他人太强大,贝托鲁奇的主人公在这样的历史中以犬儒的姿态随波逐流(他的一部名片就叫《随波逐流的人》);他可能犯罪,但却不是罪人,因为个人无法承担历史责任。他几乎所有的影片都在重述这样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说,《末代皇帝》并无差异性。中国故事只是在修辞意义上提供异国情调的造型元素:清廷、小皇帝或绿军装、红袖章的红卫兵。 像王炎所说的,当时中国观众可能不喜欢电影《末代皇帝》,但电影人可是狂恋《末代皇帝》,因为贝托鲁奇和他的《末代皇帝》成为了一个最为直观的示范,告诉我们怎么去讲述个人和历史。他在中国演讲时说的一句话,后来成为一个时代的名言,那句话是:“个人是历史的人质”。在历史中,尤其在大时代,我们被历史暴力绑架,一个遭绑架的人质当然无法承担历史责任。这个说法呼应了那个时代:结束“文革”历史,我们每个人都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但是不想为那段历史承担任何责任,相反挺身而出来审判那段历史。贝托鲁奇简直是提供了一个指南针,大家也许没从中学会好莱坞式的讲故事的方法,但是大家学会了怎么去从个人的角度去想象历史,从而否定历史。 今天看来,贝托鲁奇和《末代皇帝》成了后冷战历史书写的先声:以个人、记忆的名义重写历史。《末代皇帝》正是根据溥仪自己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改编的。因此,其中的历史叙述先在地占有了个人记忆的名义。回忆录作为“原作”,担保了故事的真实,却不担保历史的真相,因为后者不重要。溥仪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角色,始终被历史推搡、折磨、利用,始终只是一个傀儡。在贝托鲁奇那里,他关注的不是那段把溥仪变为傀儡的历史,甚至不是真实历史中的人,而是抽象人性意义上的个人——个人的心路与生命记忆,历史只是故事的景片。这正是我们之前谈到的后冷战、新主流以记忆之名再现历史、改写历史的有效方式。而1987年,在人们的浑然不觉中,将人类一分为二的冷战即将结束,后冷战就要到来。 在后冷战、好莱坞的历史书写中,必须提到《阿甘正传》。《阿甘正传》选取的是外在的、更是有效的情节剧方式。剧情设定主人公阿甘智商75,以此为前提,你便无法苛责这个人物所限定的历史视角——讲述什么、忽略什么、如何讲述,因为他没有能力认知重大的历史时刻。于是,这个“傻人有傻福”的阿甘便极为“幸运”地经历了战后美国史的似乎所有大事件,于是串连起一个背离20世纪60年代叙述逻辑的当代史。当然,《阿甘正传》与其说是为了重新建立战后美国的历史,不如说是通过阿甘,让美国每一个亲历这段历史的“普通人”,找到一个自我原谅和自我放置的空间。这部电影同样受到了中国观众的热爱,因为经历了大时代,“我们”需要的不是严正的历史,而是枕边的童话。 吴子桐:二位在叙述中也涉及到了美国的史诗题材,我们另外感兴趣的话题就是美国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非常热衷于史诗题材。这类电影不仅在美国本土取得成功,在全球电影市场上同样所向披靡。请二位谈谈此类电影成功的因素,它们在建构历史方面,与近年来中国拍摄的历史题材电影有何异同? 王炎:首先,史诗电影不仅是情节上讲历史的大叙事,还是电影技术上的一种新形式。它因电视机的普及而应运而生,在20世纪50年代,电视机进入60%的美国家庭时,电影院受到了巨大冲击。人们宁愿呆家里、在火炉边看电视。而且,观众可以经常回顾经典影片。可以想见,电视成了电影资料馆,这会给电影公司带来怎样的冲击。 电影界回应的方式第一个就是生产宽银幕电影,宽银幕电影不适合拍家庭伦理故事、室内剧或男欢女爱。于是,需要与宽银幕空间感相配的历史题材和大场面故事,战争或宗教史诗片便出现了,这是电影技术对史诗影片内容的要求。 另外一个背景,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冷战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语境,整个世界被意识形态的分歧割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政治阵营的方式对抗着。讲述这一对峙,需要新的形式重述历史。20世纪50年代,配合宽银幕和冷战形势的题材便是宗教史诗影片。出现了大概几十部圣经题材影片,从技术角度上来说,这些影片非常适合大场面、大角度,以及各种奇观、特效等新技术。另外一点,宗教史诗影片承担了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当时西方的道德优越感恰恰来自于基督教,艾森豪威尔夫妇曾带头去教堂,并在电视里反复播放,形成了一个宗教回归的运动。从那个时代开始,大量宗教史诗影片取代了二战题材的战争片。如今我们在许多科幻影片利用电影新技术制作的特效、大场景奇观里面,仍隐约看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电影应对危机、技术创新的影子,这成为好莱坞独特的风格,也是其他国家的电影工业难以抗衡的地方。当年拍史诗影片投入极大,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埃及艳后》几乎拖垮了20世纪福克斯公司。 还有一个就是戴老师刚才讲的再现历史的方式,是从内容的角度来说。史诗电影也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范式,就是psycho-historical-narrative, 心理历史叙述模式——无论多大的历史,都可以在个人的心理历程中得以呈现。包括斯皮尔伯格的《世界之战》,人类与外太空交战都可以从一个家庭的角度、父亲对女儿的关爱中呈现。还有《独立日》、《2012》等,无论多大的题材,都可以聚焦在个人的内心经验之中。我觉得这是好莱坞一个非常独特的东西。史诗片反映出美国式经验主义的世界观,即在个人经验的范围内寻找表达美国价值观和审美方式的途径。 与其相对照的就是苏联模式的史诗电影。苏联曾拍摄《解放》,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拍摄《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等——这是中国大陆20世纪90年代拍摄《大决战三部曲》——《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基本叙事模式:重大历史人物掌控全局、全景式场面、巨大的历史转折、以事件为情节动力等。这是苏联的电影传统,而冯小刚在《集结号》中,却模仿好莱坞的风格,在让中国影片走向世界的愿景中,冯小刚力图讲述一个能自圆其说的故事。 戴锦华:我同意王炎的描述——心理历史叙述,相当准确。与此并列的是苏联史诗片——《伊万雷帝》,或《列宁在十月》,或《解放》。我管后者叫历史唯物主义全息图的片段。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观是叙事基础,这一历史逻辑的前提,潜在地要求观众拥有一幅关于历史的全息图,参照着这幅整体图景,影片表现历史中的某些片段和场景。电影给出的场景与观众心中的历史全息图融合,并由后者补足,便可以有效地整合出感人的历史故事与画面。 但说到我个人的观影记忆,其实最为突出的,却是罗马尼亚史诗片,《斯特凡大公》、《蓝色多瑙河》等等。一旦(非专业地)回忆起古代战争、攻城略地,我脑子里出现的全是罗马尼亚电影的画面。(王炎:我也是。)因为当时除了内参片,我们看不到好莱坞电影,也看不到苏联电影。在我的记忆中,罗马尼亚史诗片和美、苏都有所不同。它最重要的叙事坐标是国族历史。罗马尼亚曾是罗马帝国的边陲,也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交界、冲突的地区,曾有着丰富而炽烈的古代历史。这些时段被组织在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罗马尼亚历史叙述之中,成为对其国族身份认同的依托。前现代的历史人物被描述成舍生忘死、抵御外辱的民族英雄。 民族(国家)历史的坐标,在美、苏的同一类型电影中几乎难于觉察。无论在冷战的全球对峙中,还是在后冷战的一极化世界里,美国、苏联都是作为帝国,在其历史叙述中争夺着“人类”的高度和为“人类”的代言权。在后冷战时代、或后冷战之后,多数国别电影——包括中国电影中的历史叙述恐怕更接近于昔日的罗马尼亚电影,而不大可能是美国、苏联史诗片。其历史叙述大多是在对民族国家的自我想象的逆推脉络中建立的,它也经常履行着“民族寓言”的社会功能。于是,一边是借古讽今——“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一边则是国族身份表述所要求的对自身文化差异性的自觉。所以中国古装大巨片的困局,一边是为新自由主义暴力化了的现实欲望结构,一份胜利了的失败者的历史观,一边则是为百年风云激变的历史所中空化了的文化自觉。不错,我们学不像好莱坞;但我以为,这是用美国的、或者说西方的文化逻辑叙述中国历史的必然。其结果就是从《英雄》到《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华美空洞。因为这里的历史叙述及其逻辑只能是权力博弈、君臣斗法、厚黑学、宫廷秘闻……结果就只有成王败寇,或者干脆是丛林法则。其中所谓“好莱坞元素”,便是大资本所营造的奇观场景、明星阵容、东亚或国际联军的制作团队,而没有好莱坞的个人想象、心灵悲剧历程。而中国元素则在放大无数倍的第五代“仪式美学”中,变成了武术、兵器、服饰、琴棋书画的文物展。 我们来看一下何平的《麦田》:影片实际上成就了一幅没有加害者、没有受害者,只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历史叙述。因为在影片的内部逻辑中,如果赵国胜了,并不意味着任何改变,只意味着遭杀戮的是秦人。问题不是权力、暴力、人性恶,而是如何讲述;问题是类似影片完全没有给我们提供权力、暴力逻辑之外的其他参数,仿佛赵胜杀秦、秦胜杀赵,成生败死。这就是历史?就是历史的全部?且不说该不该、能不能学好莱坞——《金陵十三钗》学得很像啊,斥巨资用了好莱坞的特效团队、一线影星贝尔,国人也认为张艺谋证明了“中国人也能拍中规中距的好莱坞A级片”;但即使不说影片的文化问题,你可以把一部中国电影拍成英语片,把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再一次搬进教堂上演(或抹除),但迄今为止,好莱坞或者说美国似乎并不买账——当然,我们很清楚,这里面纠缠着国际政治的林林总总,并不只与电影有关。 回到我们的话题:好莱坞——至少是A级/大制作片和多数B级/类型片的价值始终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所谓“人性”、“心理”叙述只是美国主旋律得以讲述的小关节和润滑剂。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古装大片也就是一些厚黑的故事,它仍需要以中国式伦理、人情的细查和体认来润滑、贯通。在这种意义上,二月河的清廷小说算是一个成功的例证:帝王、统治的故事里是中国式的权力与人情逻辑。无怪有大型民营企业将二月河的小说定做员工商战读本。一旦你真的获知并能够体察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情理逻辑,你就可能进一步理解到历经逾百年现代化历程的中国从来不是、现在仍然不是“东方专制主义”或权钱的“厚黑学”所可能概括的。这就又说到了陈凯歌的《赵氏孤儿》:《赵氏孤儿》应该说是最古老的中国历史故事之一,也是元杂剧中的名作。且不用列举王国维的著名评价:“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或引证欧洲启蒙运动高潮中伏尔泰对《赵氏孤儿》的改编;可以说,《赵氏孤儿》或中国文化的叙事主题之一——托孤救孤,是某种文化精髓或幽隐之所在。当然是、但不仅是忠义,是善恶,是正义,更主要的是“诺”——中国文化中承诺的至高位置,“千金重一诺”,为此才有程婴舍子、公孙杵臼舍命的苍凉悲慨。对一己私欲的超越,该是对人性的基本定义吧。这应该也是欧洲现代思想的发轫之际,伏尔泰盛赞和改编的由来之一。但陈凯歌的“现代”改编(还是在林兆华、田沁鑫的话剧之后)却似乎必须抽空其中原有的文化意涵与价值表述,于是,我们看到的便是一群莫名其“妙”的人,做着一些颇为“变态”的事,却没有任何心理的或哲学的叙事逻辑来支撑它。 也许要多说几句的是,中国古装大巨片的特定困局,不仅是非西方、晚发现代化国家民族(电影)叙述的普遍困境,其特殊之处在于,它在近乎短短的十年间陡临中国的“崛起”。从熟悉的自我叙事——闭关锁国、积弱不振、落后挨打、东亚病夫,“突然”转化成了世界“第三极”(美国、欧洲之后的第三极)。于是,电影的历史叙事不仅关涉自我言说,而且联系着朝向世界的言说。当然参数也变了:不仅是以电影为“形象名片”“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是可否成为世界电影大国,分享全球电影票房利润。仅就电影叙述而言,问题既老且新:不只是“他人的语言,自己的故事”;也不只是困扰了我们近百年的问题:世界的?民族的?(我自己是不认同那种乐观结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性的。)而是继续保持自我批判精神的、深刻的自我认知,是对自身的社会与文化差异性的真实指认。越来越多的人谈起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但必须说,我们今天拥有的还只是对文化自觉的自觉,那不该只是延续百年的焦虑或急迫的新段落,而是一个不同的自我批判与确认。电影依旧是一个重要的路径。不论是《孔子》的结构性破碎,或是《赵氏孤儿》、《麦田》的价值贫血;当然,最令人感慨的仍是《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的自我中空——对于这段幸存者犹在的历史,我们已经丧失了自我叙述的有效路径:如果不依重日本兵,就只能借助美国殡葬师,似乎不通过教堂的彩镶玻璃窗(——宗教建筑意义上的上帝之眼)便无法看到我们身历的灾难。这实在是20世纪中国文化自我流放的最佳例证之一。如何有效地自我叙述、自我想象,如讲述前现代、现代的中国历史,不仅在于批判性地确认中国文化的差异性元素,更重要的,在于回答是否存在着某种“中国道路”,它是否具有别样的资源性价值。作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大国,中国是否能够、或是否应该承担起不同的文化责任?我们,或者干脆说,我,更关注的是“作为过去的未来”。对历史的叙述始终是对未来的勾勒,是打开未来想象的钥匙。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02月22日1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