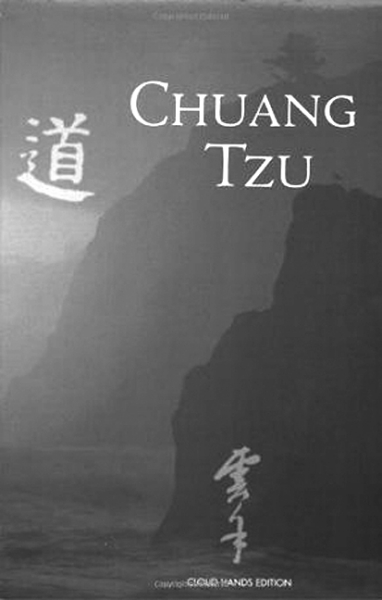对我国读者来说,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是一个几乎陌生的名字。然而在俄国现当代文坛上她却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化用俄国著名作家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笔下一个主人公的话(“没有我世界就不完整。”),我们可以说:“没有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20世纪俄国文学就不完整。”因此《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一书无疑将有助于我国读者全面地认识20世纪俄国文学。 1907年,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科尔涅依·丘可夫斯基是一位著名的全能型文学家: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利季娅幼年时感受过沙俄的专制与落后,但她从小就认识的父亲的那些伟大朋友——诗人勃洛克、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那克,小说家柯罗连科、安德列耶夫、库普林,画家列宾,歌唱家夏里亚平等人——却让她体会到了俄国文化白银时代自由的创作精神,接受了直面人生的俄国优秀文学传统的熏陶。利季娅就是在这些文化前辈的影响下步入文坛的。她当过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写诗,写小说,也写时政评论和文学评论文章。她的文学创作活动从1930年代一直延续到1996年,长达半个多世纪,给后人留下了一笔颇为丰厚的文学遗产。 这次收入《捍卫记忆》里的作品有中篇小说《索菲亚·彼得罗夫娜》、回忆录4篇、日记4组,共9种。这只是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文学创作的一小部分。虽然这9种作品中没有一种作品的名称有“捍卫记忆”四个字,但“捍卫记忆”这一译者从集子中提炼出来的“神来之笔”却忠实反映了利季娅创作的整体风格和审美与道德取向:纪实,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 记忆是人类的一大特质。俄罗斯民族历来非常重视记忆。普希金的朋友弗拉基米尔·达利编撰的《俄语详解词典》中“记忆”一词的释义是这样写的:“记住和不忘记过去的能力;灵魂保存和记住关于过去事情之意识的性能。记忆之于过去就同结论、推测和想象之于未来一样。和对过去的记忆相对的是对未来的洞见……外在记忆是对反复确定的事物无意识的稔熟……内在记忆是对已经认识的事物之科学联系的理性了解,对精神和道德真理的永久性把握。”也就是说,人类不可以没有记忆,因为没有记忆就没有思想,人也就无法称之为人了。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使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掌控国家机器的权力,他们声称要建设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的成员都应是与传统的观念实行了最彻底决裂的“新人”。因为记忆让人不忘记过去,让人保存关于过去事情的意识,让人理性地了解已经认识的事物之间的科学联系,让人不忘记精神和道德的真理,所以记忆就成了苏俄当局最不喜欢的东西。 于是以前传承文明的学校被指为灌输“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知识”的罪魁,“书读得越多越反动”一时成了“公理”。在地主、资本家、官僚被打倒的同时,大批知识精英或主动出走,或被驱逐出境(如“哲学船”事件)。就连“革命的海燕”高尔基也因其思想不合时宜而被革命领袖“强请”出国治病。为了建设理想社会,也为了培养出“新人”,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实行了后来被俄共党魁久加诺夫归纳为“三个垄断”(即垄断思想、垄断政权、垄断经济)的做法。 青年时代的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努力学习和工作,她热爱文学,热爱生活,对未来抱有美好的希望,因为她属于1920年列宁所说的“将要看到共产主义社会,并亲手建设这一社会”(列宁:《青年团的任务》)的那代人。但是19岁时她竟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并被流放,几个月后才在父亲的多方奔走之下获释。1937年,利季娅的丈夫无辜遭到安全部门的逮捕,并于次年被枪杀。利季娅自己也差一点再次被捕。关于白银时代自由创作的记忆、关于二月革命后俄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列宁语)的记忆与1917年后恐怖而贫穷的社会现实,在她心中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促她思考,让她发现了当局大力传播的漂亮谎言和他们竭力掩盖的丑恶罪行之间的尖锐矛盾。于是利季娅在1939年末与1940年初的那个冬天,写下了中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 《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运用俄罗斯经典现实主义的笔法,描述了同名主人公的悲惨遭遇。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是一位勤劳、善良、正直的知识女性。她年约五旬,独自一人把独生子培养成了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在1937年的大恐怖中,她那“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工厂,忠于斯大林”的儿子被人“咬”成了根本不存在的“阴谋团体”的成员,因而被捕,受到非人待遇,并被判了重刑。一向相信国家,“相信报纸和官方人士……甚至胜过自己”的索菲娅竭尽全力也无法拯救无辜的儿子,还受到了无知识、无记忆的邻居和同事——即官方所谓的苏维埃人——的粗暴侮辱,以致精神失常。 《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体现了作家对典型化手法的娴熟掌握:在女主人公形象中不仅包含有女作家自己的丧夫之痛、受辱之苦,而且也浓缩着千百万苏联人在大恐怖时期所经历的怀疑、彷徨、惊恐、悲痛、苦难和绝望。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她的命运就是苏俄人民的命运。 1939年前后,苏俄官方“经典作家”都在大写特写领袖的丰功伟绩(如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1937;包戈廷的《克里姆林宫的钟声》,1940)、苏联人热火朝天的劳动与幸福生活(如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1938;列别杰夫-库玛奇的《生活变得更好了,生活变得更快乐了》,1937)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重重灾难(如科里佐夫的《西班牙日记》,1938)。只有利季娅用她的中篇小说及时保存并捍卫了苏联人民关于大恐怖时期的新鲜记忆。迄今为止,《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仍然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本大恐怖时期写下的描写大恐怖的小说。遗憾的是,直到1988年这本书才在苏联和读者见面。 除《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是文艺小说外,《捍卫记忆》中的其他作品都是纪实性题材的。在这些作品中,丘可夫斯卡娅直截了当地陈述了她对记忆与文学、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理解。她说,“文化是人类精神之高尚激情凝聚的痕迹,这些痕迹互相穿越,互相交叉,铺设出通向未来的新道路。无所畏惧的记忆保存它们不被遗忘,不受践踏。”(第94页)“文化是人们之间的纽带,人类创造的精心守护者……文化体现往昔的记忆,所以记忆才能永世长存。”(第221页) 在深受东正教文化影响的俄苏民众看来,话语应当传达真相、真理,话语应当是真言(即正言,东正教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的。——余一中注),所以丘可夫斯卡娅认为,“话语是灵魂中最珍贵的东西……话语可以吸引人、治愈人、使人幸福、揭露丑恶、令人不安,但不能领导”(第118页)。俄语中的“文学(словесность)”一词就来自“话语”(слово)。也就是说,文学应当传播真言,传播真相和真理,承载民族的记忆。换言之,“知识分子和文学……是人民的活记忆”(第207页)。 丘可夫斯卡娅指出,苏联政府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也实行了计划思想,即思想垄断。他们粗暴地规定“谁应当回忆谁,什么应当永远铭记,什么应当彻底遗忘”(第98页)。因为承载真言的话语、文学、文化和专制、垄断是天然对立的,所以当局一方面“对艺术珍品和俄国历史漠然置之”,“慷慨地把文化创造者投入西伯利亚劳改营或者送给西方和东方”(第127页),“他们杀死了巴别尔。他们杀死了梅耶霍德”(第208页;据维·申塔林斯基著《有罪无罚》一书的统计,仅斯大林时期苏联就有数以千计的作家被杀害。——余一中注),“仿佛从事艺术和科学的人不属于人民”(第127页)。另一方面,他们炮制出“像醉汉嘴里的酒气”一样的“充满谎言”的官方宣传神话(第208页),他们用谎言代替话语-真言,而谎言让人们神志不清。 在“解冻”时期,斯大林大迫害的罪行受到了并不彻底的揭露和批判。但到了19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当局就变了一个调子。他们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必要记住‘所发生的事,主要是因为无益’”(第71页)。他们还说:“斯大林做过一些错事——过火,错误,但这一切已经通通揭发了……人死了不能复活,越少谈论过去越好!”(第79页) 利季娅敏锐地觉察到“我们这里又开始剥夺记忆”(第76页),即“铲除人们对毁灭的生命的记忆”了(第79页)。她认为,如果对此表示沉默,那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是集体谎言和集体沉默的同谋”,所以她表示,“无论如何我也不会交出用痛苦换来的财富,并竭尽全力阻挠人民再次失去记忆”(第76页)。文集中的纪实性作品生动地记载了丘可夫斯卡娅在苏联存在的最后20几年间是怎样艰苦卓绝地捍卫记忆,也即捍卫话语、文学、文化和他们的创造者(其中包括享有世界声誉的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的。这些作品细致而详尽地剖析了克格勃、作家协会、司法机关以及它们的组成人员在毁灭记忆、玷污文学和文化、迫害具有创造力的杰出人士的勾当中,单独或沆瀣一气共同玩弄的种种伎俩,充分展示了它们和他们的狂妄、虚伪、奸诈、卑鄙、无耻和野蛮。用利季娅的话说,她是在“一个螺丝钉一个螺丝钉地追查这架把充满创造力的活生生的人变成冷冰冰的尸体的机器”(第79页)。为此利季娅遭到了当局的疯狂报复。她的作品被禁止发布,她的电话被监听,她的行动受到监视,克格勃人员甚至直接闯入并搜查她的住所,她受到文学界庸碌同行们恣意而粗暴的羞辱并被开除出作家协会,官方成立的她的父亲科尔涅依·丘可夫斯基文学遗产委员会竟然把她排除在外,克格勃甚至对她的家人也实施威胁…… 1960-1970年代利季娅已值花甲和古稀之年,而且身体羸弱、高度近视、行动吃力,但她还是挺了过来,因为她认识到,“真实的祖国历史是教育青少年一代最好的教材……在他们面前的责任感不允许我歪曲真相”,因为她坚信人民“对谎言和赝品有一种顽强抗拒的记忆”,因为她确信苏联当局“掌握的只是现在和部分过去。还有一个管辖过去和将来的机构:文学史”。 读着《捍卫记忆》,我常常为利季娅的公民精神和侠义情怀所感动:她在帕斯捷尔纳克受到全国大批判的时候,保持着和他的密切联系,尊敬他,赞赏他,支持他;她在索尔仁尼琴被作家协会和克格勃逼得无处安身的时候,把他留在自己家里,为他提供了写作和休息的场所;当沙哈罗夫处在克格勃严密监视之下和被流放时,她每年都给他寄生日蛋糕;在布罗茨基被苏联法院当作“寄生虫”审判及被流放时,她尽管自认“我不喜欢布罗茨基”,但因为“他是诗人,应该救他,为他辩护”(第313页),于是就不畏艰险与强权,奋力为他的胜诉、为减轻他的痛苦而多方奔走……被利季娅引为同道的作家、社会活动家们也都和她一样具有公民精神和侠义情怀。这种“友谊和人所散发的温暖必定产生精神产品:对共同伤痛的共同记忆和对共同事业的召唤”(第148页)。正是这种共同记忆和和召唤激发起俄苏知识分子创作出了世界一流的文学和文化杰作。 读着《捍卫记忆》,我常常为利季娅高雅的审美品位和深刻的思想拍案叫绝。例如,如果利季娅没有在与帕斯捷尔纳克的交往中准确捕捉到他关于文学体裁的论述,并把它写入《鲍里斯·帕斯捷尔那克》(第278页)中,我们就无法完整理解帕斯捷尔那克的创作,包括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格医生》;早在索尔仁尼琴备受当局打压的1968年,利季娅就给了他高度评价,并称他为“经典作家”(第361页),在《古拉格群岛》发表后利季娅又称他为“今日的但丁”(第140页)。再如,对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争论、索尔仁尼琴创作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等难以理清的历史问题和文学问题,利季娅都做出了准确、中肯、令人信服的分析。 读着《捍卫记忆》,我会不时地想到,当年围剿话语、文学、文化和记忆的传承人——帕斯捷尔那克、萨哈罗夫、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丘可夫斯卡娅等——的作家协会、克格勃和法院的衮衮诸公是何等地威风,何等地不可一世,仿佛他们就是执掌真理的上帝。三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今天还有谁在读那些苏联作协头目伪造历史、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字,还有谁在赞颂克格勃与苏俄法院迫害正直人士的“功绩”呢?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被记入了历史的耻辱簿之中。然而利季娅与她支持和捍卫的那些人却获得了俄国和世界范围的尊敬。人们读他们的书,给了他们以崇高的荣誉(利季娅获得了法国科学院的自由奖、俄国国家奖等国内外重要奖项),用来表彰他们捍卫记忆的功绩。这种结局既说明了苏联官方文艺批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实质,也印证了利季娅的名言:“……还有一个管辖过去和未来的机构:文学史。”这和我国“要上书的”老话是一致的,即人最终都是要接受历史审判的。 读完《捍卫记忆》,我由衷地感谢此书的两位译者蓝英年先生和徐振亚先生。窃以为,翻译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两个问题:“怎么译?”和“译什么?”俄国文学是一个浩瀚的大海,其作品数以万种计。要想从中选出当下我国读者真正需要的书实非易事。中俄两国的语言、社会、历史、文化差别巨大。利季娅的书中涉及到的人物、事件纷繁复杂,要想把它忠实地译成中文也颇为困难。但是两位先生都是鲁迅说的“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人,他们“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进行“占有,挑选”(鲁迅:《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凭借着自己广博而深厚的俄国文学与文化知识和辛勤而严谨的劳作译出了《捍卫记忆》。书于去年9月出版,11月即被评为2011年“深圳年度十大好书”之一。这无疑是对两位译者准确的选择眼光和优秀的翻译质量的肯定。 读完《捍卫记忆》,我还留有一点点遗憾:其中没有收入丘可夫斯卡娅1966年写的名篇《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信》(见附录)。这是集中反映作者思想与创作风格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丘可夫斯卡娅和当代俄罗斯文学及苏俄社会思想。但愿《捍卫记忆》在再版时能收入这封信和其他一些重要作品。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02月01日09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