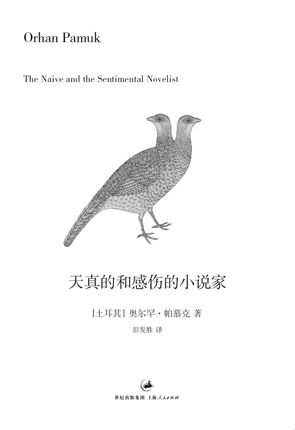《那么远 那么近》是蓝英年先生退休后出的第十本随笔集。我是蓝先生的忠实读者,收入这本集子的文章我以前几乎都在报刊上读过,但这次在集子里重读一遍后我不由觉得:如果说,以前读到那一篇篇文章时我把它们看作是蓝先生从大量苏俄文史资料“矿藏”中提取出的一粒粒思想的金属铀,那么这本集子就是由许多金属铀颗粒积聚成的、超过了临界质量的硕大铀块,它应当在读者的脑子里引发一次思想的核爆。有一句俄国谚语说:所有的比喻都是蹩脚的。我的比喻也不例外,但它确实道出了我阅读《那么远 那么近》时的真实感受。 这种“思想的核爆”打破的首先是苏联文学的光明梦。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我们在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的情况下,把苏联文学当作社会主义文学的样板。于是,苏联文学作品以文化倾销的形式进入到我国的文化生活之中。仅《那么远 那么近》中提及的苏联文学作品就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难忘的一九一九》(以上三部为电影剧本,根据前两部剧本拍摄的同名影片在我国曾长期频繁放映)、《毁灭》、《磨刀石农庄》、《彼得大帝》、《第一骑兵军》、《乐观的悲剧》、《被开垦的处女地》、《青年近卫军》、《俄罗斯问题》、《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等。这些作品都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其中许多都得过斯大林文学奖或列宁文学奖。 有论者说,苏联文学讲究人性、人情,承认爱情的美丽,着力表现人的内心,颇多对大自然和风景的描写,具有强大的抒情性,五十年代起似乎已有一定的自由度。《那么远 那么近》无情地揭开了在这些所谓特点掩盖下的虚妄。最好的例子就是文集中的那篇《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该文中的一段话说出了蓝先生年轻时代读阿扎耶夫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48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以下简称《远离》)所留下的深刻印象: “今天,书中人物仍神奇地留在脑子里……架设电话线的漂亮姑娘丹妮亚、大胡子总工程师别里捷、一心想上前线的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害单相思的姑娘然妮亚……他们忘我的献身精神,他们的痛苦和喜悦,他们真挚的爱情和忠贞的友谊深深地打动过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对远东大自然的绝妙描写……”(《那么远 那么近》,第254页) 一群人在远东壮美的大自然中怀着美好的感情以战斗的姿态铺设输油管道,支援卫国战争的前线,在《远离》为我们绘出的艺术图景中可以看到上面所说的苏联文学的特点:承认人性、人情、爱情,喜欢表现人的内心,喜欢自然风景和细节的描写,有强大的抒情性。然而这些都只是现实主义的表象,而非现实主义最根本的东西——真实性。 1960年代,阿扎耶夫创作了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车厢》,其中讲述了主人公在基洛夫被刺后的肃整中被捕,不经审判就被判刑,并被押解到远东劳改的苦难经历。《车厢》和《远离》都具有自传性。蓝先生指出,“按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车厢》在前,《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在后。先把罪犯用火车押解到远东,劳改犯才在远东铺设输油管道。”(第256页)蓝先生是一位细心的读者,他从《远离》里的“工程管理局局长身着军服”(第256页)一语得出结论:原来,《远离》是在把劳改当作自由的社会主义劳动啊! 西蒙诺夫在1966年为《车厢》作的序中,这样解释《远离》里面没有说出真相的原因:“因为那时公布真相根本不可能。”(第256页)但即使在1966年,有西蒙诺夫这样的文学高官撑腰,《车厢》还是不能发表。它的最终发表是在1988年。这时作者已经逝世二十年了。可见所谓五十年代起苏联文学界似乎已有一定自由度的说法并不准确。比较靠谱的是塔吉扬娜·托尔斯泰娅的说法:苏联文学,也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就是在领导允许的尺度内歌颂领导”。而所有不按领导允许的尺度歌颂领导的作品,更不用说描写生活的作品,是绝对享受不到一丁点儿自由度的。例如,在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时发表的几部思想稍微解放一点的作品《解冻》、《不只是靠面包》、《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在发表后都受到了严厉批判,后来不仅苏联官方出版的苏联文学史教科书中对它们只字不提,就连在图书馆里也借不到这些书了。 关于领导的意图决定了作品和作家的命运的例子,在《那么远 那么近》中比比皆是:当高尔基的文学与社会活动与领导意图有抵触时,列宁会对他说:“如果您不走,我们将遣送您出去。”(第84页)斯大林喜欢不喜欢决定了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一生,“喜欢的可以获得斯大林奖金和各种称号。称号也是福利”(第7页)。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那克受到了迫害及全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批评(我国的《译文》1958年第12期和《世界文学》1959年第1期就刊登有大量批判《日瓦格医生》及其作者的文章),因为“苏斯洛夫认为,就意识形态而言,这(指《日瓦格医生》)是一本危险的书,因为书里说得太多了”(第61页)。另一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遭到苏共中央组织的批判和围剿,最后被驱逐出国,而其亲人也受到株连——妻子被开除公职,岳母被开除党籍(第13页)。被驱逐出国的还有另外一名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格罗斯曼那部被誉为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让苏斯洛夫大发雷霆,后者扬言《生活与命运》“两三百年之后也许能出版”(第114页)。仅《那么远 那么近》中提及的苏联时期迫害作家和查禁作品的事就有数十起之多。 莱蒙托夫有诗云:“在海面蓝色的雾霭中/一叶白帆在闪着光亮/……它的下面是翡翠色的水流,/它的上方是金色的阳光。”这很像1950年代我国读者眼中的苏联文学:因为离得“那么远”,更因为苏联官方向我们推荐的和我们的翻译出版界为读者选择的都是经过了严格筛选的东西,所以那时的读者脑子里才形成了苏联文学的光明形象。然而这只是一个假象。在今天的俄国,意识形态不再至上,昔日的“异端”已经解禁,大量历史档案也已经公开,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研究者们已不再认同和使用苏联文学这一概念,而代之以“苏维埃时期的俄国文学”这一术语。在这一概念中包含有苏维埃时期的俄国官方文学、半官方文学、地下文学和侨民文学几个部分。官方文学即传播苏联官方意图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半官方文学则是作家们在政治高压下凭借勇敢和机智创作的有一定自由度的文学,但其自由度仅限于用来装饰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开明形象。地下文学则是审美观和历史观与苏联官方不同的作家们的作品,它们不见容于官方,只能在“地下”流传。侨民文学则是一代代俄国侨民在苏俄境外创作的文学。地下文学与侨民文学常相互交叉和共通。如帕斯捷尔那克的《日瓦格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布宁、巴尔蒙特、布罗茨基等人的诗作都曾长期在“地下”和俄侨中流行。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年所谓光明的苏联文学,只是浩荡的苏维埃时期俄国文学长河中的一股虽然喧嚣,但思想与审美分量很轻的小水流。受到现代俄国读者喜爱的那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当首推布宁、帕斯捷尔那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人的代表作。而那些当年官方百般褒奖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品则很少有人问津了(第46页)。需要提及的是,一个因为自由创作而非常优秀的作家一旦接受了苏联官方文学的一套创作方法与模式,或曰受了“招安”,他就会变成权势的御用文人,其创作也就枯竭了。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肖洛霍夫。他在二十多岁时就写出了巨著《静静的顿河》,1940年代后不断逢迎官方,甚至在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还大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结果沦为了苏联官方打压自由作家们的一根粗暴的棍子——他攻击过帕斯捷尔那克和索尔仁尼琴,建议苏联官方比苏联法庭还要更加严酷地惩罚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他的两位文学同行。而在那之后,他的文学创作则如同莉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所预言的那样“绝无成就”(详见《中华读书报》2012年2月1日第9版《致〈静静的顿河〉作者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信》)。 《那么远 那么近》应当唤醒那些苏联文学雾海中的梦迷人了。 俄国文学是俄国文化的中心,许多俄国学者都这样认为。《那么远 那么近》以俄国文学为切入点,为我们展示了苏俄文化,即苏维埃时期俄国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存在方式。那是1950年代中国人热切向往的存在方式。可那是怎样一种存在方式呢?在这种存在方式中,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第8页),甚至“议论领导人本版推荐私生活就判处徒刑”(第115页);领袖会亲自指挥暗杀自己的公民(第184页);领袖赋予警察机构以巨大的权力,通过警察“无微不至地”控制着整个国家,还鼓励人们互相告密(第6页),并在“苏联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网。在每个单位都设有情报员”(第204页);媒体只知道重复领袖意旨,以至于苏联“民间流传两句话:《真理报》上没真理,《消息报》上没消息”(第119页);民众的物质生活被长期压抑在贫困水平上——几家人同住一套住宅(第83页),物资供应匮乏,告密成风,道德处于失范的状态(第199页)。看到这样的苏俄社会与政治生活真相,我们不禁要叹息:当年只知道片面地“以俄为师”,而实际上真应该多讲讲“以俄为戒”啊!幸好,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摆脱苏俄模式的社会主义。 读着《那么远 那么近》,我不由地想起1990年代蓝英年先生刚刚开始他的俄苏文化随笔创作时的情况。一些俄苏文学研究者对他的写作并不看好,有人甚至称之为“野路子”。但蓝英年先生却乐此不疲,一写就是二十年。他曾说,这些年来他一篇关于俄苏文学的学术论文都没有写。然而,他的俄苏文化随笔却起到了众多俄苏文学研究家们的论文所起不到的作用,诚如章廷桦先生所说,“恰似串在一起的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把人们的眼睛照亮”。在我国,俄苏文学和文化早已失去了曾有过的显学地位,但蓝英年先生的俄苏文化随笔却不断引起读者的关注,他的随笔集常常名列人文社科畅销书榜。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条。 首先,蓝先生在其随笔写作中始终遵循思想自由和学术无禁区的原则。例如,他最早的一篇文章《试拨尘雾现清辉》记述了俄国女诗人兼小说家苔菲的生平与创作,这位女诗人不仅名不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连1980年代的《苏联百科辞典》里也找不到她的名字,而蓝先生却秉笔直书,高度评价苔菲这位“俄国幽默小说女皇”的深刻思想和艺术成就,尽管她在十月革命后作为“白俄”作家“背叛”了祖国。这样做在改革开放处于特殊时刻的1990年代初是确实需要坚持思想自由的原则的。在《那么远 那么近》中,蓝先生依然是这样做的。例如,《革命者涅恰耶夫》一文就揭示了列宁对恐怖分子涅恰耶夫(涅氏曾被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魔头的身份写入小说《群魔》中)的肯定,列宁说:“涅恰耶夫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能用自己的思想震撼人心……应当出版涅恰耶夫的全部著作。”(第222页)文章进而指出,“涅恰耶夫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是无疑的”。(第224页)在《苏波战争和〈骑兵军〉》一文中,蓝先生指出,俄波战争之所以演变为苏俄对波兰的侵略战争,其根源是列宁坚决主张通过打波兰引发德国乃至世界革命(第242页)。蓝先生就是这样像太史公一样,不为尊者讳,不为主义讳,剖析着苏俄社会历史上的一个个人物与事件,完善着我们关于苏俄国家与文化的客观认识。 蓝先生随笔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广泛占有资料,文史哲社打通,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这一特点在《那么远 那么近》中再次得到了充分体现:书中既有讲述演员、音乐家、作家的文章,也有描写苏共领袖、高官、劳模典型、少先队标兵的文章,还有反映少数民族遭遇、共产国际活动、历史上的恐怖分子的文章。在随笔中蓝先生把他所掌握的信息融会贯通,用严谨的逻辑加以组织,用深刻的刀笔剔去蒙在前人未曾揭示过的一个个文化盲点上的表象,再用地道流畅的现代汉语将真相和本质娓娓道出。例如,在蓝先生之前我国的史家都以为苏共中央1946年《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打压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的产物,而蓝先生却说出了隐藏在这一决议后面的复杂而神秘的故事——苏联高层各个利益集团的内斗(第122~第129页),从而让读者的认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在本文开头我把蓝先生的随笔写作比作从成吨的铀矿里提取铀。我想,这样比喻蓝先生在随笔写作过程中付出的巨大劳动和卓越智慧是符合情理的。仅一篇《与果戈理对话》就需要蓝先生阅读多少俄苏作家的作品并对这些作家的创作特质及他们在历史上的位置做出精辟的评价啊!那诙谐活泼,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恣肆常常让读者不由得拍案叫绝。 蓝先生随笔写作的第三个特点是:讲述苏俄文学与文化时念念不忘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密切关注。例如,在讲到十月革命后苏俄曾粗暴对待老知识分子时,蓝先生就加上一句“有点像1949年以后中国对待老知识分子的态度,要求他们改造思想,跟上形势,但并不信任他们”(第21页);蓝先生还说,“斯大林的世界主义有点像我国批判过的崇洋媚外”(第67页)…… 蓝先生随笔的这一特点是时下的许许多多学术论文中所稀缺的。正是由于这一特点,这些点睛之笔使我们在读蓝先生的俄苏文化随笔时感到亲切,有益,开智。1950年代,我国流行过一句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曾经急匆匆地机械地搬用了许多苏俄的东西,其中包括很多坏东西,一些坏东西即使现在也仍然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和社会生活里顽固地起着作用,尽管如前所述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也竭力摒弃那些东西。蓝先生的书就是帮助我们摒弃从苏俄照搬来的坏东西的好助手,因为它让我们认识到:苏联不成功的社会主义文学、文化与社会模式离我们是“那么远”,又“那么近”。 收在《那么远 那么近》里的文章几乎篇篇是华章。我相信它们将长久在我国的读者中流传。但我建议集子再版时删去最后的那篇《荒诞中的现实——读〈羊奶煮羊羔〉》,因为《羊奶煮羊羔》是一位当代俄国三流甚至更多流的作家,站在旧有的文化立场上,对苏联解体后俄国文学生动活泼局面的充满羡慕嫉妒恨的诋毁,反映了苏联文化的遗老遗少们对昔日文坛“秩序井然”的留恋,不值得让我们的读者花时间去读。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12月19日09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