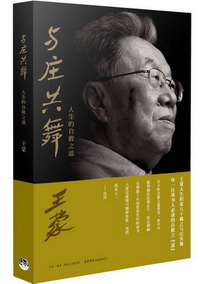 《与庄共舞:人生的自救之道》;王蒙 著 庄子这人太有意思了。惠子总是充当他的辩论方,然而惠子也很可爱,智商也非常高。庄子他不跟惠子辩论,他还精神不起来。《逍遥游》里两人有这样一段对话: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大瓠无用,可信,但不可爱。乘瓠浮游也好,散发弄扁舟也好,可爱,但不可信。可爱的许多东西,并不是真实的月与花,只是想象中的水中月梦中花罢了。 什么意思呢?惠子讽刺庄子。惠子说,我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魏王得到了一粒种子,这种子长成了一个大葫芦,这葫芦大到什么程度呢?将这个葫芦的心挖空,可以装五石的容量。过去讲究石、斗、升、合,这都是容器,是度量衡的工具。可这葫芦长这么大你怎么用呢?在这葫芦里装水吧,葫芦很脆,一下就裂了缝,水哗啦流下来了。把它劈成两半吧,裂开后又不能当工具用了。若是这葫芦长得小点儿我们倒有法子,过去农村尤其是河北农村,包括新疆农村都很喜欢用葫芦做工具。因为过去没有自来水,得挑水,挑上两挑或三挑,把水缸装满。用水的时候,就用这轻巧的葫芦伸进水缸舀一瓢水,非常方便。如果是葫芦太小了不好用,那就拿来当玩具,这个倒简单。葫芦不大不小,正好用来舀水。那么这个特大的葫芦,用它干什么呢?当然,葫芦还可以当容器,用来装别的东西,或者是别的什么用途。庄子一听就笑了,说一看你就是只会往小了用,你就不懂得往大了用。 这个庄子说话啊,是故事里套故事,他马上就讲一个故事: 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纟光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纟光,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纟光,则所用之异也。 庄子说,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地方,当地的人都是靠洗衣为生。以洗衣为生就要防止一件事———手皴裂,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所以当地人发明了一种擦手润肤的外用药,这个擦手药涂上后,手沾到水,风再一吹,不会皴裂。结果有一个高人,就来买这个药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买这个知识产权,我不买药,只买药方,而且我一下给你们很多钱。当地的这些洗衣服的人心想,我们靠洗衣服挣得太少了。现在有人一下拿这么多钱来买这药方,卖给他!于是,这个人拿了药方以后跑去献给了吴王。 吴王(吴国即现在的江苏一带,越国是浙江一带)正要和越国打仗,越国的水多,吴国军队很怕到了越国沾了很多的水后,身上这儿长皴、那儿长皴,皮肤受不了,所以就把这个药方和制出来的药当作军需用品、军事物资。最后由于吴军使用了按照这个药方配制出的药,保障了他们皮肤不皴不裂,并且身体不生病,吴一举大破越国,取得了战争的辉煌胜利。那么这个献药方的人因此被裂土封侯,成了贵族。(这个故事稍微悬乎点儿。) 庄子说这个药方在村里那些洗衣服人手里,它的最大作用就是让他们继续洗衣服。在高级宾馆,洗一件衬衫能够给你三四十块或者更多的钱,但那些洗衣妇是挣不上什么钱的。那个人买药方,假设用了五万元,让人觉得这了不得了。但他把这个献给吴王以后,瞬间变成了军需物资,支援了水战,军队以此取得了战争胜利。这个人也因此被裂土封侯,光宗耀祖。你看这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用法,平常人就不会用。 再来说这个大葫芦,大葫芦很好办啊: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既然它不能舀水也不能用来做别的,干脆坐上这个葫芦,在江河湖海中游历、游玩,让它成为一种水上旅游或者个人逃避尘世、逃避朝廷、躲开公众、自我救赎、特立独行的新项目,用当代的说法,视之为体育活动或旅游新招也未尝不可。庄子的想象力当然远远超过了向他发难的惠施。惠施谈的是实用,是操作性掂量;而庄子谈的是想象,是浪漫性抒情。虽然此情阔大张扬、无边无际、优哉游哉,其乐何如,以浪漫辩务实,仍会有诡辩———即避实就虚、高空立论、以忽悠代替讨论、以艺术想象取代日常生活的嫌疑。浮于江湖,偶一为之或有可能,将之视为大瓠(瓠就是那个大葫芦)的用途,技术性问题恐怕太多。惠子已经预设,大瓠脆而不坚,舀不起那么多水,水往上一舀,它也“嘎巴”就裂纹,难道经得住一两个活人坐在上头航行?乘着这个在江河湖海中游玩,恐怕是只有“中国横渡第一人”张健才敢吧。 但是庄子这个心态让你觉得好得没有办法,你拿他没辙,大葫芦不能当工具用,我把它当旅游用品、交通用品、当水上五日游的用品,他是这样一种心态。而且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后世。我们知道,李白名诗:“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然后底下他说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既然人生有这么多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一想到这些事情就会心乱,有很多的焦虑。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些东西全抛弃,把头发散开,也不拢头了,也不吹风了,也不用定型胶了,头发随便它什么样。然后坐一条小船,在水上,在洞庭湖,说老实话,古人讲海上的游玩少,喜欢讲的是江湖,乘瓠游于江湖。 李白的这首诗里头,尤其是谈到散发弄扁舟部分,我们可以看出庄子乘瓠而游于江湖的这样一个影响:自由、逍遥、孤独、空茫,接近于、消失在地平线上。这又怎能不让人为庄周与李白感到悲凉呢?然而很美。用粉丝们对张爱玲的说法,叫作“凄美”。浮游江湖的阅读审美性能,大大超越了思辨功能,更不具备实践性。它同样是哲学为人类困境寻找答案的无力与美丽的空话果实。正如王国维感叹:“世上的哲学,可爱的多不可信,可信的多不可爱。”说大瓠无用,可信,但不可爱。乘瓠浮游也好,散发弄扁舟也好,可爱,但不可信。一切不是真实的月与花,只是想象中的水中月梦中花罢了。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