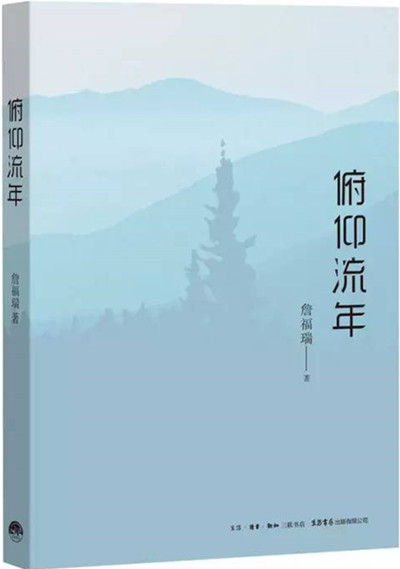|
国家图书馆老馆长任继愈先生(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字又之,汉族,山东省平原县人,中国哲学家、宗教学家、墨学研究专家,1916年出生,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西方哲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他认为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认识到中国佛教和道教思想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力图将其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2009年7月11日逝世,享年93岁。俯仰之间,急景流年,任继愈先生已经离开8年了。 本文是国家图书馆前馆长詹福瑞先生悼念老馆长任继愈先生的一篇文章,收录于新书《俯仰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 2017-6)。  任继愈在国家图书馆310室 国家图书馆的310室 文 | 詹福瑞 今天是老馆长任继愈先生的忌日。八点,走在国家图书馆行政楼走廊里,经过装修的行政楼焕然一新,红色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六楼服务台,白色大理石贴面,站在台前的两个女服务员漂亮光鲜,见到我来,站得笔直,颔首点头,以示敬意。一切都同往常一样。 走到楼道的尽头,蓦然想到了任先生的办公室。五年,却恍如隔世。任先生的办公室原在三楼,紧靠东头的两间。外间是会客室,里间是办公室。说是两间,其实外间似走廊,极狭窄,摆着新馆开馆时的旧沙发,木扶手,灰布面坐垫和靠背。沙发虽小,摆在那里,人来去也要侧身而过了。就是在这样简陋的会客室,任先生接待中央领导,也接待普通读者。办公室也不大,一个写字台,四周排满书架。这里既是他办公的地方,也是他从事研究的所在。 任先生一九八七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此前,虽经十年调整,恢复了图书馆的正常业务,但条件依然处在逐渐改善之中。十八年寒窑之苦,任先生率领员工,使国家图书馆终于显现出天堂的模样。为此,不仅本馆的员工,本国的同行,就是世界图书馆界,对这位出身于哲学家的管理者,也都充满了敬意。 我和任先生谈工作,一般都在周四。先生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倾下身来,认真听,再发表意见。他的语言如同其文章,极省练,却切中肯綮。二〇〇五年,馆里按照上面的要求实行全面改革,工作人员要定为几等岗,矛盾很大。任先生听了我的汇报,讲了王安石变法的故事。王安石推行新法,极为神速,但是激化了矛盾,立足未稳,就被推翻。因此改革不宜速进,而应渐进。他虽然未对改革方案提出具体意见,但他的改革渐进的观点,显然是深谋远虑的意见。  老馆长任继愈(左)和詹福瑞 早在一九九九年,任先生就预见,二十一世纪的图书馆,存在和发展模式将有根本性的变化。国家图书馆要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出战略性、前瞻性的规划和部署。我到馆工作后,任先生就此与我有过多次长谈。二〇〇五年我馆提出的两大发展目标:建设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国家图书馆;三大发展战略:人才兴馆、科技强馆和服务立馆,就体现了任先生的思想,包含了他的智慧,多是我们交流讨论的结果。 我与任先生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人才问题。我曾经看过任先生历年在职工大会上的讲话,有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人才,为什么如此?任先生说,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二十世纪,世界列强争夺的是自然资源,进入二十一世纪,已经转向人才资源,拥有人才的国家才有前途。以色列是世界二十个最发达国家之一,但是它国土很小,被沙漠包围,缺水,靠什么成为强国?靠人才。所以建设现代化的图书馆,必须从抓人才入手。他给我分析过国家图书馆的队伍。“文革”后,百废待兴,国家图书馆缺少馆员,尤其是新馆开馆,更需要扩充队伍。但在当时,社会上还没有大学生,所以招来的馆员,主要是回城知识青年和部分占地安置人员。这些人虽然学历低,但有极强的责任感和上进心,他们通过自学考试、上大专班等形式,取得中专或大专学历,成为馆里的业务骨干。八十年代初,恢复高考的大学毕业生陆续进入国图,队伍不断增强,但还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事业形势。因此,九十年代,他就提出实施人才发展工程,提高现有人员的水平,尤其是注重有影响带头人的培养,同时还要大力引进人才,为未来的事业准备人才。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馆里完善了馆员继续教育制度,出台了首席专家、外籍专家、资深馆员制度。 任先生重视科学研究与现代技术的应用,并且身体力行。他给我讲,没有理论指导,我们的工作就是盲目的、低层次的,因此必须加强图书馆理论与应用的研究,解决发展的方向问题、政策问题,也要解决业务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这些工作有人做,高校就是研究的主力。但是图书馆不能让出这个阵地,尤其是国家图书馆,要引领全国图书馆业务发展方向,不研究就无法引领。我到馆不久,任先生就叫办公室给我送来美国国会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书,要我读,嘱咐我关注数字图书馆的研究。我们两人还专门讨论过研究院三个方向的设计。  国家图书馆新馆 任先生对中华民族文化有过论断,认为,中华民族过去有过春秋与汉唐三次文化大繁荣,我们将会迎来第四次繁荣期。我个人并未把任先生此话作为他对中华文化发展的预测,而是看成了他对民族文化复兴寄予的厚望。他强调的不是繁荣期的到来,而是如何为文化繁荣做准备。任先生常说,文化没有暴发户,不似炒股,一夜暴富,文化的繁荣不是等来的,要靠长期的积累,现在就是文化积累期。当代人的工作,就是为迎接第四次文化大繁荣做好准备。而他和图书馆的任务,就是做好文献的整理,当后人的铺路石。正是在此种自觉的文化发展意识下,任先生自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就率领中华大藏经、敦煌遗书、中华大典等几支整理与编纂队伍,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而办公室就成为任先生领导这些工作的指挥部,也是他组稿、审稿的编辑部。所以办公室虽小,包蕴却甚大,涵载了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厚重信息。 图书馆的服务,任先生与我谈得最多的是文献揭示。国家图书馆收藏着中国历代最珍贵的图书,它既是国人的财富,也是世界的财富,但束之高阁,谈何嘉惠学林?任先生说,文献整理,对于国家图书馆而言,不仅仅是为了文化积累;同时也是为读者阅读使用提供方便。任先生讲到他组织编纂《中华大藏经》的最初缘由。有一年,在本馆见到了老朋友季羡林先生。此次季老来国图,不是自己看书,是陪他的学生来看《赵城金藏》。任先生不明原因,问之,才知道,馆里有规定,似《赵城金藏》这样的文献,不给普通读者提供阅读。没办法,季老只能自己出面,借出此书,给学生使用。此事深深地触动了任先生。图书馆的职责就是为读者提供文献阅读,更何况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躺在图书馆里的书,怎能发挥其作用。但是又如何克服文献保护和读者阅读的矛盾?任先生想到了文献整理与揭示。于是在一九八二年国务院古籍保护规划会上,任先生提出了在《赵城金藏》基础上编纂《中华大藏经》的项目,开始了历经十余年的《中华大藏经》编纂工作。而这一切,都是在这小小的办公室里酝酿、展开的。  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编纂工作 我在任先生身边工作了六年,亲身感受到何为仁者。大儒必为仁者,好领导也应具仁者之风。仁者是真人,心胸坦荡。任先生早年信儒教,新旧中国比较,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怀疑,改信马克思主义。为此,给自己的老师熊十力写信,老师回复:“诚信不欺,有古人风。”他的诚信,不仅在对老师坦诚,更在信仰之真。今之学者、领导们,要么没信仰,要么嘴里咳唾珠玑,其实皮里阳秋。大哉,任老的“古人”之誉! 待事如此,待人亦如是。不分贵贱,无论官民,一律谦卑恭敬,真诚相待。凡与任先生接触过的馆员都有感受,任先生是一位温厚幽默的长者,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哲人,却没有人感到他是个官。子夏说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任先生给人的感觉是如此,又非如此。任先生望之严整,即之温厚,听其言淬炼而不乏幽默。他的办公室是敞开的,对每一位员工,甚至是读者。只要有约,任先生总是排出时间接见。有一年,我原单位的领导来访,他大学就读于南开大学哲学系,学的就是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听说任先生就在隔壁,甚为激动,希望能拜见任先生。任先生每次来馆,公务很忙,客人的临时之请,使我有些犯难。就说,我去问问吧。谁知,任先生痛快地答应了,而且还一起合了影,这让我和客人都颇感意外。后来办公室人员告诉我,时有这样的情况,读者事先无约,慕名而来,任先生知道了,也会见上一面。 仁者,爱人。二〇〇五年,任先生卸任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我当了十八年馆长,只做了一件事。办公楼一楼进门玻璃没有标志,有人撞破了脸,我叫人贴上标志。”一件小事,却是领导最根本的工作,对员工的仁爱。在馆里,我常常听到任馆长关心员工的故事。为了员工的事,任先生也写过便签,嘱咐我解决。作为他的同事和晚辈,我也亲自感受到他的关心、甚至关照。二〇〇六年,我还在舞蹈学院租房住。一天,任先生爬上四楼来看我,进门,还没落座,就说:“福瑞同志,我把你请来,真是委屈你了。”那年,任老九十岁。二〇〇八年十月,我因病住院,任先生要来医院看我,我嘱咐办公室主任,千万劝住任先生,不叫他来。但一天午后,任先生还是拄着拐棍到了病房,那年他九十二岁。出院后,任先生又来办公室,嘱咐我工作不要着急,读书不要熬夜,还送了我一台周林频谱仪,叫我理疗。 如果不是其他原因,周一和周四,任先生无一例外,都要到办公室上班,直到二〇〇九年住进医院。每到这个早上,一辆车都会悄然滑行到楼门口,一个老人精神矍铄地登上通往五楼的楼梯。从来不让人拎包,从来不用人陪同,一个人走过楼道,开门,进入办公室。我与他的办公室紧邻,每到此时,总会感受到一个老人轻缓但又坚定的步履,没有喧嚣,没有张扬,但是他的气场却充盈着整个楼道,他使国家图书馆、使我们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员工,都充满了底气。我知道,那不是权力的力量,是思想、学问与人格的力道。没有行迹,却力透丹青。 任先生去世后,他的办公室一直原样保存。本来设想,以之作为纪念室,纪念这位担任馆长之职二十余年的老馆员、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同时用来教育年轻的馆员。但是二〇一一年行政楼重新装修,任先生办公室没有保留下来。每每想起此事,就颇感遗憾。有时也会想,如任先生在世,以他的性格,也不会建纪念室的。有的人把纪念馆建在了地上,有的人却把纪念馆建在人们的心里,任先生当属于后一种吧。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