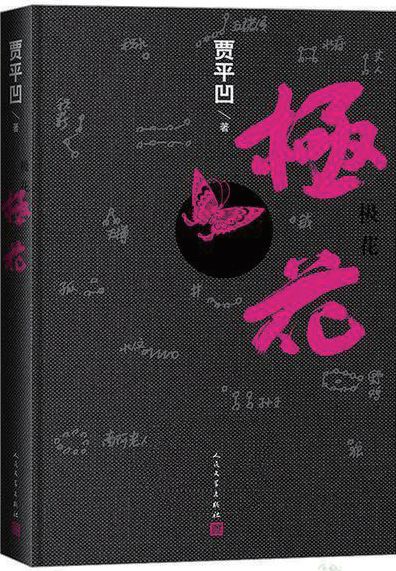 《极花》在蝴蝶的看似不得已的认同中也内在化和自然化了这一性/社会性别制度,并将这个制度放在了寓言的框架中将女性在这个古老的性别权力关系中的认同视为了必然。那么,当《极花》在用城乡矛盾这个“因”去合理化性别问题的“果”时,去打破这个因果逻辑并揭示女性如何被结构化于“性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才是《极花》这部小说的书写方式带给我们的“负面”启示。 贾平凹的小说《极花》写的是一个拐卖女性的故事,但是小说在《后记》中说作者关注的是大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怎样地凋蔽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的问题。所以从性别的角度看,一方面女性作为被交易的物品被放置到不同位置上的客体性仍然没有变化,具体到小说中,女性是城乡矛盾中可以被城市夺走的资源,也是乡村反夺回来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小说从拐卖女性的残暴问题倒推出拐卖女性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即城市对农村资源的剥夺导致的女性资源流失。于是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将拐卖女性的不合法性转变为牺牲女性以拯救农村的合理性,至少是一种无奈。但是,小说并没有直接用城乡矛盾掩盖性别问题,贾平凹所关注的农村凋蔽问题是和蝴蝶的认同过程同时展开的,所以就非常寓言化地带出了关于女性的一些讨论:在讨论性别问题时,城乡等问题必然缠绕其中,但是为何性别却往往被看得不那么“重要”而被搁置?小说主人公蝴蝶最终又回到了农村,这是被拐卖女性的必然认同,还是男作家对女性道路的狭隘性想象?为何女性在城乡的资源争夺中成为可被交易的一部分而成为牺牲品? 在小说所呈现的城乡问题和性别问题讨论中,后者往往作为“果”而被城乡问题的“因”所裹挟,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主人公蝴蝶的认同过程的话,我们会看到蝴蝶被迫一步步地认同了自己的性别身份和在乡村中的处境。而这一性别的认同过程被充分自然化了,以至于在充满复杂的性别权力关系的父权制村庄中,这种被自然化了的认同根本不会让人觉得存在任何问题,因而蝴蝶寻花的寓言就成为被拐的女性的必然道路。 小说的封面便非常寓言化地体现出了主人公的道路:蝴蝶在向“极花”飞去,蝴蝶寻花的寓言成为主人公现实中的认同之路。而这个认同是通过蝴蝶肉体的“死”来完成的,即“蚌病成珠”的过程,正如蝴蝶在土窑的感受:“感觉这土窑已经不是牛魔王了,是一只蚌,吞进了我这粒沙子,沙子在磨砺着蚌肉,蚌肉又把沙子磨成了珍珠,挂在黑亮的脖项上给他着得意和体面。”当蝴蝶第一次跑被抓回来时,蝴蝶的魂跳出了她的身子,蝴蝶被一分为二,“我竟然成了两个,我是蝴蝶吗?我又不是蝴蝶”。让被拐来的女人不再跑的方法就是让她在性上屈服并为男人生孩子,“你上不了她,她就不给你生孩子,你就永远拴不牢她。”在《招魂》这一部分,黑亮爹指挥着黑亮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上演了一出残暴的“强奸盛宴”,当6个人跑到蝴蝶的窑里时,“我”和蝴蝶成了两个人,在描述这场戏剧冲突时,小说的叙述视角也从“我”转变成了蝴蝶。当蝴蝶怀孕以后,她突然透过白皮松看到了两颗星,“我那时心里却很快慌起来,我就是那么微小昏暗的星吗?这么说我是这个村子的人了,我和肚子里的孩子都是这村子的人了?命里属于这村子的人,以后永远也属于这村子的人?我苦苦地往夜空里看了多么长的日子啊,原来就是这种结果吗?” (责任编辑:admin) |
